安陵容重生之点子王的诞生(安陵容夏冬春)热门网络小说_小说推荐完结安陵容重生之点子王的诞生(安陵容夏冬春)
刀锋落在砧板上,发出沉闷而规律的哒、哒声。洋葱半透明的表皮蜷缩起来,辛辣的汁液渗出来,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催人泪下的气息。我正低头对付着最后一瓣,他声音就从厨房门口飘过来,不高,却像枚楔子,精准地钉入了这日常的噪音里。
“我们分手吧。”刀尖一顿,然后猛地一滑。指尖传来一丝凉意,紧接着是迟来的、细微的痛。我没去看那刀口,只是抬起头。
洋葱那股子浓烈的气味直冲眼眶,视线瞬间就模糊了,眼泪不受控制地唰地往下流,又急又烫。他站在那儿,身后是客厅寡白的光,表情看不太真切,只有一个沉默的轮廓。
我抬手用手背胡乱抹了一把脸,皮肤上立刻留下辛辣和咸涩混合的味道。嘴角却努力往上弯,做出一个笑的模样。声音大概被眼泪腌过,有点哑,但努力轻快着:“没关系啊。”顿了顿,像是在找一个合适的、轻松的理由,来承接他这突如其来的判决。
“反正……”我又抹了一下眼睛,语气更轻巧了些,“反正明天是星期八。”星期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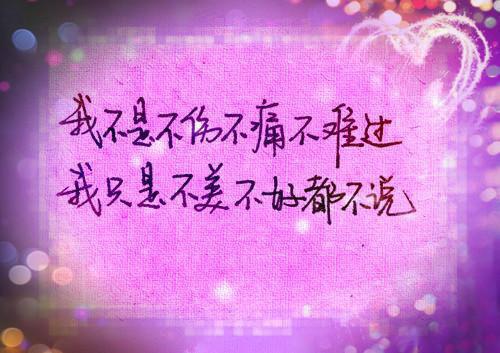
那是我和他之间的一个老梗。刚在一起时,日子甜得发腻,总嫌周末太短,抱怨为什么没有第八天。后来就说好,偷一天,只属于我们俩的一天,不管日历上印着什么,那天就是星期八。是窝在沙发里看旧电影啃一袋薯片的星期八,是赖床到中午共享一碗泡面的星期八,是手牵手在深夜无人的街道上漫无目的闲逛、大声唱着走调的歌的星期八。
一个现实里根本不存在、被我们凭空捏造出来的日子。他好像哽了一下,没接话。
沉默了几秒,转身走了。厨房里只剩下我,和那半个被剁得七零八落的洋葱,弥漫着让人持续流泪的气味。后来,就是收拾东西的窸窣声,拉链划上的声音,行李箱轮子碾过地板。门锁咔哒一声,轻巧地合上。世界突然静得可怕。眼泪早就停了,眼睛干涩得发痛。我站在原地,看着砧板上的狼藉,看着料理台上那道细微的、几乎看不见的血痕。忽然觉得,这房子真大,空得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回声。他走了。把所有的“星期八”也一并带走了。
时间好像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锈住的,齿轮卡在一个再也转不动的点。日子照样过,太阳东升西落,窗外的街灯准时亮起又熄灭。但我好像被留在了那个他说分手的午后,留在了那个洋葱气味弥漫、眼泪肆意横流的瞬间。日历一页没撕。不是刻意纪念,只是忘了。
或者觉得,撕不撕,也没什么分别。冰箱门上还贴着那张黄色的便利贴,是他搬走前最后一张。字迹有点飞,是匆忙间写下的:“牛奶过期了,记得买。
”下面还画了个小小的、歪扭的笑脸。那瓶喝了一半的牛奶,果然静静立在冰箱冷藏室里,瓶身上印着的日期,早已过去了好几天。我把它拿出来,拧开盖子。气味似乎没什么不同。
我倒了一杯,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带着一点若有似无的、说不清是变质还是心理作用的微涩。每天喝一点,每天喝一点。
仿佛这是一种顽固的仪式,只要这瓶他提醒过过期的牛奶没有彻底喝完,有些事情就还没有真正结束。好像那扇门还会咔哒一声从外面打开,他带着一身室外的空气走进来,皱着眉问:“怎么还在喝这个?”胃偶尔会轻微地抗议,隐隐作痛。我把它当作一种陪伴式的疼痛。生活被抽走了某种核心的动力,变得扁平而重复。
上班,下班,对着电视屏幕发呆,直到屏幕熄灭映出自己模糊的脸。食欲变得很差,经常就用一杯过期的牛奶和几片饼干打发一餐。体重秤上的数字悄悄往下掉了几格。
朋友发来过问候的消息,寥寥回复几句“我没事”、“挺好的”,屏幕便暗下去不再亮起。
睡眠是另一个难题。床变得格外大,空出一大半。有时半夜惊醒,手会无意识地伸向旁边冰冷的被褥,然后彻底清醒,在黑暗里睁着眼,直到天色泛白。
梦里总重复同一个场景:我在切洋葱,他站在门口说话,眼泪流下来,我说“反正明天是星期八”。每一次,梦就停在这里。
有时会无意识地在空荡的房间里叫他的名字,声音脱口而出,才被四周的死寂吞没,显得格外突兀和可笑。日子像一卷循环播放的录像带,内容单调,画质灰败。而我,活在一个被命名为“星期八”的、不存在的间隔里,不前,也不后。直到那天晚上,家里的饼干彻底吃完了,连替代的零食也找不到一包。胃里空得发慌,一阵阵收缩着提醒我。
不得不换下家居服,套上件外套,下楼去拐角那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夜风有点凉,吹在脸上让人清醒不少。便利店的白光刺眼得很,货架排列整齐,冷气开得很足。
我径直走向摆放饼干的货架,拿了两盒最常吃的口味。转身想去柜台结账,视线不经意地扫过冷柜区。整个人瞬间被钉在原地。冷柜明亮的灯光下,是他。侧对着我,正低头看着手里的一盒鲜奶,检查日期。他身边站着一个女孩,穿着明亮的鹅黄色连衣裙,头发挽起来,露出一段白皙的脖颈。女孩伸手从冷柜里又拿出一盒酸奶,凑到他眼前,笑着说了句什么。他侧过头看她,脸上露出一种我很久没见过的、放松又温和的笑容。
那笑容像根细针,轻轻扎了一下心脏某处。不剧烈,但尖锐无比。他恰好在这时抬起头。
目光越过女孩的肩头,和我撞个正着。那点笑容瞬间冻结、碎裂,从他脸上剥落。
只剩下全然的意外,和一丝无处遁形的尴尬。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将手里的那盒鲜奶往身后藏了藏,像一个做错事被抓现行的孩子。
女孩顺着他的目光疑惑地转过头来看我。空气凝固了几秒。他喉结滑动了一下,像是艰难地吞咽下什么。然后往前挪了半步,动作有些僵硬,声音干巴巴的,对那个女孩说:“呃……这是我前女友。”“前女友”三个字,被他吐得格外清晰,又格外轻飘,像烫嘴。女孩的脸上立刻露出一种混合着好奇、打量和一丝微妙优越感的神情。
她很年轻,眼睛亮亮的,充满某种未经世事磋磨的光泽。她大大方方地冲我笑了笑,那笑容明媚得有些刺眼。“哦——”她拖长了声音,目光在我和他之间转了转,最后落回我脸上,语气轻松,甚至带着点天真无邪的残忍,“好巧啊。你们……分手多久了?
”问题抛向我。便利店里的背景音乐正好放到一首甜腻的情歌,歌词唱着永恒不变的爱。
我握着那两盒饼干,手指无意识地收紧,纸盒边缘硌着掌心。视线越过他们,落进他们身后的购物车里。里面零零碎碎放了些东西,最上面,是几盒鲜奶,纸盒崭新,生产日期印得清晰而新鲜,预示着很长一段不会变质的日子。
胃里那杯过期牛奶沉淀下的微涩感,忽然又泛了上来,细细密密地灼烧着。我抬起眼,看向提问的女孩,再慢慢看向他——他避开了我的目光,盯着便利店光洁的地板,仿佛那上面有什么极其吸引人的花纹。声音出了口,才发现平静得连自己都意外。“不久。
”我说。顿了顿,像在认真计算一个不存在的日历。“刚好一个星期八。
”空气似乎凝滞了一瞬。便利店的冷气嘶嘶地响,吹得我裸露的胳膊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
他像是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猛地别开脸,视线死死黏在冷柜玻璃上,仿佛那里面陈列的不是牛奶,而是什么至关重要的学术标本。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
那女孩脸上的明媚笑容短暂地僵了僵,显然没听懂,细长的眉毛困惑地挑起:“星期八?
”她下意识地重复,语气里裹着一种天真又残忍的探究欲,目光在我和他之间逡巡,试图找出这个陌生词汇下隐藏的密码。他没有解释。一个字也没有。像是骤然患上了失语症,沉默得近乎失礼。而我,也不再开口。胃里那点过期牛奶的酸涩感顽固地弥漫上来,顶着喉咙口。我捏紧了手里的饼干盒,纸壳边缘深深陷进掌心,带来一点清晰的、可供锚定的痛感。
女孩似乎终于察觉出这氛围里某种不容插入的粘稠和怪异,那点好奇被尴尬取代。
她不太自然地伸手,轻轻拉了一下他的胳膊肘,声音低了下去,带点催促的意味:“……走吧?还要去买别的。
”他几乎是立刻、顺从地被那一点微小的力量牵引着转身,像是巴不得立刻逃离这个冰柜前的方寸之地。他没有再看我一眼,背影显得有些仓促,甚至踉跄了一下,手臂不小心撞到旁边的促销堆头,几瓶果汁摇晃着险些滚落。
他手忙脚乱地扶稳,动作完全失了平时的从容。女孩紧跟在他身侧,微微侧头,最后投来一瞥。那目光里没有了笑意,只剩下一种模糊的警惕和说不清的费解。
他们绕过货架,消失在排列整齐的商品丛林之后。
收款台的方向传来模糊的扫码声和店员机械的“谢谢光临”。我站在原地,冷柜的寒气一阵阵扑来,直到手脚都变得冰凉。手里两盒饼干的重量,忽然变得沉甸甸的,几乎要提不住。最终,我没有去买单。我把那两盒饼干放回了原处,甚至小心翼翼地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