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归来,我成了恶毒奶奶的克星(堂屋晓萌)完本小说_全本免费小说重生归来,我成了恶毒奶奶的克星堂屋晓萌
第1章:重生初醒,晨光中的算计1992年3月7日清晨,陈家屯北方平原初春的晨雾尚未散尽,像一层灰白的纱,笼罩着陈家屯的土路。
昨夜刚下过雨,低洼处积起浑浊的水洼,泥泞不堪。村口的老式广播喇叭吱呀作响,声音断断续续,听不清在播报些什么,更像是这个沉闷清晨的背景噪音。
我躺在西屋冰冷的土炕上,猛地睁开了眼睛。身下是硬得硌人的炕席,身上盖着一条洗得发白、边缘早已磨出毛边的粗布被子。我动了动手指,指尖触到粗糙的被面,一股冰冷的寒意立刻顺着皮肤蔓延上来。
这具十八岁的身体瘦削得厉害,窄窄的脸庞,微微凸起的颧骨,头发用一条旧布条胡乱扎在脑后,几缕碎发被汗湿了,贴在额角。我是陈晓禾。
陈德海和李桂芳的长女,陈晓萌和陈晓强的姐姐。也是三个月后,会被奶奶周氏以六百块彩礼的价格,卖给赵家村张屠户家的儿子张铁柱“冲喜”,最终在婚后遭受持续殴打致死的那个陈晓禾。我回来了。回到了悲剧发生前的三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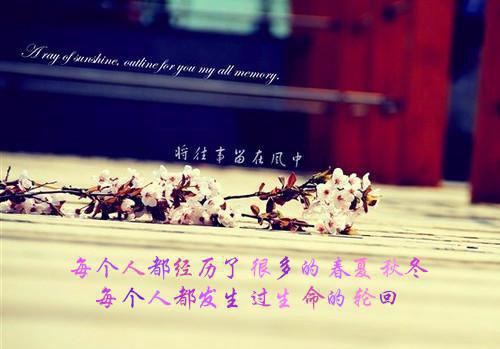
前世的眼泪、哀求、下跪,换来的只是周氏毫不留情的一巴掌,和一句“不孝不顺,白养你十八年”的冰冷斥责。父亲只会低头抽着闷烟,母亲躲在厨房角落偷偷抹泪,妹妹沉默地低下头,弟弟则一心只读他的圣贤书——仿佛这个家的所有指望,都压在我一个人的牺牲上。我死在了那个冬天。雪下得并不大,却冷得刺骨。
他们甚至连一口像样的棺材,都没舍得给我置办。但现在,我不再指望任何人。也不再流泪。
我只冷静地等待,那个能撬动命运的机会。西屋的门被“吱呀”一声推开时,我正闭着眼假寐。是奶奶周氏进来了。她手里端着一个粗瓷碗,里面是昨晚剩下的、已经凝成坨的玉米糊,碗边还挂着一圈糊底的焦痕。她六十出头,背微微佝偻,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深沟,嘴唇习惯性地紧抿成一条严厉的直线。
作为爷爷的续弦,她虽未生育,却在陈家掌了整整三十年的家。她最常骂我懒惰,却把所有的疼爱都给了弟弟。“还躺着?”她把碗重重搁在炕沿,声音干涩生硬,像晒焦的豆荚,“天都大亮了,还不起来烧火?你娘得带晓宝,晓萌得看着弟弟,你这个当大姐的,就只会挺尸?”我没有动,只是轻轻地、压抑地咳嗽了两声。
她皱起眉头:“装什么相?赶紧起来干活!”我慢慢地侧过身,一只手虚弱地按在胸口,声音刻意放得又轻又飘:“奶……我昨夜一宿没睡踏实,今早起来头晕得厉害,眼前发黑,怕是……真病了。”我的脸色本就苍白,加上昨夜故意熬着没睡,眼下泛着明显的青黑。
我刻意将呼吸放得急促些,手指也微微颤抖,俨然一副气力不支的模样。她盯着我,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半信半疑的光。我知道她不信。从小到大,我从未被允许请过一次大夫,病了也只能硬扛。但她也不敢真让我就此倒下——家里三个孩子,里里外外的杂活,她还指望着我去做。她往前凑了半步,压低声音:“真病了?”我点点头,又重重地喘了口气,像是费了极大的力气才挤出话:“我……我昨夜做了个梦,梦见王婶来咱家了……说赵家村的张屠户……愿意出八百块彩礼,想娶……想娶晓萌。
”我故意顿住,又急促地喘了几下,仿佛连说话的力气都快耗尽。
王婶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媒婆,四十多岁,能说会道,经她手撮合成的婚事少说也有二三十桩。她虽从未踏进过我家门槛,但名头在村里却是响当当的。提她,能增加这话的可信度。奶奶的眉头猛地一挑。“谁说的?
”她的声音瞬间绷紧了,“王婶真来过了?”我摇摇头,眼神黯淡下去:“是梦……可那梦做得太真了。我甚至听见张屠户夸,说晓萌‘眉清目秀,是好生养的相’,比……比我强多了。”我低下头,语气里刻意掺入一丝卑微和认命。
屋里陷入短暂的寂静。奶奶没有立刻说话,但她的眼神变了。最初的不耐烦和嫌弃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难以察觉的光亮,虽一闪即逝,却清晰无比。八百块。
比预定卖我的六百块,整整多出两百块。她沉默了两秒,才冷哼一声:“胡吣什么!
病了就少嚼这些舌根子,仔细闪着舌头!”可她转身离开时,脚步明显快了。
她没有再骂我懒,也没有端走那只粗瓷碗,只是匆匆掀开门帘走了出去。我知道,她信了。
或者说,那多出的两百块彩礼,让她宁愿相信这是真的。我重新躺回炕上,闭上眼睛,慢慢调整着呼吸。藏在被子底下的手指,却一节一节地轻轻屈起,像是在无声地计算着所剩无几的日子。八百块彩礼,足以换一个人。那原本定给我的六百块,为什么不能退掉?母亲李桂芳端着一碗热水进来时,我正睁着眼,望着房顶上那根有裂纹的老松木房梁,以及角落里积着的蜘蛛网。她年纪不到四十,看上去却苍老得像五十岁的人,头发枯黄,眼角无力地下垂着。她站在门口,见我醒着,迟疑了一下,轻声问:“……真不舒服了?”我点点头,没说话。她把碗放在炕沿,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她的手很粗糙,带着常年操持灶台的烟火气。她似乎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又咽了回去,只轻声嘱咐:“你爹说今天要去翻东头那块地,晌午……就不回来吃饭了。”说完,她转身要走。“娘。”我叫住她。她回过头,眼里带着惯有的怯懦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晓萌……最近,有人来给她提亲吗?
”她愣了一下,随即摇头:“没、没人来。你奶天天就念叨你弟读书费钱,哪还有心思张罗别的婚事……”我轻轻地“嗯”了一声,不再追问。她顿了顿,最终还是沉默地转身走了,脚步很轻,仿佛生怕惊动了什么。我知道她在害怕。
害怕奶奶的威严,害怕这捉襟见肘的日子,更害怕我一时失言,又给这个家招来祸端。
她不是坏人,只是被生活压弯了脊梁,磨平了棱角,连喘气都早已习惯了低着头。
院子里传来细微的水声,是妹妹陈晓萌在给弟弟陈晓宝喂水。晓宝才三岁,瘦瘦小小的,却是全家的心尖肉,也最爱哭闹。晓萌比我小两岁,圆脸,大眼睛,从小被养得细皮嫩肉,看着比实际年纪更显小。此刻她正抱着晓宝蹲在井台边,拿着个小勺子,一点点地耐心喂着。
她听见西屋的动静,抬起头朝这边望了一眼,似乎想进来,却被母亲用眼神无声地制止了。
“你姐身子不舒坦,别去吵她。”母亲低声说。晓萌乖巧地“哦”了一声,便低下头继续喂水,没有再过多询问。她在这个家里向来如此安静。不争不抢,像一株生长在墙角阴影里的草,默默无闻。但我知道,她心里其实比谁都明白。
前世她后来嫁了个老实本分的木匠,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
她从未出面阻拦过我被卖的命运,也未曾为我说过一句求情的话。我不怪她。
在这样一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家庭里,能够默默保全自己,已是一种本事。
奶奶从堂屋出来后,没有再进西屋。透过门缝,我看见她站在院子当中,手里虽然拿着扫帚,却心不在焉,根本没有扫地。她来回踱了两圈,最后蹲在屋檐下,手指无意识地在泥地上划拉着什么,那神态,像极了在反复盘算一笔至关重要的账。
她的心里,那八百块彩礼的种子,已然开始发芽。八百块,能买半头肥猪,能供晓强踏踏实实念大半年的书,能换回好几袋上好的化肥。更重要的是,张屠户是邻村赵家村的,家里有房有院,操持着杀猪卖肉的营生,怎么说也不算穷户。而我,仅仅六百块,就要被推去换一个病痨鬼的“冲喜”,换一条注定早夭的命。差了两百块,差的可能就是一生的命运。我闭上眼,感觉到清晨的阳光斜斜地透过窗棂照进来,落在我的右脸颊上,带来一丝微弱的暖意。前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刻,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是: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我绝不让任何人替我决定该去哪条路。现在,我真的回来了。我不急。奶奶会自己一步步把她算计的路走通。她会发现,那八百块的婚事,远比六百块的“买卖”更划算。等到那时,她自然会想方设法,推着晓萌往那条她认为的“好路子”上走。而我,只需要静静地等待。等待她亲手,将原本悬在我头顶的那把刀,递到我的手里。第2章:裂痕初现,午后的试探与贪婪西屋的土炕上,我睁开眼时,阳光已从窗纸的上半截移到了下半截,一道斜长的光痕投在斑驳的墙上,浮尘在光柱中无声飞舞。我慢慢坐起身,刻意让动作显得比平日迟缓些,带着几分病后的虚弱。粗布被子滑到腿边,我伸手去拉,指尖触到那磨得起毛的边沿,糙得硌手。外头灶房传来锅铲刮过铁锅底部的刺耳声响,是母亲李桂芳在准备一家人的午饭。我趿拉着鞋走到堂屋时,八仙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一碗蒸得裂了皮的红薯,一盘切得细细的腌萝卜条,中间是半碗油星几乎看不见的炒豆角。奶奶周氏早已坐在上首,手里紧攥着筷子,眼睛却时不时瞟向门口,像是在等什么,又像是在盘算什么。
父亲陈德海蹲在屋檐下的阴影里,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头的火光在昏暗中一明一灭。
妹妹晓萌抱着三岁的弟弟晓宝坐在门槛上,正小心翼翼地用小勺喂他喝水。
我悄无声息地走到桌边,挨着板凳边缘轻轻坐下。“病好了?”奶奶的眼风扫过来,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探询。“好些了。”我低下头,夹起一根豆角,慢慢地嚼,喉头像是还堵着东西,吞咽时显得有些费力。母亲端了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粥放在我面前,什么也没说,只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混着担忧和一种习以为常的麻木,随即又退回到灶台边,把自己缩进那片阴影里。我吹了吹碗里冒出的热气,忽然用不大却足以让桌上人都听见的声音,像是自言自语般地轻声说:“昨儿夜里,又做了个怪梦。”奶奶夹菜的手顿了一下。“梦见赵家村张屠户家院子里杀年猪,满院子都是白茫茫的热气,那肉香味……浓得我醒了好像还闻得见。”我顿了顿,声音更轻了些,“梦里他还说话,说娶人的事,彩礼愿意出到这个数。
”我伸出两根手指叠在一起,比了个“八”的手势,“八百块。
还说……往后家里能常有肉吃。”堂屋里霎时静得只剩下晓宝咿呀的吞咽声。晓萌抬起头,手里的勺子停在半空,愣愣地看着我。父亲从屋檐下站起身,把烟头在鞋底摁灭,一步步踱过来,沉默地坐在桌边。奶奶没动,但眼皮耷拉下来,遮住了眼底骤然闪过的精光:“你又瞎梦些什么?”“不是我瞎编的。”我摇摇头,语气虚弱却坚持,“昨天下午,王婶在井台边跟李家媳妇嘀嘀咕咕,我离得远,恍惚听见她提了一嘴,说赵家村那边确实有人来打听过,事儿还没定死,但人家……好像更中意晓萌。”“她真这么说了?”奶奶的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却透出急迫。“我离得远,没听全乎。”我低下头,用筷子慢慢搅着碗里的稀饭,“但王婶话里话外的意思,张屠户家……嫌我身子骨单薄,怕压不住福,冲喜不成反招灾。
倒是夸了晓萌……说脸盘圆润,一看就是好生养、能持家的。”话音落下,桌上没人接话。
父亲伸手去拿筷子,动作慢得像是灌了铅。奶奶盯着桌上那盘寡淡的豆角,嘴唇无声地抿了几下,忽然从鼻腔里挤出一声冷笑:“穷根还没拔掉,倒先做起吃肉梦了?
你当那八百块是天上掉下来的?”我没争辩,只是低头喝了一口稀饭,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仿佛那口粥有多难以下咽。我放下碗,手微微发抖,声音里带上一丝哽咽:“我不是馋肉……我是想着,要是真能攀上这门好亲,咱家日子也能宽裕些。晓萌能体体面面嫁过去,穿件新棉袄;晓强往后念书的钱,也不用愁了。”奶奶没立刻说话,但眼神彻底变了。那里面不再只有惯常的嫌弃和不耐烦,而是飞快地闪过一种权衡利弊的精明。她不傻。六百块卖了我,是处理负担;八百块嫁出晓萌,那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是赚头。父亲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在油腻的桌面上敲了两下,闷声道:“这事儿……不是说换就能换的。
铁柱那边虽没正式过礼,但话已放出来了,咱家现在反悔,赵家能善罢甘休?不怕人家闹?
”“闹什么?”奶奶的声音压得更低,却透着一股狠劲,“一没写婚书,二没过彩礼,空口白牙一句冲喜的话,谁能当真?再说了,张家肯出八百,实打实比铁柱家多两百块,里外里咱们都不亏!”“可晓萌才十七……”母亲的声音忽然从灶台那边飘过来,很轻,像怕惊醒了什么。奶奶猛地扭过头瞪过去,目光锐利得像刀子:“十七怎么了?
我嫁给你爹那会儿还不到十六!她比晓禾显小?身段不比她结实?脸盘子不比她周正?
张家能瞧不上?”母亲立刻噤声,把头埋得更低。晓萌抱着晓宝,喂水的手微微发颤,一滴水从勺边滑落,滴在晓宝的衣领上。她浑然未觉,只是死死盯着地面,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线。我慢慢把面前的碗推远了些,像是胃口全无。手垂到膝盖上,指尖悄悄掐进掌心,用细微的痛感提醒自己保持镇定,不能露出半分痕迹。“奶。
”我抬起眼,声音怯怯的,“要不……您私下找王婶问问?就当是打听打听消息,探探口风。
万一真有这回事,对咱家……终归是条好路。”奶奶没看我,枯瘦的手指在桌沿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心里那副算盘打得噼啪作响。
这顿午饭在一种诡异的沉默中匆匆结束。父亲撂下碗又下地去了,母亲默默收拾着碗筷,晓萌抱着晓宝躲到了院子最远的角落。我站起身时,故意晃了一下,伸手扶住桌角才勉强站稳。奶奶在堂屋门口站了片刻,忽然一转身进了里屋,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摸出她的烟袋锅,也不点火,就那么一下一下地磕着,烟灰簌簌落下。
我走到院子里,拿起晾衣绳上湿漉漉的衣裳,一件件重新搭好。粗布衣裳浸了水,沉甸甸的,粗糙的绳勒得手腕发红。我嘴里无意识地哼起一段小时候听来的、调子简单的童谣,声音很轻,断断续续:“妹妹嫁得好,哥哥有书念,爹娘不愁钱,过年有肉片……”唱到一半,我忽然住了口,像是惊觉失言,慌忙低下头,用力搓着手里一件旧衣的角。堂屋那厚重的蓝布门帘,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
我借着整理衣裳的姿势,眼角余光透过窗纸的一个破洞往里瞥。奶奶果然坐在炕上,正对着父亲说着什么,嘴唇快速地一张一合。父亲低着头,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手指间夹着的烟卷,烟灰积了老长一截,也忘了弹。奶奶说了很久。父亲始终没抬头。最后,他重重叹了口气,把烟蒂摁灭在炕沿那个豁了口的破碗里,声音疲惫:“随您吧……娘,您看着办。只要……只要别耽误了晓强就成。”我手里最后一件衣裳搭上晾衣绳,绳头没系牢,被风吹得轻轻晃荡。堂屋的门帘“哗啦”一声被掀开,奶奶脚步生风地走出来,看也没看我,径直朝院外走去,目标明确,像是要去找某个能敲定这件事的关键人物。
我站在冰凉的井台边,手无意识地攥着身上那件粗布衣的衣角,指尖用力到微微发白。
风从东边吹过来,卷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我望着瞬间空荡下来的堂屋,只剩母亲灶膛里冒出的一缕青烟,歪歪扭扭地升上天空。父亲那句“随您吧”,还在耳边嗡嗡作响。三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把磨钝了的刀,慢慢地、深深地,割裂了某些一直以来勉强维系的东西。我低下头,目光落在自己右手手背上。
那里有一道极淡的旧疤,是前世被张铁柱踹门时飞溅的木屑划伤的。如今,它几乎看不出来了。我抬起手,用袖口用力擦了擦那块皮肤,仿佛这样就能擦去所有过往的印记。院外传来了脚步声,是奶奶回来了。她手里空着,但走路的姿态和节奏全变了,每一步都透着心里揣了事的沉甸甸。她经过我身边时,脚步顿了一下,侧过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不再仅仅是往日那种毫不掩饰的嫌弃和厌烦。那是一种掂量。一种权衡。一种赤裸裸的算计。
她什么也没说,收回目光,一扭头径直进了堂屋,门帘在她身后重重落下,晃了几晃,归于平静。我独自站在冰凉的井台边。风吹过,晾衣绳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
绳上湿透的衣裳还在往下滴水。滴答。滴答。砸在井沿那被磨得光滑的青石板上,碎裂成更细小的水花,转瞬即逝。第3章:利诱贪心,黄昏的嫁妆博弈奶奶从院外回来时,脚步比去时更急、更沉,像是心里那杆秤已经重重落下,砸得她步履生风。她没有再看我,径直掀开堂屋那厚重的蓝布门帘,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手里的烟袋锅子在炕桌角“咚咚”磕了两下,声音沉闷,像是在发泄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躁。
母亲正在西屋角落,俯身在一个旧木箱里翻找。那是她当年出嫁时带来的陪嫁箱,漆面早已斑驳脱落,铜扣也锈得发黑。她将一件件半新不旧的衣裳拿出来,仔细抚平褶皱,再重新叠好,准备收进柜子深处。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声音放得又轻又低,确保堂屋能隐约听见:“娘,晓萌要是真嫁到张家,总得有些像样的东西带过去撑撑场面。
赵家村那边的大户人家最讲究这个,新媳妇要是没点陪嫁,进门头一天给公婆敬茶,怕是都得跪在冷地上。”母亲的手猛地一顿,抬起头来看我,眼里满是慌乱和无措:“这……家里哪还有闲钱置办嫁妆?你奶手里攥得紧,一块新布都舍不得扯,更别说别的了。”我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一件洗得发白、边缘已经磨出毛边的蓝布衫,语气带着几分无奈的提醒:“王婶特意提过,张家相看人家,最看重这些脸面。
张屠户家底厚,要是觉得咱家太寒碜,别说八百块,怕是连谈好的彩礼都能借故压价……”母亲的嘴唇嗫嚅了几下,终究没说出话来,只是手下叠衣服的动作更快、更用力了些,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
堂屋里适时地传来一声清晰的咳嗽声,是奶奶在清嗓子。她果然一直在听着。我慢慢站起身,走到堂屋门口,停在门帘外侧的阴影里,没有进去。“奶。”我开口,声音不大,却足够让屋里那两个人听清楚,“晓萌嫁过去,总得有台缝纫机做嫁衣吧?
不然连身像样的新袄都缝不出来,让人家看了,还以为咱家穷得连台机子都没有,日子都揭不开锅了。”屋里霎时静了一瞬,空气仿佛凝固了。“缝纫机?!
”奶奶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冰冷的怒意,“那是你爹干活吃饭的家伙什!补裤子缝棉袄,全家都指着它!你能动?”我垂下眼睑,像是被这呵斥吓住了,声音变得更弱,带着几分委屈和怯懦:“可是……王婶说了,张家那边最瞧不起不会针线、没点陪嫁的姑娘。
新娘子要是连件衣裳都做不利索,公婆头一个就要嫌弃,连带……连带晓强往后说亲,都要被人看不起,说咱家家风不行。”一直闷头坐在炕沿的父亲,手里捏着那半截自卷的烟卷,闻言终于动了动。烟灰簌簌地掉在他的旧裤子上,他也没去拍,只是慢慢地、极其缓慢地抬起了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极了,里面有挣扎,有疲惫,有对现实深深的无力,但最终,都化作了某种认命般的妥协。他没有出声反对。
奶奶猛地从炕上站起身,烟袋锅子重重地磕在炕沿上,发出刺耳的声响:“你倒是真会算账!
为了个还没进门的外姓人,就想着把家里的根基往外掏?”“我不是为了外姓人。
”我低下头,手指紧张地绞着破旧的衣角,声音却努力保持着平稳,“我是为了这个家想想。
六百块换我去冲喜,家里最后落不下什么。八百块换晓萌,多出整整两百块,够晓强多念一年书。机子给了张家,咱们眼下是少了个物件,可脸面上光彩,妹妹在婆家也能硬气些。”屋里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父亲终于再次开口,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娘……她说的,也不是……全没道理。
”奶奶猛地瞪向他:“你也觉得该给?!”父亲没有抬头迎视她的目光,只是把抽到尽头的烟蒂狠狠地摁灭在炕沿那个豁了口的破碗底,动作缓慢却带着一种决绝:“随您吧……娘。只要……别耽误了晓强就成。”“随您吧”。
这三个字轻飘飘地从父亲嘴里说出来,却像一把重锤,彻底敲定了局面。我知道,事,成了。
奶奶重新坐回炕沿,脸色铁青,枯瘦的手指在烟杆上一下下地敲着,仿佛在精密计算那多出的两百块彩礼和一台缝纫机之间,究竟划不划得来。她心里清楚,一旦换了婚约,张家那边绝不会再提六百块的老黄历。八百块是明码实价,换人顺理成章,可还要再搭上一台缝纫机……她只觉得心肝肉都疼。但她更怕丢脸。
她怕村里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陈家穷酸得连台像样的嫁妆都凑不出,女儿嫁过去连条新裤子都得求人缝。她更怕那眼看就要到手的二百块差价,就这么飞了。
最终,她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咬紧后槽牙,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行!机子给他们!
可这话我得说前头,这事儿,谁要是敢往外传是我点头的,我撕烂她的嘴!”我低着头,恭顺地应了一声“是”,没再多说一个字。转身退回西屋时,我看见晓萌正抱着晓宝站在院子的最角落,拿着小勺给孩子喂水。她显然全都听见了,手里的勺子僵在半空,眼睛直直地盯着堂屋门口,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我走过去,神色自然地从她手里接过咿呀作响的晓宝,轻轻抱在怀里。“妹妹。
”我朝着堂屋方向抬了抬下巴,语气温和得像是在分享一件好事,“以后啊,那台缝纫机就归你用了。给你宝儿缝漂亮小袄,给爹娘做暖和的新衣,好不好?
”她没有接话,只是死死地盯着我,嘴唇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我继续说着,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命都是天定好的。我认了我的命,你也得认你的。
”她猛地抬起头,那双原本总是低垂温顺的眼睛里,骤然涌上一股强烈到几乎要溢出来的恨意,像两把淬了毒的刀子,直直地剜在我脸上,仿佛第一次真正看清我这个姐姐的真面目。那一眼,锋利无比,带着冰冷的寒意。她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猛地伸出手,近乎粗暴地将晓宝从我怀里抢了回去,紧紧抱住,然后转身就走。脚步又急又乱,差点被高低不平的门槛绊倒,但她踉跄了一下,硬是没停,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院角的阴影里。我独自站在原地,看着她决绝的背影消失。风吹过,晾衣绳吱呀呀地晃动,一件没拧干的湿衣裳掉下来,“啪”地一声砸在泥地上。傍晚时分,天边泛着一种沉闷的暗红色。那台沉重的、漆色暗旧的缝纫机被母亲从西屋窗下搬了出来,放在了院子正中央。机身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母亲拿着半湿的抹布,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直到露出些许光亮,最后,她郑重地给机子盖上了一块红布。
那红布是她当年出嫁时盖头的备料,边角早已褪色,但依稀还能看出用金线绣着一对交颈的鸳鸯。奶奶始终坐在堂屋门口的门槛上,手里的烟袋锅就没停过,一下下磕着地面,发出单调而焦躁的“咚咚”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