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世界:我和我的兄弟在异世界(克洛斯特维克托)完结小说推荐_小说全文免费阅读异世界:我和我的兄弟在异世界克洛斯特维克托
杏子林事变十年后,江湖再起惊涛。 一个不会武功的瞎子,手持当年乔峰的折扇,竟令丐帮八大长老跪地痛哭。三十六洞七十二岛主一夜之间尽数归顺灵鹫宫,只因宫主是个穿红肚兜的女童。少林藏经阁频频失窃,守阁僧却只反复念叨:“是他,是他回来了……” 而我,才是这连环局中最后的杀招。---杏子林的雨,冷得像是积了十年的旧怨,淅淅沥沥,敲打着早已腐朽的枯枝和人心。
空气里黏着的是泥腥气,还有一种散不掉的铁锈味,不知是来自当年那场叛乱的残留,还是今夜即将泼洒的热血。林深处有火把燃起,光晕摇曳,勉强撕开浓得化不开的黑暗。
火把围出的空地上,人影幢幢。丐帮残存的八大长老,如今已是江湖上跺跺脚四方乱颤的人物,此刻却个个面色惨白,袍袖无风自动。
他们围成一个半弧,目光死死钉在弧心处的那个人身上。那是个青衫人,很瘦,坐在一张粗糙的木轮椅上,膝上摊着一柄纸扇。他闭着眼,面容在火光下显得异常安静,甚至有些文弱。像个落第的书生,误入了这场江湖豪杰的杀局。但他不是误入。
“阁下究竟是谁?”传功长老吕章的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他内力最深,也最先感受到那无声无息压上心口的巨石,“此物…此物从何而来?”他指的,是青衫人指尖轻轻抚弄的那柄折扇。扇骨微黄,是上了年头的白檀木,扇面却保存得极好,依稀可见墨迹勾勒出的狂放山河,一角盖着个殷红的朱印,印文模糊,但那磅礴的气势,在场的老人们到死都忘不掉。那是乔峰的扇子。当年帮主豪饮时,便好以此扇击节而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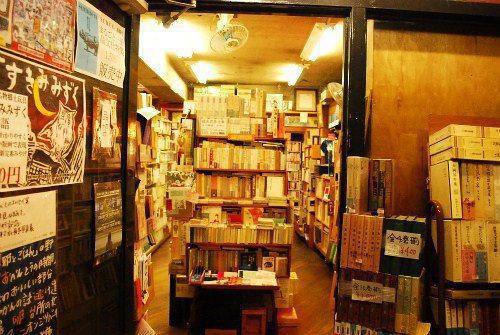
青衫人没回答。他甚至像是没听见吕章的话,只是微微侧着头,仿佛在聆听雨水穿过叶隙的细微声响。他是个瞎子。半晌,他苍白的唇动了动,声音轻飘飘的,却像一根冰冷的针,刺入每个人的耳膜。“十年了,”他说,“杏子林的泥,还没吃够么?”只一句,八大长老身形剧震!当年那场变故,身败名裂,兄弟阋墙,血染黄土……种种不堪与惨痛,如同被这一句话生生从坟墓里刨了出来,暴露在凄风冷雨之下。执法长老白世镜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他想厉声呵斥,想扑上去将这装神弄鬼的瞎子毙于掌下,可他的脚像是被焊在了地上。那瞎子的手指,正轻轻点在那方朱印上。无声的惊雷在所有人心头炸开。忽然,青衫人手腕极轻微地一抖。
嗒。一声极轻微的机括响动,淹没在雨声里。但那柄摊开的折扇,扇骨顶端猛地弹出一截三寸长的寒芒,薄如蝉翼,在火光下流转着一抹幽蓝的诡光。
就像毒蛇的信子。“缚虎手!”吕章失声骇叫,连退三步,仿佛见了鬼魅,“你怎么会……你怎么可能使得了帮主的……”“缚虎手”不是招式,是乔峰独门兵器“折扇藏锋”的机括名,普天下除了乔峰自己,绝无第二人知晓开启之法!
青衫人嘴角似乎向上弯了一下,又似乎没有。那抹幽蓝的锋刃在他指间无声旋转了一圈,又悄无声息地缩回扇骨之内。啪。他合上了扇子。这一声轻响,却如同重锤,狠狠砸在八大长老的心口。噗通——不知是谁第一个软倒,紧接着,噗通声接连响起。
威震江湖的丐帮八大长老,竟对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瞎子,直挺挺地跪了下去。头颅深埋,肩背剧烈颤抖,呜咽声再也压抑不住,混在雨声里,分不清是悔是惧是痛。
他们跪的不是这个瞎子。他们跪的是那柄扇子所代表的如山过往,是那段他们合力逼死却永远无法摆脱的梦魇。青衫人依然安静地坐着,火光在他没有焦距的眸子里跳动,映出一片虚无的冷。“起来吧,”他淡淡地说,声音里听不出丝毫波澜,“旧债,不是跪着就能偿清的。”……与此同时,万里之外,天山缥缈峰。灵鹫宫深处,暖如仲春,异香馥郁。厚厚的波斯地毯吸尽了所有声响,只余下酒液倾倒的潺潺音和粗野放肆的狂笑。七十二岛主、三十六洞主,这些盘踞一方、桀骜不驯的魔头巨擘,此刻竟济济一堂。
只是他们脸上看不到半分平日的嚣张,反而堆满了谄媚、恐惧,以及一种极力压抑的惊疑不定。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大殿正中的那张巨大软椅上。
椅上铺着雪白的熊皮,熊皮上,一个约莫七八岁的女童晃荡着一双白生生的小腿。
她只穿着一件鲜艳夺目的红肚兜,头上梳着两个抓髻,唇红齿白,眼珠乌溜溜的,像个年画里走出来的玉娃娃。她手里正捧着一只比她的脸还大的金杯,里面盛满了紫红色的葡萄美酒。“喝呀!”女童的声音清脆稚嫩,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霸道,“姥姥我这灵鹫宫的美酒,难道还灌不饱你们这些穷酸破落户的肚皮?”一个虬髯大汉,乃是东海狂鲸岛的岛主,闻言猛地站起,脸上横肉抽搐,似乎忍无可忍。他称霸海上,何时受过这等羞辱?
但他刚吐出一个字:“你……”女童忽然咯咯一笑,乌溜溜的眼珠转向他,天真无邪。
也没见她有任何动作,那虬髯大汉突然脸色剧变,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攥住了心脏,额头上青筋暴起,豆大的汗珠瞬间滚落。他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庞大的身躯剧烈地颤抖起来,然后“咚”地一声栽倒在地,蜷缩成一团,痛苦地抽搐。
满殿死寂。落针可闻。女童又捧起金杯,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殷红的酒汁顺着她的嘴角淌下,染红了肚兜,像血。她笑嘻嘻地看着殿内噤若寒蝉的群豪,伸出舌头舔了舔唇边的酒渍。“还有谁想尝尝…忤逆姥姥的滋味呀?
”扑通、扑通……这一次,跪下的是所有岛主洞主。头颅深深叩在地毯上,连大气都不敢喘。
他们怕的不是这女童的武功,而是她身上那件红肚兜隐隐透出的诡异图案,以及一种更深沉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战栗。仿佛眼前这女童,是某个他们早已发誓效忠、却又恐惧了百年的可怕存在的化身。女童看着跪满一地的豪强,笑嘻嘻的眼中,飞快地掠过一丝与她外貌绝不相称的、沧桑而冰冷的漠然。……嵩山,少林寺。藏经阁经历了百年来的又一次失窃。
丢的不是《易筋经》、《洗髓经》那般镇派之宝,而是几本无人问津、落满灰尘的梵文杂经。
值守的僧人被发现时,蜷缩在经架角落,双目圆睁,瞳孔里是无法消散的极致惊恐。
他反复喃喃自语,声音嘶哑破碎,像是被恶鬼掐住了喉咙。
“是他…是他…是他回来了……”方丈玄慈大师亲自前来,以精深内力安抚,那僧人才稍稍回神,却依旧语无伦次。
影子…没有脚步声…经书…自己飞走了……他看了我一眼…冷的…空的……”玄慈眉宇深锁,俯身柔声问:“是谁?你看到了谁?”守阁僧浑身一颤,猛地抓住方丈的衣袖,指甲几乎掐进肉里。他死死盯着前方空无一物的空气,牙齿咯咯作响,用尽全身力气挤出两个字:“…乔…峰……”……江南,听雨楼。我坐在临窗的位置,听着窗外淅沥的雨声,指尖慢慢捻动着一颗温润的棋子。桌上,一张张写着最新江湖消息的纸条摊开着。“丐帮八大长老杏子林夜跪青衣盲客。
”“灵鹫宫重出江湖,红衣女童收服三十六洞七十二岛。”“少林失窃,守阁僧疯癫呓语乔峰之名。”纸条上的墨迹还未干透,散发着淡淡的腥气。我提起笔,在一张空白的纸条上缓缓写下一行字。字迹清瘦,却力透纸背。消息是该传出去了。棋局,已经布好。该动的棋子,也都动了。现在,只差最后一步。我端起酒杯,浅浅啜了一口。
酒是上好的花雕,温得恰到好处,却暖不了这江湖深处的寒意。窗外雨声渐密,敲打着青石板路,也敲打着这迷雾重重的武林。谁都是棋子。而我,才是那只藏在最后、推动所有棋子、决定胜负的——那只手。杀招,从来不在明处。
窗外雨声未歇,敲在青石板上,一声声,冷而碎。听雨楼的酒,温到第三遍,香气就淡了。
我指尖的棋子落下,敲在楠木棋枰上,一声轻响,却似比窗外的雨更沉。楼板响起脚步声,很轻,像猫。但每一步的距离,分毫不差。来人停在雅间门外,呼吸声几不可闻。“进。
”我吐出一个字。门被无声推开。一个穿着灰色劲装的汉子闪身而入,浑身湿透,水珠从发梢滴落,他却像毫无所觉。他脸上没有任何特征,是那种扔进人海立刻就会消失的长相。只有一双眼睛,死寂,冰冷,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
他是我的一枚棋子。负责传递最紧要消息的那一枚。他没有说话,只是从贴肉处取出一张薄如蝉翼的油纸,双手奉上。油纸被体温烘得微暖,边缘已被雨水浸得有些模糊。我接过,展开。上面的字迹潦草,显然是在极度仓促或紧张的情况下写就。“盲者入丐帮总舵,如入无人之境。
八长老奉若神明,闭门密议至今未出。”“灵鹫宫红衣女童下令,三十六洞七十二岛精锐尽出,动向不明,似往中原。”“少林玄慈方丈深夜叩关,请出扫地老僧。后山佛塔,时有异光闪动。”消息很短,却足够重。
油纸在我指尖无声化为细屑,簌簌落下。该来的,都动了。比预想的更快,更急。那瞎子,那女童,还有少林寺里那若有若无的“鬼影”……他们都在把这潭水搅得更浑。但这浑水,本就是我想要的。我抬手,灰衣人躬身,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融入门外的雨幕,仿佛从未出现过。我又拈起一枚棋子。黑色的。棋局之上,黑白交错,杀机四伏。
可真正的杀招,往往藏在棋枰之外。就像现在。我起身,走到窗边。雨丝斜织,将远处的屋舍、河堤都笼在一片朦胧里。江南的雨,总是这般缠绵,带着几分阴柔的杀意。
街道尽头,出现了一个人影。蓑衣,斗笠,身形佝偻,像个最寻常不过的老渔夫,沿着湿漉漉的石板路慢慢走来。但他的脚步很稳,每一步踏下,积水却不见丝毫晃动。
他低着头,斗笠压得很低,看不清面容。可我知道他是谁。他也是一枚棋子。一枚很久以前,就该废掉的棋子。他越走越近,最终停在听雨楼下。然后,他抬起头。斗笠下,是一张布满刀疤的脸,狰狞可怖。唯有一双眼睛,锐利得像鹰,穿透雨幕,精准地锁定了站在窗口的我。他没有说话,只是抬起手,慢慢扯开了蓑衣的衣襟。里面,不是粗布麻衣,而是一袭锦绣官袍!袍服上绣着的獬豸图案,在灰蒙蒙的雨色中,刺眼得令人心寒。皇城司!他咧嘴,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然后伸出手指,对我勾了勾。挑衅。亦是命令。我看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心里却像有一面冰湖骤然裂开,寒意汹涌。皇城司的狗,鼻子果然灵。竟然嗅到了这里。
但他们嗅到的,是我故意让他们嗅到的。我转身,下楼。楼梯吱呀作响。
掌柜和小二缩在柜台后,大气不敢出,他们显然也看到了楼下那人的官袍。我推开门,走到街上。雨丝立刻打湿了我的衣衫。那皇城司的探子就站在我对面,相隔不过五步。
雨水顺着他脸上的沟壑流淌。“阁下真是让我好找。”他的声音沙哑,像砂轮磨过铁器。
“找我何事?”我问。“请你去看一场戏。”他盯着我,“一场大戏。”“什么戏?
”“杏子林里,旧主归来。灵鹫宫前,群魔乱舞。少林寺中,佛影魔踪。”他慢慢说着,鹰隼般的眼睛一眨不眨,“这戏台子搭得太大,角儿也太邪乎。朝廷,想找个明白人,问问这唱得到底是哪一出。”“为何找我?”“因为有人说,”他向前逼近一步,身上的水汽混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扑面而来,“你才是那个写戏本的人。”雨更密了。
街上空无一人,只有雨水冲刷着世界,仿佛要洗净所有阴谋和痕迹。我沉默了一下,然后轻轻笑了。“好。”我只说了一个字。探子似乎有些意外我的爽快,眼神里的警惕又深了几分。“那就请吧。”他侧身,做出一个“请”的手势。街道另一头,一辆毫不起眼的黑色马车不知何时停在了那里,车帘低垂,像一口沉默的棺材。我走向马车。
经过他身边时,我的脚步似乎微微踉跄了一下,袖袍拂过他被雨水打湿的官袍。
他身体瞬间绷紧,像一头蓄势待发的豹子,内力暗涌。但我只是扶了一下自己的额头,歉然道:“雨大,滑了一下。”他死死盯着我,数息之后,才慢慢放松下来,眼神中的疑云却更重。我掀开车帘,钻了进去。马车内部很宽敞,也很暗,散发着皮革和霉味混合的气息。探子也跟着坐了进来,就坐在我对面。马车缓缓启动,车轮碾过石板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车厢微微摇晃。我们相对无言。
只有雨点敲打车顶的单调声响。他在观察我,每一个细微的表情,每一次呼吸的频率,都不放过。我闭上眼,像是养神。马车没有驶向城外的杏子林,也没有去往官衙,而是在城内兜了一圈后,钻进了一条僻静的巷子,停在了一处不起眼的小院门前。“下车。
”探子冷冷道。我跟着他走进小院。院子很小,只有一间正屋,门关着。探子走到屋门前,却不推开,而是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无比,有嘲讽,有怜悯,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写戏本的人,”他哑声道,“往往死在自己写的戏里。”说完,他猛地推开了屋门。屋内的景象,让我的瞳孔骤然收缩。屋里有人。不止一个。
正中的椅子上,坐着一个青衫人,闭着眼,膝上摊着一柄纸扇。
是那个本该在丐帮总舵的瞎子!而他身侧,站着一个红衣女童,正笑嘻嘻地把玩着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乌溜溜的眼珠转着,落在我身上。角落里,一个阴影蠕动,缓缓现出一个穿着少林僧衣的身影,光头上有戒疤,面容却模糊不清,只有一双眼睛,空洞得吓人。瞎子、女童、少林僧!这三个搅得整个江湖天翻地覆的人,竟然同时出现在这皇城司的秘密据点!不,不对。我立刻察觉到了异样。那瞎子太过安静,安静得像一尊雕塑。那女童的笑容僵硬在脸上,眼神深处藏着一丝无法掩饰的惊惶。
那少林僧,身体在微微发抖。他们不是自愿来的。他们是棋子,也是囚徒。真正下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