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玉镇冥棺燕青霄监天司免费小说完结_最新章节列表血玉镇冥棺(燕青霄监天司)
一、夕阳小区的老楼,墙皮掉得东一块西一块的,好像出现了斑秃,露出底下黄不拉几的底色。年已八旬的邱伟兰就住这儿,她走起路来,背驼得像开春没晒透的老柳树条子,腰杆儿咋也直不起来。邻居们看到,只要是天刚一暖和,准能瞅见她搬个小马扎,往楼下小广场的石凳上一坐,跟几个老姐妹唠得热火朝天。
她嘴里总挂着句话:“趁着还能喘口气儿,就把自己的底子都给孩子吧,那才叫实打实的好!
总比一闭了眼留着钱,比他们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连亲情都争没了强!
”这话说得糙但理不糙,老姐妹们一唠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都纷纷点头认可,还说伟兰这老太太活得通透,比那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强多了。可谁能想到,真到事儿上,邱伟兰自己却犯了让她后悔的糊涂事,那后悔的劲儿,比吃了黄连还苦呢。
邱伟兰的老伴走得早,三十多岁就守了寡,这辈子最大的功劳就是拉扯大了俩儿子一个闺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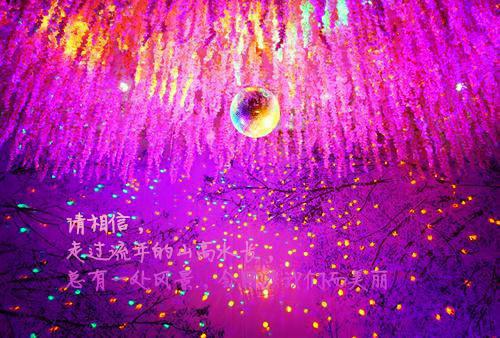
虽然手心手背都是肉,可三个孩子的性子咋差得老远了,就像一个锅里炖出来的不同的菜。
大儿子打小就木讷,跟妈说话都脸红,嘴笨得像被浆糊糊住了,一句甜言蜜语都不会说。
有一次邱伟兰过生日,大儿子拎着二斤桃酥来,坐了半天就说了句 “妈,吃”,气得邱伟兰当时就想把桃酥扔他脸上,可瞅着儿子那局促的样儿,又把火憋回去了。
大儿媳也是个实在人,过日子是把好手,蒸馒头揉面能把盆擦得锃亮,连盆底的面疙瘩都抠得干干净净。去老太太家串门,只会干坐着帮着择菜、洗碗,从来不会说“妈您辛苦了”“妈您歇着”的客套话,可碗柜里的脏碗碟,她准能一古脑地洗得干干净净。有一次邱伟兰崴了脚,大儿媳天天来照顾她,又是擦药又是炖汤,话不多,可那股实在劲儿,比啥都实诚。闺女呢,跟她妈的脾气就不对付,俩人一说事儿总急,一句话没说到一块儿就能拌起嘴来。
后来闺女嫁去了邻县,一年到头也懒得回来看一两趟,平时电话都少得可怜,比那远房亲戚还生分。有一次邱伟兰重感冒,咳嗽得肺都快咳出来了,想让闺女来搭把手,闺女在电话里说“店里忙走不开”,那语气像是在应付外人,挂了电话,老太太对着老伴的照片抹了好半天的眼泪。唯独小儿子,打小就会来事,小时候跟在邱伟兰屁股后面,一会儿“妈我帮您拿碗”,一会儿“妈我给您捶背”,嘴甜得像抹了蜜,能把邱伟兰哄得眉开眼笑。长大了更是,逢年过节准提着老太太爱吃的槽子糕、软麻花回家,那槽子糕还冒着热气,香得能勾着人肚子里的馋虫。坐下来就唠老太太爱听的嗑:“妈您这发型显年轻,比楼下张婶看着小五岁!”“妈您做的酸菜比饭馆里的香,我一想这口就得流口水!
”这哄得老太太心里暖洋洋的,浑身的骨头缝儿都舒坦,比泡了东北的大澡堂里还得劲儿。
尤其是小儿媳,那嘴更是甜得能滴出蜜来,比那卖糖人的还会说。
每次来都一口一个“妈”叫着,进门就抢着干活,擦桌子能把桌腿都擦一遍,连桌腿缝儿的灰都抠出来;拖地能把墙角的灰都蹭干净。还会给老太太剪指甲,剪完了用小错磨得溜光,摸着手心都舒服。临走还不忘说句 “妈您别累着,有事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跟小伟随叫随到!” 这话说得邱伟兰心里像开了朵牡丹花,美得不行,她也总爱跟老姐妹们念叨:“还是小儿媳妇贴心,比亲闺女还亲!”去年开春,邱伟兰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拆迁,拆迁办的人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一算下来,拆迁款能得六十多万。钱到手那天,邱伟兰揣着银行卡,手都有点抖,活了一辈子,哪儿见过这么多钱啊!可她坐在床上一琢磨,三个孩子平分,每个孩子都给点,自己再留个十万八万块的养老,平时买个药、割块肉,也就够了。可没等她琢磨好,小儿媳就找上门来了。那天是周末,天刚蒙蒙亮,外面还飘着点雾,小儿媳就提着一兜通红的草莓来了,看着就新鲜。一进门她就拉着邱伟兰的手,脸上笑盈盈的,可眼里却藏着点急切,像有啥话堵在嗓子眼,不吐不快。“妈,这回动迁了,您也没地方住了,就跟我们一起过吧,省得一个人孤单。”她又给老太太倒了杯热水,那水温度正好,双手递过去,才慢笑悠悠地开口:“您看您小儿子,上班挤公交都挤了五六年了,冬天冻得手通红,跟胡萝卜似的;夏天汗流得能湿透衬衫,那汗味儿老熏人了。他单位同事都开上小汽车,就他天天挤公交,人家都背后笑话他呢,说他没本事。还有您孙子,今年上高三了,想考个985大学,人家同学都找名师辅导呢,一节课就好几百,我也不想委屈了孩子不是?”她说着,就往邱伟兰身边凑了凑,声音放得更软了,能让人心里感到温馨:“妈,您也知道,我们俩工资不高,每个月还着房贷,那房贷压得人喘不过气,实在没多余的钱。您这拆迁款,能不能多给我们点?等以后我们日子好了,肯定好好孝敬您,带您去全国各地旅游!
”一边说,一边轻轻地帮邱伟兰捋了捋额前的碎发,那眼神眼可怜巴巴的,看得邱伟兰心里直心痛。邱伟兰本来就偏爱小儿子,再被小儿媳这么一哄、一求,心里的天秤就歪了,她一想到小儿子挤在公交里,被人推来搡去的样子,想起孙子趴在台灯下,埋头写作业的背影,心也不是个滋味,她心一软,拍了板:“行!
妈知道你们难,这钱妈多给你们点!”当天下午,邱伟兰就跟着小儿子去了银行。
银行里人多,闹哄哄的,柜台里的小姑娘把银行卡插进机器,“嘀”的一声,四十万就转到了小儿子的卡上。邱伟兰看着小票上的数字,心里有点空落落的,像少了点啥,可一想到小儿子能买汽车,孙子能找名师,又觉得值了。二、这事儿就像窗户纸,没几天就被人捅破了,大儿子和闺女那边全知道了。头一个找上门的是大儿子,那天他一下班连家都没回,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破自行车,直接就奔了邱伟兰现在住的小儿子家。一进门也不说话,闷着头往沙发上一坐,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抖抖索索抽出一根,火柴“噌”地划亮,接着就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卷烧得快,烟灰簌簌往下掉,落在裤腿上也不管。
满屋子的烟味呛得人嗓子发紧,连窗台上那盆绿萝都好像蔫头耷脑了。
邱伟兰看着大儿子紧绷的侧脸,颧骨上的胡茬没刮干净,泛着青黑,心里也明白了他这是为了啥事来的。想开口说句软话,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知道,这事儿是自己理亏,可话到嘴边,又硬气不起来,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偏了哪头都心疼。
直到一整包烟都抽完了,烟蒂在烟灰缸里堆得像座小山,看着就让人堵心。
刚进门口的大儿媳看到这个场面,便偷偷踢了大儿子一脚,她是丈夫来之前打电话叫过来的,也是怕丈夫嘴笨,三句话说不过老太太,反倒憋一肚子气。
大儿子这才慢吞吞地把最后一个烟蒂摁灭,用得那劲头大得像是要把满腔的委屈都摁进去。
他抬起头,血丝爬满了眼白,憋了半天,每说一个字都费劲:“妈,不是我贪心,这钱是老房子拆迁的,是您跟我爸一辈子攒下的血汗钱,三个孩子,咋也得一碗水端平啊!
您一下给了小弟四十万,我和妹妹啥都没有,这事儿说出去,街坊邻居不得对你说三道四?
”他话音刚落,大儿媳的眼圈也唰地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强忍着没掉下来。“妈,”她声音哽咽着,话里带着委屈,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们平时是不会说好听的,嘴笨,可您不能忘了啊!前年您急性阑尾炎住院,是谁天天早上五点就起来熬小米粥,怕粥凉了,用棉垫子裹着保温桶往医院送?是谁晚上在医院陪床,您起夜不方便,是我给您擦身子、倒尿盆?您是不是偏心啊?”邱伟兰被大儿媳问得脸上发烫,像被三伏天的太阳晒透的红薯,从里到外都热得慌,可嘴上还硬撑着,“你小弟他们日子难,小伟挤公交遭罪,冬天冻得手都握不住扶手,孙子要考大学,得多花钱补习,我帮衬帮衬咋了?你们俩口子都有工作,一个月挣得不少,也不缺这点钱!
”“我们日子好些,也是自己一分一分挣的!”大儿媳急了,声音也拔高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妈,这不是钱的事儿!是您的心偏得太狠了,寒了我们的心啊!
”俩人正吵着,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了,那力量有些大,门框都晃了晃。
只见闺女和女婿拎着包闯了进来,包上的拉链都没拉好,露出里面的纸巾盒。
原来老人的闺女一听说妈把拆迁款都给了小弟,气就不打一处来,立马接上女婿开车往这儿赶,一路上嘴就没停过,把邱伟兰数落了一路,说她老糊涂了,眼里只有小儿子。一进门看见屋里这架势,烟味没散,大儿媳在抹眼泪,大儿子红着眼,这时闺女的火“噌”地就上来了,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没等邱伟兰开口,就喊起来:“妈,我不是您亲生的啊?拆迁款凭啥都给小弟?我和大哥就不该得一点吗?您总说小弟贴心,可我们再不好,也是您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当年我出嫁,您就给了两床被子,我啥也没说,现在连拆迁款的影子都见不着,您这心也太偏了吧!”女婿站在闺女身后,脸色沉得像锅底,虽然没说话,可那眼神里也充满了不满,让邱伟兰看了心里发怵。女婿平时对邱伟兰挺客气,逢年过节也会拎着酒来,酒还是挺贵的牌子,可今儿个,连招呼都没打,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跟没看见邱伟兰似的。邱伟兰被四个孩子围着,像被围在中间的猎物,心里又急又气,一股子犟脾气也上来了,那是她年轻时就有的性子,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她拍着大腿喊,声音都变了调:“我的钱!我想给谁就给谁!你们小弟困难,我帮他怎么了?
你们就不能让着点他?你们是怎么当哥当姐的?”“妈,您这是不讲理!”大儿子也急了,猛地一拍桌子,茶杯都震得跳了起来,“您这么做,以后这个家还咋相处?
兄弟姊妹还咋来往?”“不处就不处!”邱伟兰脖子一梗,也来了劲,跟大儿子较上了劲,“我的钱我做主,不用你们管!你们爱来不来,我不稀罕!”这话像根导火索,彻底把孩子们惹恼了。大儿子“啪”地又拍了下桌子,站起来就往外走,脚步蹬蹬响,走到门口还撂下一句:“以后我再也不来了!您就跟小弟过去吧!
” 大儿媳也马上跟着站起来,狠狠瞪了邱伟兰一眼,那眼神里满是失望,转身就追了出去。
闺女抹着眼泪,对邱伟兰说:“妈,您太让人失望了,以后您有事,也别找我了!”说完,也拉着女婿摔门而去,那门“砰”地一声关上,震得墙上的日历都掉了下来。
随着门“砰”被狠狠地地关上,瞬间屋里立刻静了下来,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在数着邱伟兰的心跳,每一声都那么清晰,那么沉重。她坐在沙发上,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刚才的火气一下子就泄了,像被扎破的气球,心里又气又悔,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皱纹往下流,流过嘴角,咸涩的味道钻进嘴里,比吃了苦胆还难受。她抬手抹了把脸,手上全是泪,冰凉冰凉的,嘴里喃喃地说:“我这是咋了?明明是为了小儿子好,咋就把其他孩子都得罪了?
”三、打那以后,大儿子一家是真没再登过邱伟兰的门,过年过节连个电话都没有,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彻底没了影。闺女那边更绝,手机犹如掐了线的电灯似的,再也没响过,连个拜年的短信都没有。邱伟兰还是天天搬着小马扎,坐在楼下小广场的石凳上,可再也没心思跟老姐妹们唠嗑了。她就那么愣愣地坐着,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挽着老人的胳膊,要么去早市买刚炸好的油条,要么去公园遛弯,说说笑笑的。此刻,她心里就像被针扎了,真的疼得慌。她这时才后知后觉地明白,自己当初那步棋,走得有多糊涂,就像寒冬里踩错了冰面,“咔嚓” 一声掉进了冰窟窿,惊恐地看到冰水没到脖子,却连个拉自己一把的人都没有。住在小儿子家里头,邱伟兰头两三个月倒是觉得还挺热乎,早上一睁眼,小儿媳准把热豆浆端到跟前,还卧个荷包蛋,蛋黄流心,香得能勾着人肚子里的馋虫。晚上看电视,小儿媳会凑过来,胳膊搭在沙发扶手上,软乎乎地问:“妈,要不要吃点夜宵?我煮碗疙瘩汤给您,放俩西红柿,酸溜溜的开胃。
”就连邱伟兰换下来的旧衣裳,小儿媳都抢着拿去洗。这时的邱伟兰心里头熨帖,跟老姐妹们打电话的次数也多了,话里话外还念叨:“还是小儿子家贴心,这钱没白给,值当!比那俩没良心的强多了!”可没成想,等邱伟兰手头那十万块零花钱不再出手花了,看看再也抠不出啥油水了,给孙子买辅导资料的钱没了,给小两口贴补家用的钱也不见了,小儿媳的脸就跟六月的天似的,说变就变,前一秒还晴着呢,下一秒就阴云密布。先是做饭。
以前邱伟兰说句 “今天菜有点淡”,小儿媳立马就笑盈盈地应:“下次多放勺盐,妈您爱吃咸口的我记着呐!”后来倒好,邱伟兰刚小声说句“这菜咸了点”,小儿媳“啪”地就把就把筷子摔在饭桌上,那声音脆得像摔了个碗,“咸了?
嫌咸您自己做啊!我天天上班累得跟孙子似的,回家还得伺候您,您倒好,挑三拣四的,真把自己当老佛爷了?我们家可没那条件专门供着您!”再后来,连邱伟兰起早都成了错。
邱伟兰一辈子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天刚蒙蒙亮,外面还黑着,就起来收拾屋子,擦桌子、扫地面,尽量轻手轻脚的,生怕吵醒小两口。可小儿媳还是能听见动静,在卧室里扯着嗓子嚷嚷:“大清早的瞎折腾啥?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您睡不着就出去溜达溜达,别在屋里瞎晃悠!”话里话外全是刺,指桑骂槐更是家常便饭。
一会儿说 “有些人吃白饭不干活,净占着地方,跟个摆设似的”,一会儿说 “有些人光会添麻烦,不如回老家待着,省得在这儿碍眼”,明着暗着都在说邱伟兰。邱伟兰心里头委屈,像堵了团湿棉花,可也不敢多说啥,毕竟是住在人家里,吃人家的饭,喝人家的水,寄人篱下的滋味,比吃了黄连还苦。
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咽得心口发疼。直到有一回,邱伟兰忙着擦柜子,忘了把门口的垃圾袋提下去。那垃圾袋里装着剩菜剩饭,都有点发馊了,散着股怪味儿。
小儿媳下班回来一看见,当时就炸了毛,指着门口的垃圾,冲邱伟兰拍着桌子嚷嚷:“你个老东西!连扔个垃圾都记不住,你说你留着有啥用?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咋让你跟我们一起过!”那声音大得,隔壁邻居家的狗都跟着叫,“汪汪”的。邱伟兰的脸“唰”地就红了,从脸颊红到耳根,站在那儿,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差点掉下来,可她还是强忍着。再看小儿子,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手机,就是吭都不敢吭一声,连个屁都不敢放。邱伟兰瞅着他,心里头一下就凉了半截,这可是自己疼了一辈子的小儿子啊!小时候把他揣在怀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有块糖都先给他吃,自己舍不得尝一口;他小时候生病,自己抱着他跑了好几里地去看医生,鞋都跑掉了一只。现在看着媳妇这么骂自己,连句公道话都不敢说,这养的哪是儿子,简直是个白眼狼!因为小儿子没拦着媳妇的不满,没过几天,小儿媳干脆连装都不装了,脸上的嫌弃都快溢出来了。
那天邱伟兰从外面溜达回来,刚走到单元楼门口,就看见自己的行李被扔在门口的一个旧拉车里。小儿媳叉着腰站在旁边,脸拉得老长,恶狠狠地说:“你赶紧走!别在这儿碍眼了!我们家可养不起你这尊大佛,吃得多干得少,还净挑毛病!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闹心一天!”邱伟兰站在门口,气得浑身直打哆嗦。
眼泪噼里啪啦地掉在地上。她看着小儿媳那张凶巴巴的脸,又看看躲在屋里,连门都不敢开的小儿子,心里头像被无数根针扎着,疼得喘不过气。
她嘴里不停地念叨:“白眼狼啊!真是白眼狼!我当初咋就瞎了眼,把四十万都给你们了啊!
我真是老糊涂了,老糊涂了!”可不管她咋说,小儿媳就是不松口,最后还推了她一把,那力气不小,邱伟兰差点没站稳,踉跄了一下才扶住墙。“赶紧走!别在这儿耽误我做饭!
”邱伟兰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拄着拐杖,拉着那辆吱呀响的旧车,一步一挪地走出单元楼。
那车轱辘不好使,走起来“嘎吱嘎吱”响,像是在哭。街上人来人往,汽车喇叭声、小贩叫卖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可她觉得自己像个孤魂野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