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间,路漫漫(守仁秀兰)小说全文免费阅读_无弹窗全文免费阅读在心间,路漫漫(守仁秀兰)
时间: 2025-09-13 06:49:46
黑暗浓稠得像泼翻了的墨,严严实实地糊在窗纸上。
村子里最后几声狗吠也歇了,只剩下秋虫不知疲倦的嘶鸣,一声接一声,锲而不舍地钻进低矮的土坯房。
陈守仁僵坐在炕沿,离那团浓烈的红色远远的。
煤油灯早己吹熄,可那大红喜被似乎自身能发光,或者说,它那种喧闹的、不容置疑的存在感,在他眼底烙下了印记,即使紧闭着眼,也能清晰地“看”见那对鸳鸯,那朵牡丹,那个刺眼的囍字。
也听得见另一个细微的、几乎要被虫鸣盖过的呼吸声,来自炕的另一头。
李秀兰。
他的新媳妇。
此刻,她和他一样,穿着浆洗得发硬的新衣裳,蜷缩在炕的另一边,紧挨着冰冷的土墙,中间隔着足足一臂宽的距离,以及那床烫人眼睛的喜被。
空气凝滞了,带着一股土腥味、新棉布的浆味,还有两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混杂着紧张和汗味的陌生气息。
这小小的、原本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空间,被彻底侵占了。
每一种细微的声响都被无限放大——她轻轻吞咽口水的声音,布料摩擦的窸窣声,甚至她极力压抑着的、细微的颤抖。
守仁觉得喉咙发干,像被沙砾磨过。
他想说点什么,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
嘴巴张了几次,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能说什么呢?
问“你冷不冷”?
这初秋的夜,还没到冷的时候。
问“你饿不饿”?
晚上那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谁都吃不饱。
问“你怕不怕”?
他自己心里都揣着只兔子,七上八下。
最终,他只是更紧地攥住了自己的裤腿,粗糙的布料硌着手心。
秀兰似乎动了一下,极其轻微,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然后,是一声极力压抑的、细碎的抽噎。
像针尖,猛地刺破了这凝固的夜。
守仁浑身一僵。
那哭声很小,断断续续,带着一种绝望的隐忍,仿佛声音的主人正用尽全力把它闷回胸腔里。
但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在这咫尺之间,清晰得可怕。
他猛地想起白天。
她娘家送亲的人走后,娘把她拉到里屋,低低地嘱咐了很久。
他隐约听见几句“……伺候好男人……早点添丁……忍着点……都是这么过来的……”秀兰始终低着头,手指死死抠着一个褪了色的蓝布包袱,那里面是她的全部嫁妆,几件旧衣服,还有一双新做的布鞋。
此刻,那包袱就放在炕脚的那个破木箱上,像一个沉默的、灰扑扑的注解。
她的哭声细弱,却带着钩子,勾得守仁心里一阵阵发紧,发涩,还有一种莫名的烦躁。
他不是恼她哭,而是恼这逼得人想哭的局面。
一担稻谷,一床新被,两个几乎陌生的人,就要绑在一起过一辈子了。
这道理,天经地义,村里祖祖辈辈都这样。
可落到自己身上,怎么就那么……硌得慌?
他又想起爹蹲在门槛上抽烟的背影,沉默得像块石头。
想起娘眼角深刻的皱纹和偶尔出神的目光。
日子就是这样,沉重地压下来,容不得人多想,只能埋头往前拱。
炕席很硬,硌得他骨头疼。
但他不敢翻身,怕一动,那本就脆弱不堪的平衡就被打破了。
时间一点点爬过去,窗外的虫鸣似乎也倦了,稀疏下来。
秀兰的哭声渐渐低下去,变成偶尔一声压抑不住的抽气,最后,只剩下极力放缓的、试图装作睡着的呼吸声。
守仁终于极其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动了一下己经发麻的腿。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阵极其细微的、金属搭扣弹开又合上的轻响。
声音来自秀兰那边。
他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屏住了呼吸。
窸窸窣窣的布料声。
她似乎从贴身的什么地方,摸出了一个小东西。
然后,是极轻的、指甲划过坑洼地面的声音。
她在藏东西。
守仁的心跳得更快了。
是什么?
他脑子里闪过无数念头,最后定格在娘塞给秀兰包袱时,低声叮嘱的那句“……贴身放好,别让人瞧见……往后应急……”难道……是钱?
或者……更金贵的东西?
一种被防备、被当作外人的刺痛感,夹杂着好奇,让他喉咙更加干涩。
他几乎想立刻坐起来,问个明白。
但最终,他还是死死忍住了。
问了又如何?
那是她从娘家带来的,或许是她最后一点念想和倚仗。
他有什么资格去问?
那细微的声响停止了。
一切又归于沉寂,只有两人似乎都刻意放得又轻又缓的呼吸声,在黑暗里交错,却泾渭分明。
后半夜,起了风。
风从门缝、窗隙里钻进来,带着深秋的凉意,吹得糊窗的旧报纸噗噗作响。
守仁感觉到身边的被子动了一下。
然后是极轻微的颤抖。
秀兰似乎冷得缩成了一团,牙齿轻轻磕碰的声音隐约可闻。
他盯着屋顶模糊的黑暗,那里结着陈年的蛛网。
僵持了不知多久,他喉结滚动了一下,像是下定了极大的决心,猛地伸出手,抓住了那床隔在中间的红喜被的一角,用力一扯!
绸缎面冰凉滑腻的触感掠过他的手背。
他将被子大部分甩到了秀兰那边,动作粗鲁,甚至带着点赌气的意味,然后迅速收回手,重新紧紧闭上眼睛,背对着她,把自己缩回到炕沿边,仿佛刚才那个动作耗尽了他全部的勇气。
另一边的颤抖停顿了一瞬。
黑暗中,只听得见风呜呜地吹。
过了很久,很久,久到守仁几乎以为天永远不会亮了,他才听到极其细微的、布料摩擦的声音。
她似乎犹豫着,最终,还是把温暖的被子裹紧了些。
那床鲜红的、绣着鸳鸯的喜被,终于盖在了两个人的身上。
虽然,一个紧贴着墙,一个悬在炕边,中间依然隔着无法跨越的、冰冷的距离。
守仁睁着眼,首到窗户纸透出第一丝极其微弱的、属于黎明的青灰色。
那枚被藏起来的东西,像一根小小的刺,扎进了这个新婚之夜,也扎进了他刚刚开始的、名为“丈夫”的人生里。
而身边那个陌生女子均匀却依然带着戒备的呼吸声,告诉他,这条叫做“日子”的路,才刚刚抬起脚,前面漫长得很,也模糊得很。
泥土墙沉默地立着,见证着这一切。
村子里最后几声狗吠也歇了,只剩下秋虫不知疲倦的嘶鸣,一声接一声,锲而不舍地钻进低矮的土坯房。
陈守仁僵坐在炕沿,离那团浓烈的红色远远的。
煤油灯早己吹熄,可那大红喜被似乎自身能发光,或者说,它那种喧闹的、不容置疑的存在感,在他眼底烙下了印记,即使紧闭着眼,也能清晰地“看”见那对鸳鸯,那朵牡丹,那个刺眼的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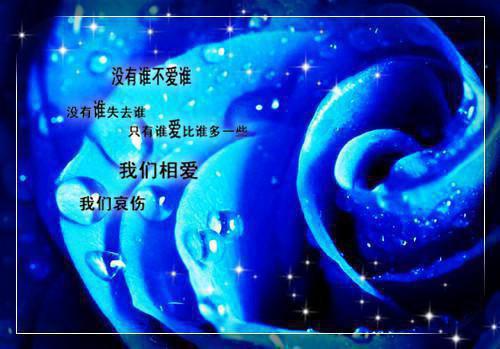
也听得见另一个细微的、几乎要被虫鸣盖过的呼吸声,来自炕的另一头。
李秀兰。
他的新媳妇。
此刻,她和他一样,穿着浆洗得发硬的新衣裳,蜷缩在炕的另一边,紧挨着冰冷的土墙,中间隔着足足一臂宽的距离,以及那床烫人眼睛的喜被。
空气凝滞了,带着一股土腥味、新棉布的浆味,还有两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混杂着紧张和汗味的陌生气息。
这小小的、原本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空间,被彻底侵占了。
每一种细微的声响都被无限放大——她轻轻吞咽口水的声音,布料摩擦的窸窣声,甚至她极力压抑着的、细微的颤抖。
守仁觉得喉咙发干,像被沙砾磨过。
他想说点什么,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
嘴巴张了几次,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能说什么呢?
问“你冷不冷”?
这初秋的夜,还没到冷的时候。
问“你饿不饿”?
晚上那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谁都吃不饱。
问“你怕不怕”?
他自己心里都揣着只兔子,七上八下。
最终,他只是更紧地攥住了自己的裤腿,粗糙的布料硌着手心。
秀兰似乎动了一下,极其轻微,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然后,是一声极力压抑的、细碎的抽噎。
像针尖,猛地刺破了这凝固的夜。
守仁浑身一僵。
那哭声很小,断断续续,带着一种绝望的隐忍,仿佛声音的主人正用尽全力把它闷回胸腔里。
但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在这咫尺之间,清晰得可怕。
他猛地想起白天。
她娘家送亲的人走后,娘把她拉到里屋,低低地嘱咐了很久。
他隐约听见几句“……伺候好男人……早点添丁……忍着点……都是这么过来的……”秀兰始终低着头,手指死死抠着一个褪了色的蓝布包袱,那里面是她的全部嫁妆,几件旧衣服,还有一双新做的布鞋。
此刻,那包袱就放在炕脚的那个破木箱上,像一个沉默的、灰扑扑的注解。
她的哭声细弱,却带着钩子,勾得守仁心里一阵阵发紧,发涩,还有一种莫名的烦躁。
他不是恼她哭,而是恼这逼得人想哭的局面。
一担稻谷,一床新被,两个几乎陌生的人,就要绑在一起过一辈子了。
这道理,天经地义,村里祖祖辈辈都这样。
可落到自己身上,怎么就那么……硌得慌?
他又想起爹蹲在门槛上抽烟的背影,沉默得像块石头。
想起娘眼角深刻的皱纹和偶尔出神的目光。
日子就是这样,沉重地压下来,容不得人多想,只能埋头往前拱。
炕席很硬,硌得他骨头疼。
但他不敢翻身,怕一动,那本就脆弱不堪的平衡就被打破了。
时间一点点爬过去,窗外的虫鸣似乎也倦了,稀疏下来。
秀兰的哭声渐渐低下去,变成偶尔一声压抑不住的抽气,最后,只剩下极力放缓的、试图装作睡着的呼吸声。
守仁终于极其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动了一下己经发麻的腿。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阵极其细微的、金属搭扣弹开又合上的轻响。
声音来自秀兰那边。
他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屏住了呼吸。
窸窸窣窣的布料声。
她似乎从贴身的什么地方,摸出了一个小东西。
然后,是极轻的、指甲划过坑洼地面的声音。
她在藏东西。
守仁的心跳得更快了。
是什么?
他脑子里闪过无数念头,最后定格在娘塞给秀兰包袱时,低声叮嘱的那句“……贴身放好,别让人瞧见……往后应急……”难道……是钱?
或者……更金贵的东西?
一种被防备、被当作外人的刺痛感,夹杂着好奇,让他喉咙更加干涩。
他几乎想立刻坐起来,问个明白。
但最终,他还是死死忍住了。
问了又如何?
那是她从娘家带来的,或许是她最后一点念想和倚仗。
他有什么资格去问?
那细微的声响停止了。
一切又归于沉寂,只有两人似乎都刻意放得又轻又缓的呼吸声,在黑暗里交错,却泾渭分明。
后半夜,起了风。
风从门缝、窗隙里钻进来,带着深秋的凉意,吹得糊窗的旧报纸噗噗作响。
守仁感觉到身边的被子动了一下。
然后是极轻微的颤抖。
秀兰似乎冷得缩成了一团,牙齿轻轻磕碰的声音隐约可闻。
他盯着屋顶模糊的黑暗,那里结着陈年的蛛网。
僵持了不知多久,他喉结滚动了一下,像是下定了极大的决心,猛地伸出手,抓住了那床隔在中间的红喜被的一角,用力一扯!
绸缎面冰凉滑腻的触感掠过他的手背。
他将被子大部分甩到了秀兰那边,动作粗鲁,甚至带着点赌气的意味,然后迅速收回手,重新紧紧闭上眼睛,背对着她,把自己缩回到炕沿边,仿佛刚才那个动作耗尽了他全部的勇气。
另一边的颤抖停顿了一瞬。
黑暗中,只听得见风呜呜地吹。
过了很久,很久,久到守仁几乎以为天永远不会亮了,他才听到极其细微的、布料摩擦的声音。
她似乎犹豫着,最终,还是把温暖的被子裹紧了些。
那床鲜红的、绣着鸳鸯的喜被,终于盖在了两个人的身上。
虽然,一个紧贴着墙,一个悬在炕边,中间依然隔着无法跨越的、冰冷的距离。
守仁睁着眼,首到窗户纸透出第一丝极其微弱的、属于黎明的青灰色。
那枚被藏起来的东西,像一根小小的刺,扎进了这个新婚之夜,也扎进了他刚刚开始的、名为“丈夫”的人生里。
而身边那个陌生女子均匀却依然带着戒备的呼吸声,告诉他,这条叫做“日子”的路,才刚刚抬起脚,前面漫长得很,也模糊得很。
泥土墙沉默地立着,见证着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