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爱我,心底却在喊救命(佚名佚名)无弹窗小说免费阅读_小说完整版免费阅读她说爱我,心底却在喊救命佚名佚名
我准备了整整一个夏天,只为在毕业前向我的青梅竹马林溪告白。
我以为那会是一场漫长暗恋的结束,和我们未来所有故事的开始。那天傍晚,她答应了。
她看着我,轻轻地点了点头。可就在那一瞬间,我刚获得的、那该死的读心能力,让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她心里的声音。那不是少女的羞涩,也不是恋爱的喜悦,而是一声发自灵魂深处的、凄厉的呐喊:快逃!1傍晚的风吹过湖面,带着一点水汽和青草的味道。我看着对面的林溪,连她头发被风吹起的弧度,都像是我预演过无数遍的场景。我不慌。语言是会骗人的,但细节不会。一个眼神,一次指尖的颤抖,对我来说,比一万句“我爱你”都更真实。我信赖的不是我们说过什么,而是我们之间那些无法言说的磁场。这,才是我和她之间真正的现实。就像高二那年,我们第一次去看那部沉闷的文艺片,影院里又黑又冷,我几乎要睡着。但我眼角的余光里,她坐得笔直。我看不清她的脸,却能清晰地看见,当银幕上的主角被迫与家人分离时,她放在膝盖上的手,指尖正随着压抑的配乐,极轻微地、神经质地颤抖着。那一刻,整个影院的悲伤,仿佛都浓缩在了她那一点点的颤抖里。我懂那种颤抖,就像我懂她那三种不同的微笑:嘴角上扬15度是礼貌,眼睛弯起来是真的开心,而只有嘴角动、眼睛却一潭死水的,是她想藏起心里的难过。今天的她,眼睛是弯的。所以,这场告白不是堵伯,只是走个流程。我深吸一口气,开了口。
那些提前背好的漂亮句子全忘了,说出来的话又笨又乱,我只是把我们俩从小到大的事串了一遍——从小学她分给我半块橡皮,到上个礼拜,我们在图书馆为了同一本书同时伸出手,然后看着对方傻笑。我说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变快了。我看见她的手在紧张地绞着衣角,脸也越来越红。
这些都是我熟悉的信号,是她紧张又期待的样子。我从她的眼睛里,读到了和我一样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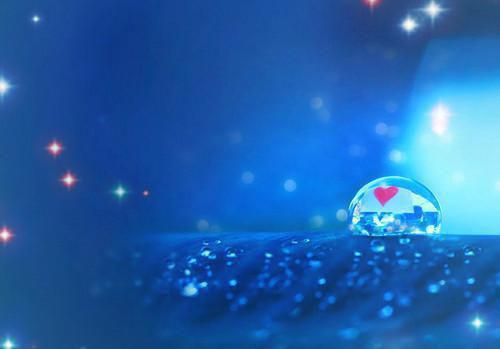
她抬起头,眼神亮晶晶的,像有星星掉在里面。她很轻地“嗯”了一声,然后说:“我……我愿意。”那一瞬间,我感觉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世界变成了一场无声电影,只有她的口型在闪闪发光。
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耳腔里擂鼓的声音,一声,又一声,敲打着“你是对的”这个节拍。
我,陈默,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她的人。我脸上挂着这个傻乎乎的笑,张开胳膊,准备给她一个我们早就该有的拥抱。就在我的指尖快要碰到她肩膀的衣服时——一个声音,一个不属于我的、尖锐又绝望的女声,毫无征兆地在我脑子里炸开了。“快逃!离他远点!
快逃啊!”这声音不像是用耳朵听到的,它是直接灌进我脑子里的,带着最原始的恐惧,和我眼前林溪那张又害羞又幸福的脸,形成了地狱一样的反差。我耳边的心跳声戛然而止。
来——风声、远处模糊的音乐、甚至是我自己因为笑容而僵硬的脸部肌肉被拉扯的细微声响。
我伸出去的手臂停在半空,第一次感觉到了傍晚空气里的凉意,那股凉意顺着我的指尖,像毒液一样钻回我的心脏。这是什么?幻觉吗?我看着林溪,她正温柔地对我笑着,等着我的拥抱。可那个声音还在我脑子里拼命地喊。我花了十八年搭建起来的世界,被这一声尖叫震出了第一道裂缝。然后,我眼睁睁地看着我所确信的一切,从那道裂缝里,掉了下去。2我僵在原地,伸出的手臂像一座瞬间凝固的雕塑。林溪脸上的笑容,在我凝固的表情前,也一寸寸地碎裂了。她眼里的光迅速黯淡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我看不懂的慌乱。“陈默?你怎么了?”她小声问。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该怎么说?说我听见了你心里的尖叫?说你一边对我笑,一边在心里让我快逃?我的沉默,似乎成了最伤人的回答。她眼中的慌乱变成了受伤,然后迅速被一层坚硬的伪装覆盖。她往后退了一小步,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我妈让我早点回家。”她丢下这句蹩脚的借口,像是被什么东西追赶一样,转身快步离去,背影仓皇得可笑。我一个人站在湖边,直到路灯一盏盏亮起,将我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那句“快逃”像一个魔咒,在我脑子里无限循环播放。
接下来的几天是地狱。我的世界被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她点头时亮晶晶的眼睛,另一半是她心里那声凄厉的呐喊。我看到的现实,和我听到的现实,在我脑子里打了一场仗,而我就是那个战场,被炮火轰得一片狼藉。我试着给她发信息,石沉大海。我打电话给她,听筒里永远是“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的冰冷女声。我被彻底隔绝了。她用沉默,在我面前关上了一扇我永远无法打开的门。一周后的那个下午,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像个幽灵一样在她家附近游荡,毫无目的,只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脚。然后,我看到了她。
她和她的继父王建军,正从街角的超市里走出来。那个男人脸上挂着温和的笑,甚至还和路过的邻居点头打招呼,看起来无可挑剔。但搭在她肩上的那只手,像一把铁钳,牢牢地将她固定在自己身边,不容许丝毫偏离。而林溪,她的脸上也挂着笑。
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僵硬而顺从的微笑,嘴角上扬的弧度像是用尺子量过,标准得没有一丝活气。她就像一个被画好表情的人偶,被那只手带着,一步一步,僵硬地往前走。我的呼吸停住了。我死死地盯着他们,所有的困惑、焦虑和不安,在这一刻高度集中,我的太阳穴突突地跳,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就在这时,那个声音又来了。这一次,它不再是模糊的呐喊,而是带着我的名字,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精准地捅进我的胸口。
“别看我……快走开……陈默……求你快走开……”这声音比“快逃”更让我痛苦。
它在推开我,用一种近乎哀求的姿态,执行着最残忍的命令。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我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困境。我该相信哪个“真实”?是相信我听到的?
尊重她内心的意愿,立刻转身,从她的世界里消失得干干净净?还是相信我看到的?
相信她那人偶般僵硬的表情,和她继父那只充满控制欲的手所透露出的危险信号?
我看着她越来越远的背影,那哀鸣还在我脑中回响。我忽然明白了,那声音里没有厌恶,也没有拒绝。那全是恐惧。我做出了决定。我不能走。我的问题,不再是“她为什么不愿和我在一起”。而是……她到底在害怕什么?3这个问题,成了我的整个世界。我开始像个贼一样,守在她家小区外面。躲在树荫下,藏在楼道的拐角,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罪犯。她心里的声音像根钉子,扎在我脑子里。
“快走开……陈默……求你快走开……”我站在这里的每一秒,都像是在背叛她。
可我没办法走。走了,就等于把她一个人丢在那个我看不见的恐惧里。
这种负罪感和保护她的冲动,像两只手,要把我的灵魂撕成两半。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
等一个信号,等一个能让我看清真相的裂缝。第三天傍晚,我等到了。
王建军从楼道里走了出来,手里提着一袋黑色的垃圾。他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还是那种温和的、让人挑不出错的笑。他走到小区的垃圾桶旁边,随手将垃圾袋扔了进去。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动作。但他扔得太随意,垃圾袋口没有扎紧,撞在垃圾桶的内壁上,袋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撒出来一些。我看见一抹惨白的颜色,从一堆果皮和废纸里滚了出来,掉在地上。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那是一个贝壳。
一个手掌大小的、带着漂亮纹路的白色贝壳。那是我送她的。初三毕业旅行时,我们在海边捡的。她说这是她收到过最好的礼物,一直放在书桌上,每天都擦。她说,把贝壳贴在耳朵上,就能听见我们那个夏天的海浪声。我曾经以为,那枚贝壳会永远待在她的书桌上。可现在,它就躺在那里,离一个被捏扁的酸奶盒子只有几厘米远。那一瞬间,我全身的血都凉了。那不是一块贝壳。
那是我们的过去。是她小心翼翼珍藏起来的,属于我们俩的、小小的世界。现在,它躺在烂菜叶和脏纸巾旁边,像个笑话。王建军看都没看一眼,转身就往回走。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一个念头,像一滴滚烫的、肮脏的油,滴进了我的大脑。
那不是林溪那种纯粹的、刀割般的呐喊。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入侵。
一种油腻的、带着腐烂气味的满足感,像一条冰冷的蛆,直接钻进了我的脑髓,让我一阵生理性的恶心。“总算清静了。”我脑子里所有乱七八糟的线头,瞬间被这冰冷的愤怒拧成了一股绳。清晰,而且坚硬。他不是在扔一个贝壳。
他是在抹掉我存在的痕迹。他是在告诉林溪,所有她珍视的东西,他都可以像扔垃圾一样,轻易地毁掉。她那句“快逃”,那句“快走开”,根本不是对我说的。她是在对自己,对那个想要向我求救的自己说。她在逼自己推开我,因为她害怕,她怕我被牵连进来,怕我像这枚贝壳一样,被这个男人轻易地碾碎。我所有的困惑、犹豫、自我怀疑,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常规的方法没用了。报警?我拿什么报警?说他扔了一个贝壳吗?
我看着王建军的背影消失在楼道口。我从树荫里走了出来,一步一步,走到那个绿色的垃圾桶旁边。我没有犹豫,弯下腰,伸手从那堆肮脏的垃圾里,把那枚贝壳捡了起来。它沾着一点黏腻的污渍,冰冷地躺在我的手心。
我没有擦掉上面的污渍。我把它放进口袋,任由那黏腻的污秽,紧紧贴上口袋里那张我们一起看过的、早已褪色的电影票根。过去的美好和眼前的罪恶,现在待在了一起。我把它紧紧攥住,贝壳坚硬的边缘硌得我手心生疼。这点疼,让我无比清醒。他以为他打造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完美世界。那我就做他这个世界里,唯一的幽灵。他想当这个家的主人。今晚,我就让他尝尝,被噩梦拜访的滋味。
4天上下着大雨。雨点像无数冰冷的石子,狠狠地砸在窗户上,砸在我脸上。
我站在她家楼下那棵老樟树的阴影里,全身都湿透了。
我找到了她很久以前告诉我的那块松动的地砖。掀开它,下面躺着一把被塑料袋包好的备用钥匙。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她忘了带钥匙,被锁在门外,是我陪她等到半夜。从那以后,她就把备用钥匙放在这里,还得意地告诉我,这是我们俩的秘密基地。这把钥匙,曾经是我们友谊的证明,是我们之间不需要言语的信任。
此刻,它在我手心里,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我感觉自己像个卑劣的小偷,正准备闯进自己最珍视的圣地。我犹豫了。也许我错了,也许一切都是我的胡思乱想。
可口袋里那枚冰冷的贝壳,用它坚硬的棱角,又一次刺痛了我的掌心。那上面黏腻的污渍,提醒着我它曾经躺在哪里。我不能再犹豫了。我用那把钥匙,打开了通往地狱的门。
屋子里一片漆黑,只有我和我咚咚作响的心跳。我没开灯,凭着记忆,像个幽灵一样摸进了她的房间。空气里有她身上那种淡淡的、像阳光晒过被子一样的味道。
我贪婪地吸了一口,罪恶感却像藤蔓一样缠住了我的脖子,让我几乎窒息。她的书桌很整齐。
书本、笔筒,都摆放得一丝不苟。在书桌的角落,我看到了那个上了锁的粉色日记本。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小的折叠刀,刀刃对准了那个脆弱的锁扣。撬开它的那一瞬间,我听见了自己心底某个部分碎裂的声音。我偷走了她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秘密。我的罪恶感,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我翻开了第一页。字迹是娟秀的,带着少女的雀跃。
上面写着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的感想,写着她在图书馆看到我时的小心思,甚至还有一句用铅笔轻轻写下的话:“今天陈默对我笑了,我觉得天都晴了。
”这些甜蜜的文字,像一把把尖刀,反复捅进我的心脏。我正在偷窥的,是一个女孩最干净、最美好的梦。而我,这个梦里的主角,却亲手把它打碎了。
我继续往后翻。突然,字迹变了。原本娟秀的字体变得潦草而扭曲,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写出来的。内容也从那些明亮的少女心事,急转直下,坠入了无尽的黑暗。日记里断断续续地记录着王建军那些带着笑意的警告,那些不动声色地毁掉她心爱东西的暴行,还有那些深夜里,他以“关心”为名,对她进行的、令人窒息的精神控制。然后,我看到了最关键的那一段。那是她上初二时写的。
字迹被泪水晕开,模糊不清,但我还是看懂了。她写道,她终于鼓起勇气,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最信任的班主任。老师很震惊,答应会帮助她。可是第二天,王建军就带着她妈妈一起去了学校。他用那种无懈可击的温和谎言,把一切都解释成是“青春期的叛逆”和“父女间的误会”。他演得那么好,连她妈妈都站在他那边,笑着对老师说,是孩子太敏感了。老师信了。那天晚上,王建军没有打她,也没有骂她。他只是当着她的面,给了她妈妈一记耳光。那一巴掌不重,声音却很脆。然后,他温柔地对她说:“你看,你一不听话,妈妈就会伤心。
”日记里写着:“那一整个晚上,我都听见妈妈在隔壁房间压抑着哭。那哭声像针一样,一针一针扎在我的心上。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向任何人求救了。因为我的求救,只会伤害我唯一想保护的人。”看到这里,我手里的日记本掉在了地上。真相像一场雪崩,将我彻底掩埋。我终于明白了。那句“快逃”,那句“快走开”,根本不是对我说的。
那是她对自己下的命令,是她在那次求救失败后,刻在灵魂里的诅咒。她怕我,不是因为讨厌我,而是因为她怕她的求救,会让我像她妈妈一样,被那个恶魔拖下水。
我没有感到任何解脱。我只感到一阵排山倒海的、想要呕吐的自我厌恶。
我觉得自己和王建军没有任何区别。他用暴力和谎言,控制着她的身体,囚禁着她的生活。
而我,用这把代表着信任的钥匙,用这把卑劣的小刀,闯进了她最后的避难所,撕开了她用尽力气才缝合好的伤口,窥探了她最痛苦的灵魂。我们都是闯入者,都是罪人。
这份罪恶感像水泥一样灌进了我的喉咙,让我几乎崩溃。就在我被这无边的黑暗吞没时,我的目光,落在了日记本翻开的最后一页上。那一页没有字。上面只有一幅画。
用黑色的水笔,一遍又一遍,反复描画出的一只鸟。那只鸟的翅膀张开到极限,羽毛的每一根线条都充满了挣扎的力量,它的姿态不是在飞翔,而是在拼尽全力,想要挣脱这张纸的束缚。那不是画。那是她无声的呐喊。这幅画,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我脑中所有的混乱和痛苦。我猛地醒悟过来。我那点可笑的道德挣扎,我那点自以为是的罪恶感,和她这种被困在笼子里、拼了命想要活下去的绝望相比,根本一文不值。我必须行动。这不再是为了拯救我暗恋的女孩。这是为了赎罪。
为了偿还我今晚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5我选了废弃车站。这里是城市的边缘,铁轨锈迹斑斑,一直伸向看不见的远方。这里代表着离开,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
我捏着口袋里那两张连夜买好的、去往南方小城的火车票,心脏在肋骨后面狂跳。
我给林溪发了条信息,只有六个字:“废弃车站。我等你。”我没有说“我来救你”,也没有说“跟我走”。因为我没资格。我不是来拯救她的。我是来赎罪的。
我偷走了她的秘密,现在,我要用我的一切,来换回她画里的那只鸟的自由。
哪怕她会因此恨我一辈子,我也认了。风吹过空旷的站台,发出呜呜的声响。我站得笔直,像一个准备奔赴刑场的士兵。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她会来,然后我们一起走。
或者她不会来,那我就冲到她家去,把她硬拽出来。甚至,我想过王建军会追来,我会跟他打一架,打得头破血流。我什么都想到了,也什么都准备好了。远处的铁轨尽头,出现了一个人影。我的呼吸停住了。那个人影越来越近,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几乎要从喉咙里蹦出来。是她!一定是她!她来了!我攥紧了口袋里的车票,向前迎了两步。
人影走出了阴影,站到了月台昏黄的灯光下。不是林溪。是王建军。
他脸上还是挂着那种温和的、无可挑剔的笑。他甚至穿得和我那天看到的一样,干净的衬衫,一丝不苟的裤子,像个来参加家长会的模范父亲。那一瞬间,我全身的血都凉了。
一股冰冷的寒气从脚底板升起,瞬间冻住了我所有的决心和勇气。“陈默,是吧?
”他先开了口,语气像是早就认识我一样亲切,“别紧张,我们谈谈。”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准备好的所有狠话,所有搏命的姿态,在他这副温和的面孔前,都显得像个笑话。“你是个好孩子,我知道。”他慢慢向我走近,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脏上,“你关心林溪,叔叔很感谢你。但有时候,关心会变成一种压力,你懂吗?”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怎么会在这里?林溪呢?
她把我的信息给他看了?还是他抢了她的手机?“她是个敏感的孩子。”王建军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