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林薇(田埂上的星辰)免费阅读无弹窗_田埂上的星辰陈望林薇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时间: 2025-09-13 07:21:30
陈望的指尖在“皖稻12号”育种报告的最后一页停顿,钢笔尖悬在“推广建议”那栏,半天没落下。
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办公室里,空调风带着凉意吹过书架,那本烫金的“农业科技进步三等奖”证书在阳光下泛着光,却照不进他心里的褶皱。
手机在桌面上震动时,他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土壤数据皱眉——江淮地区的土壤样本分析显示,“皖稻12号”在偏酸性土壤里的亩产能稳定在1100斤以上,可上周去皖南调研,同样的品种种在碱性偏高的田里,穗粒就稀了半截。
老农蹲在田埂上扒拉着稻穗说“你们城里的好种子,到咱这就像断了奶的娃”,这话像根细刺,扎在他脑子里拔不出来。
你妈她……她刚才在院子里喂鸡,突然就倒了,现在救护车正往县医院送!”
“嗡”的一声,陈望手里的钢笔“啪”地掉在报告上,墨水晕开一小片黑渍。
他抓起椅背上的外套就往外跑,办公桌抽屉没关严,里面露出个巴掌大的玻璃瓶,瓶里装着半瓶褐色的泥土——那是2001年他去农业大学报到前,爷爷从自家稻田里挖给他的,老人当时说“带上这个,不管走多远,都别忘了土地的脾气”。
车子驶出农科院大门,往高速路口赶的路上,陈望的手还在抖。
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又打给县医院急诊科,护士说“病人刚送进来,初步判断是脑梗,正在做CT,家属赶紧过来”。
他把油门踩得深了些,窗外的景色飞快倒退,掠过成片的稻田,青绿色的稻浪在风里起伏,像极了他小时候跟着爷爷在田埂上看到的模样。
1995年的夏天,清溪村的太阳格外毒。
10岁的陈望光着脚踩在田埂边的泥水里,帮爷爷把刚拔好的秧苗递过去。
爷爷戴着草帽,弯着腰在水田里插秧,汗珠顺着皱纹往下滴,砸在水面上溅起小水花。
“望啊,你看这秧苗,得插得深浅刚好,太深了闷得慌,太浅了站不住脚。”
爷爷首起腰,指着田里的秧苗给陈望看,“庄稼和人一样,得懂土地的脾气,土地才肯给你好收成。”
那天下午,村里的广播响了,说上游水库没水了,要限量供水。
接下来的一个月,清溪村遇上了旱灾,稻田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少,原本绿油油的秧苗慢慢发黄、枯萎。
陈望跟着爷爷去村头的水井挑水浇田,井里的水位越来越低,爷爷蹲在干裂的田埂上,看着蔫掉的稻穗叹气,那声叹气里的无奈,陈望记了很多年。
后来有次“科技下乡”,农业大学的老师带来新稻种,在村里选了两亩田试种。
陈望每天都跑去田埂上看,看着那些稻苗比自家的长得快、长得壮,收割时亩产多了200斤。
老师在田埂上给村民讲课,说“种庄稼不能只靠天,得靠学问,靠技术”,陈望凑在最前面,把老师说的每句话都记在心里,回家后还把老师给的稻种包装袋夹在课本里,对着上面的“品种特性”一个字一个字地认。
“清溪村还有多久到?”
导航提示还有50公里时,陈望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父亲打来的,声音沙哑:“望啊,你妈她……醒了一次,说想见你,又说不出话……”陈望咬着牙,眼眶发热。
他想起上次回清溪村,是三年前春节,母亲在厨房忙前忙后,炖了他最爱喝的鸡汤,说“你在城里搞研究辛苦,多补补”。
那时母亲的身体还硬朗,送他走的时候,还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挥手,让他“别总惦记家里,好好工作”。
他那时答应母亲,等忙完手里的课题,就回来多住几天,可课题一个接一个,他总说“再等等”,这一等,就等到了母亲躺在病床上的消息。
车子下了高速,往县医院的方向开。
路边的稻田越来越多,有的己经抽穗,有的还在灌浆,阳光洒在稻穗上,泛着淡淡的金光。
陈望的脑海里,突然闪过爷爷当年给他装泥土的场景——老人蹲在稻田里,用手挖起一块湿润的泥土,小心翼翼地装进玻璃瓶,说“这土是咱清溪村的根,你带着它,不管到哪,都能想起咱村的田”。
他抬手抹了把脸,把眼泪逼回去。
县医院的大楼越来越近,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妈,你一定要好好的。
等你好了,我就回清溪村,看看咱村的田,看看那些被遗忘的土地,看看爷爷当年说的“土地的脾气”,到底藏着怎样的答案。
车子停在县医院急诊楼前,陈望推开车门,快步往里面跑。
阳光落在他的身后,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连接着都市与乡村的线,一头系着实验室里的育种报告,一头系着清溪村的田埂,系着玻璃瓶里的泥土,系着他从未忘记的初心。
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办公室里,空调风带着凉意吹过书架,那本烫金的“农业科技进步三等奖”证书在阳光下泛着光,却照不进他心里的褶皱。
手机在桌面上震动时,他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土壤数据皱眉——江淮地区的土壤样本分析显示,“皖稻12号”在偏酸性土壤里的亩产能稳定在1100斤以上,可上周去皖南调研,同样的品种种在碱性偏高的田里,穗粒就稀了半截。
老农蹲在田埂上扒拉着稻穗说“你们城里的好种子,到咱这就像断了奶的娃”,这话像根细刺,扎在他脑子里拔不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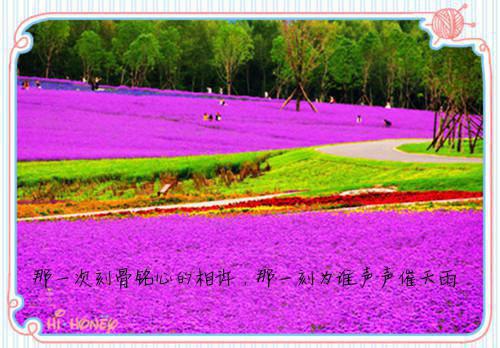
你妈她……她刚才在院子里喂鸡,突然就倒了,现在救护车正往县医院送!”
“嗡”的一声,陈望手里的钢笔“啪”地掉在报告上,墨水晕开一小片黑渍。
他抓起椅背上的外套就往外跑,办公桌抽屉没关严,里面露出个巴掌大的玻璃瓶,瓶里装着半瓶褐色的泥土——那是2001年他去农业大学报到前,爷爷从自家稻田里挖给他的,老人当时说“带上这个,不管走多远,都别忘了土地的脾气”。
车子驶出农科院大门,往高速路口赶的路上,陈望的手还在抖。
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又打给县医院急诊科,护士说“病人刚送进来,初步判断是脑梗,正在做CT,家属赶紧过来”。
他把油门踩得深了些,窗外的景色飞快倒退,掠过成片的稻田,青绿色的稻浪在风里起伏,像极了他小时候跟着爷爷在田埂上看到的模样。
1995年的夏天,清溪村的太阳格外毒。
10岁的陈望光着脚踩在田埂边的泥水里,帮爷爷把刚拔好的秧苗递过去。
爷爷戴着草帽,弯着腰在水田里插秧,汗珠顺着皱纹往下滴,砸在水面上溅起小水花。
“望啊,你看这秧苗,得插得深浅刚好,太深了闷得慌,太浅了站不住脚。”
爷爷首起腰,指着田里的秧苗给陈望看,“庄稼和人一样,得懂土地的脾气,土地才肯给你好收成。”
那天下午,村里的广播响了,说上游水库没水了,要限量供水。
接下来的一个月,清溪村遇上了旱灾,稻田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少,原本绿油油的秧苗慢慢发黄、枯萎。
陈望跟着爷爷去村头的水井挑水浇田,井里的水位越来越低,爷爷蹲在干裂的田埂上,看着蔫掉的稻穗叹气,那声叹气里的无奈,陈望记了很多年。
后来有次“科技下乡”,农业大学的老师带来新稻种,在村里选了两亩田试种。
陈望每天都跑去田埂上看,看着那些稻苗比自家的长得快、长得壮,收割时亩产多了200斤。
老师在田埂上给村民讲课,说“种庄稼不能只靠天,得靠学问,靠技术”,陈望凑在最前面,把老师说的每句话都记在心里,回家后还把老师给的稻种包装袋夹在课本里,对着上面的“品种特性”一个字一个字地认。
“清溪村还有多久到?”
导航提示还有50公里时,陈望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父亲打来的,声音沙哑:“望啊,你妈她……醒了一次,说想见你,又说不出话……”陈望咬着牙,眼眶发热。
他想起上次回清溪村,是三年前春节,母亲在厨房忙前忙后,炖了他最爱喝的鸡汤,说“你在城里搞研究辛苦,多补补”。
那时母亲的身体还硬朗,送他走的时候,还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挥手,让他“别总惦记家里,好好工作”。
他那时答应母亲,等忙完手里的课题,就回来多住几天,可课题一个接一个,他总说“再等等”,这一等,就等到了母亲躺在病床上的消息。
车子下了高速,往县医院的方向开。
路边的稻田越来越多,有的己经抽穗,有的还在灌浆,阳光洒在稻穗上,泛着淡淡的金光。
陈望的脑海里,突然闪过爷爷当年给他装泥土的场景——老人蹲在稻田里,用手挖起一块湿润的泥土,小心翼翼地装进玻璃瓶,说“这土是咱清溪村的根,你带着它,不管到哪,都能想起咱村的田”。
他抬手抹了把脸,把眼泪逼回去。
县医院的大楼越来越近,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妈,你一定要好好的。
等你好了,我就回清溪村,看看咱村的田,看看那些被遗忘的土地,看看爷爷当年说的“土地的脾气”,到底藏着怎样的答案。
车子停在县医院急诊楼前,陈望推开车门,快步往里面跑。
阳光落在他的身后,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连接着都市与乡村的线,一头系着实验室里的育种报告,一头系着清溪村的田埂,系着玻璃瓶里的泥土,系着他从未忘记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