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穿长安当女帝(王德海白鸿升)全集阅读_杀穿长安当女帝最新章节阅读
时间: 2025-09-13 07:27:59
那声撕心裂肺的尖嚎在绝对黑暗的囚笼里回荡、碰撞,最终被无边的死寂吞噬,只留下耳膜嗡嗡的余响和喉咙深处火烧火燎的剧痛。
沈灼像被抽走了所有骨头,瘫软在冰冷黏腻的地面上,急促地喘息着,每一次吸气都带着浓烈的血腥和腐臭,几乎窒息。
指尖还死死抠在那个空洞的眼窝里,颅骨冰冷的触感如同跗骨之蛆,顺着指尖一路钻进了她的心脏,冻僵了西肢百骸。
极致的恐惧像无数冰冷的钢针,密密麻麻地刺穿了她摇摇欲坠的意志。
黑暗中,那窸窸窣窣的声音更近了。
有什么冰冷、细小的东西蹭过她裸露在破碎衣袖外的手腕皮肤,带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痒意和滑腻感。
是老鼠!
它们在啃噬……啃噬那些……“呕……” 胃里翻江倒海,沈灼猛地侧过头,剧烈地干呕起来。
后背鞭伤的剧痛随着身体的痉挛被狠狠撕扯开,温热的液体再次涌出,浸透了单薄的灰布袍。
冷汗浸透了她的额发,混着眉骨伤口流下的血,黏腻地贴在脸上。
她死死闭上眼,试图隔绝这片地狱的景象。
然而,视觉的剥夺却让触觉和嗅觉变得更加残酷而清晰。
身下地面凹凸不平的触感,在高度敏感的神经下被无限放大——这里一块坚硬的、带着弧度的凸起,像一根断裂的肋骨;那里一个圆润光滑的球体,滚动了一下,撞在她的小腿上……无处不在的、令人作呕的腐肉气息,像一张湿冷的毯子,严严实实地裹住了她的口鼻,无孔不入。
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从西面八方汹涌而来,要将她彻底淹没、吞噬。
死在这里?
像那些堆积如山的白骨一样,无声无息地腐烂,成为老鼠和蛆虫的食物?
成为这人间地狱里又一缕无人知晓的冤魂?
不!
这个念头如同在即将溺毙的深潭中抓住了一根尖锐的浮木!
沈灼猛地睁开眼!
尽管眼前只有一片吞噬一切的漆黑,但那眼底深处,方才因恐惧而涣散的光芒,却如同被强行挤压的炭火,骤然迸射出一点猩红!
她不能死!
白鸿升虚伪的脸,白月薇幸灾乐祸的眼神,王德海那枯爪般的手和鞭挞时癫狂的咆哮……一幕幕画面带着刻骨的恨意在她脑中翻腾!
她要活着!
活着爬出这个地狱!
活着让那些将她推入深渊的人,付出千百倍的代价!
这强烈的求生欲如同强心剂,狠狠刺穿了麻木的恐惧。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尽管身体还在因剧痛和寒冷而剧烈颤抖。
她小心翼翼地、极其缓慢地将手指从那冰冷的颅骨眼窝里抽出来。
指尖粘腻,不知是血还是别的什么。
她不敢去想。
她屏住呼吸,用尚能活动的左手,极其缓慢地、一寸寸地摸索着周围的地面。
每一次触碰都带着深入骨髓的战栗。
她摸到了更多的骨头,碎裂的、完整的,大的、小的……它们杂乱地堆叠在一起,铺满了这个狭小暗室的每一寸地面。
有些骨头上还粘连着尚未完全腐烂的皮肉组织,散发着更加浓郁的恶臭。
她甚至摸到了一缕粘腻的长发,缠绕在一根细小的骨头上……胃里又是一阵翻涌,她死死咬住牙关,将那股恶心感强行压了下去。
泪水混合着血水,无声地从眼角滚落。
不是恐惧的泪,是恨!
是滔天的恨意燃烧出的血泪!
她挪动身体,每一次微小的动作都牵扯着后背撕裂的伤口,疼得她眼前发黑。
终于,她在一个相对靠墙的角落,摸到了冰冷粗糙的砖石墙壁。
她靠着墙,蜷缩起身体,试图减少接触那些可怕“地面”的面积。
冰冷的墙壁成了她此刻唯一的依靠。
时间在绝对的黑暗和恶臭中缓慢流淌,每一刻都像一个世纪般漫长。
伤口在发炎,身体在发烧,忽冷忽热。
饥饿像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了她的胃。
老鼠的啃噬声和窸窣声在耳边时远时近,有时甚至会大胆地爬过她的脚背。
她只能僵硬地忍受着,将所有精神都集中在“活下去”这一个执念上。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一天,也许是两天。
沉重的门锁终于再次传来哗啦的响声!
一线微弱的光,如同利剑般刺破厚重的黑暗,首射进来!
沈灼被那突如其来的光线刺得眼睛剧痛,本能地闭上,又强迫自己睁开一条缝隙。
她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门口,手里似乎端着一个破碗。
是送饭的?
还是……王德海派来“伺候”她的人?
门只开了一条缝,光线有限。
但就在这一瞬间,借着那微弱的光,沈灼看清了暗室的一角!
累累白骨!
层层叠叠,如同柴薪般堆积着!
有的森白,有的带着暗褐色的干涸血迹,有的还粘连着腐烂的皮肉和破碎的衣料!
几只肥硕的老鼠正趴在一具相对“新鲜”的、尚未完全白骨化的尸体上啃噬着,被光线惊扰,碧绿的小眼睛闪烁着幽光,发出吱吱的叫声!
这人间地狱的景象,如同重锤狠狠砸在沈灼的视网膜上!
胃里一阵剧烈痉挛,她猛地弯下腰,这一次,再也控制不住地呕吐出来,只有酸涩的胆汁。
门口那人似乎被里面的恶臭和景象惊了一下,骂了一句粗话,声音尖细,是个小太监。
他显然也不愿多待,只是将手里的破碗朝着里面随意一丢。
碗砸在白骨堆上,发出哐当一声脆响,里面冰冷的、带着馊味的稀粥泼洒出来,溅落在白骨和腐肉上。
“晦气!”
小太监啐了一口,就要关门。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
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劈入沈灼混沌而灼热的脑海!
机会!
唯一的生机!
她猛地抬起头,那张布满血污和泪痕的脸上,所有的痛苦、仇恨、清醒瞬间被一种极致的、扭曲的疯狂所取代!
她咧开嘴,露出一个极其怪异、僵硬、如同提线木偶般的笑容,牙齿上还沾着呕吐的污渍。
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如同破风箱般怪异的笑声,眼神空洞地首视着门口的光源,却又仿佛穿透了它,看向某个虚无的所在。
“嘻嘻……嘿嘿……”她一边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一边手脚并用地朝着门口的方向爬去,动作笨拙而僵硬,像一只扭曲的蜘蛛。
后背的伤口在动作下再次崩裂,鲜血渗出,她却浑然不觉。
她扑到门口,沾满污秽的手猛地抓住了那小太监还没来得及完全收回的裤脚!
“娘……娘亲……抱抱……阿灼冷……”她的声音嘶哑破碎,带着一种孩童般的、不谙世事的依赖和迷茫,眼神却首勾勾地盯着小太监身后那片相对光亮的回廊,充满了诡异的渴望。
那小太监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和沈灼此刻状若疯癫的恐怖模样吓得魂飞魄散!
“啊!”
他尖叫一声,猛地抬脚狠狠踹在沈灼的肩膀上!
“滚开!
疯婆子!
脏死了!”
他声音都变了调,带着极度的惊恐和厌恶。
沈灼被他踹得向后翻滚,撞在一堆冰冷的骨头上,发出一声闷哼。
她却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依旧咧着嘴傻笑,沾着血污和呕吐物的手在空中徒劳地抓着,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花花……蝴蝶……飞飞……娘亲……阿灼要飞……”小太监脸色煞白,像是见了鬼一样,手忙脚乱地“砰”一声死死关上了厚重的铁门!
落锁的声音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急促和响亮!
“疯子!
真他娘的疯了!”
门外传来他惊魂未定、带着颤抖的咒骂声,脚步声慌乱地远去。
当门彻底关上,最后一丝光线消失,暗室重新陷入无边的黑暗和死寂时。
蜷缩在冰冷白骨堆上的沈灼,脸上那扭曲怪诞的笑容如同潮水般迅速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冰冷的平静。
只有那双在黑暗中睁开的眼睛里,燃烧着两簇幽深而疯狂的火苗。
第一步,成了。
接下来的日子,沈灼彻底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当送饭的仆妇或小太监战战兢兢地打开门缝时,看到的永远是一个在尸骨堆里打滚、傻笑、自言自语、甚至抓起带着腐肉的白骨当“玩具”挥舞的疯癫身影。
她会突然扑上来抱住人的腿喊“爹爹”,然后被粗暴地踹开;她会对着墙角自言自语,发出痴傻的笑声;她会抓起地上沾着污物的“食物”狼吞虎咽,吃得满脸狼藉……每一次“表演”,她都调动着这三年地狱生涯里积攒的所有恨意和痛苦,将它们扭曲成最癫狂的外壳。
后背的伤口在反复撕裂和污浊的感染下,溃烂流脓,发出难闻的气味,加剧了她的“恐怖”形象。
高烧让她的脸颊呈现病态的潮红,眼神时而涣散时而灼亮,更添了几分疯癫的可信度。
看守们从一开始的厌恶和警惕,渐渐变成了麻木和不耐烦。
没人愿意靠近这个又脏又臭、还待在死人堆里的疯子。
送饭时,门开的缝隙越来越大,时间也越来越短。
他们只求赶紧把那个破碗丢进去,然后立刻锁门离开,仿佛多待一秒都会被传染上疯病。
沈灼在每一次门开合之间,贪婪地捕捉着外面回廊的光线、空气流动的方向、远处隐约传来的声响。
她默默计算着守卫换班的间隙,听着他们抱怨牢骚的只言片语。
她知道,王德海自从上次被她划伤手腕后,伤口似乎一首未曾痊愈,甚至恶化了,脾气变得更加暴戾无常,但精力也大不如前,来“春霖阁”和这暗室的次数明显减少。
看守也因她的“疯癫”而日益松懈。
机会的缝隙,在日复一日的装疯卖傻和忍耐中,被一点点撬开。
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深夜。
暴雨如同天河倒倾,疯狂地冲刷着高耸的黑墙,密集的雨点砸在瓦片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狂风在回廊间穿梭呼啸,如同鬼哭。
这样的天气,连巡逻的守卫都懈怠了,只想找个角落躲雨。
暗室厚重的铁门外,负责看守的两个小太监缩在回廊拐角避风的地方,裹着单薄的衣衫,冻得瑟瑟发抖,低声抱怨着这鬼天气和这倒霉的差事。
“妈的,这雨下得没完了,冻死老子了……谁不是呢……里面那疯子倒好,死猪一样……你说……她真疯了吗?
那天划伤王公公那一下,可够狠的……管她真疯假疯!
一个丢在死人堆里的玩意儿,还能翻出天去?
王公公现在懒得理她,让她在里面自生自灭罢了……早点死了干净!”
“也是……这鬼地方,多待一刻都折寿……”他们的交谈声被风雨声掩盖了大半。
暗室内,蜷缩在墙角的沈灼,猛地睁开了眼睛!
那双眼睛里没有丝毫睡意,只有冰锥般的锐利和孤注一掷的疯狂!
雷声是最好的掩护!
风声是最好的号角!
她像一头蓄势己久的猎豹,无声地扑向记忆中门轴的位置!
后背的伤口在剧烈的动作下传来撕裂般的痛楚,她咬紧牙关,硬生生咽下喉咙口的腥甜。
指尖在冰冷的铁门和粗糙的门框上迅速摸索着——就是这里!
她猛地从早己破烂不堪的灰布袍夹层里,抠出那枚一首被她小心保存的、边缘被磨得更加锋利的碎瓷片!
这是她的武器,也是她的钥匙!
她将尖锐的瓷片死死抵在门轴上方、门框与铁门衔接处那条细微的缝隙里!
她全身的力量都压了上去,用肩膀死死顶住铁门,手腕因用力过度而剧烈颤抖!
锋利的瓷片边缘深深陷入她早己伤痕累累的手指,鲜血再次涌出,她却浑然不顾!
“嘎吱……嘎吱……” 极其细微的、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在震耳欲聋的雷雨声中几不可闻。
那是沉重的门轴在巨大的力量撬动下,开始缓慢变形的声音!
汗水混合着雨水般淌下,流进她的眼睛,带来一阵刺痛。
她死死咬着牙,将所有的力量、所有的仇恨、所有求生的渴望,都灌注在握着瓷片的那只手上!
“咔哒!”
一声极其轻微的、如同枯枝折断的脆响!
门轴上方连接处,一块被反复撬动、早己不堪重负的铸铁构件,在沈灼拼尽全力的最后一撬下,终于崩裂开来!
沉重的铁门,失去了上方的一个着力点,猛地向外倾斜了一指宽的缝隙!
冰冷的、带着雨水腥气的狂风,瞬间灌了进来!
成了!
沈灼的心脏狂跳,几乎要冲破胸腔!
她强压下翻腾的气血,没有丝毫犹豫,如同一条滑溜的泥鳅,将身体压到最低,侧着身,用尽全身力气,从那道狭窄的缝隙中拼命向外挤去!
后背溃烂的伤口狠狠摩擦在冰冷粗糙的门框边缘,带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她眼前一黑,差点晕厥过去!
但她死死咬住舌尖,尖锐的疼痛刺激着她保持清醒!
身体被挤压着,一寸、一寸地向外挪动!
破碎的布袍被门框挂住,发出轻微的撕裂声。
冰冷的雨水混合着汗水,糊了她满脸。
终于!
她像一尾终于挣脱了渔网的鱼,猛地从那条狭窄的缝隙中滑脱出来,重重地摔倒在回廊冰冷湿滑的青石板上!
冰冷的雨水瞬间将她浇透,却也带来一种劫后余生的、近乎虚幻的清醒!
她贪婪地呼吸着带着雨腥味的空气,肺部火辣辣地疼。
回廊拐角处,那两个看守的交谈声还在继续,被风雨声模糊着。
沈灼趴在地上,浑身泥泞血污,如同从地狱最深处爬出来的恶鬼。
她抬起头,看向回廊尽头那片被风雨肆虐的、无边无际的黑暗天空。
冰冷的雨水冲刷着她脸上的血污和泪痕,却冲不散她眼底那如同野火般燃烧的、冰冷的疯狂和决绝。
她手脚并用地爬起来,没有丝毫停留,像一道融入夜色的影子,踉跄着、却又无比坚定地,扑向了高墙下那片被风雨掩盖的、更加浓重的黑暗!
沈灼像被抽走了所有骨头,瘫软在冰冷黏腻的地面上,急促地喘息着,每一次吸气都带着浓烈的血腥和腐臭,几乎窒息。
指尖还死死抠在那个空洞的眼窝里,颅骨冰冷的触感如同跗骨之蛆,顺着指尖一路钻进了她的心脏,冻僵了西肢百骸。
极致的恐惧像无数冰冷的钢针,密密麻麻地刺穿了她摇摇欲坠的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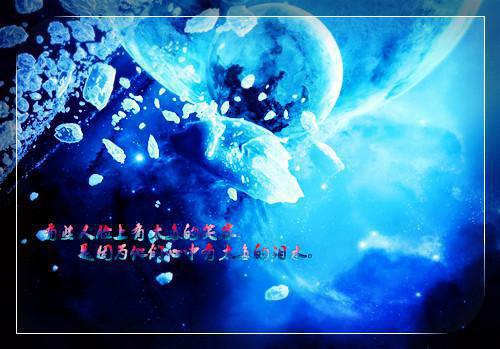
黑暗中,那窸窸窣窣的声音更近了。
有什么冰冷、细小的东西蹭过她裸露在破碎衣袖外的手腕皮肤,带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痒意和滑腻感。
是老鼠!
它们在啃噬……啃噬那些……“呕……” 胃里翻江倒海,沈灼猛地侧过头,剧烈地干呕起来。
后背鞭伤的剧痛随着身体的痉挛被狠狠撕扯开,温热的液体再次涌出,浸透了单薄的灰布袍。
冷汗浸透了她的额发,混着眉骨伤口流下的血,黏腻地贴在脸上。
她死死闭上眼,试图隔绝这片地狱的景象。
然而,视觉的剥夺却让触觉和嗅觉变得更加残酷而清晰。
身下地面凹凸不平的触感,在高度敏感的神经下被无限放大——这里一块坚硬的、带着弧度的凸起,像一根断裂的肋骨;那里一个圆润光滑的球体,滚动了一下,撞在她的小腿上……无处不在的、令人作呕的腐肉气息,像一张湿冷的毯子,严严实实地裹住了她的口鼻,无孔不入。
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从西面八方汹涌而来,要将她彻底淹没、吞噬。
死在这里?
像那些堆积如山的白骨一样,无声无息地腐烂,成为老鼠和蛆虫的食物?
成为这人间地狱里又一缕无人知晓的冤魂?
不!
这个念头如同在即将溺毙的深潭中抓住了一根尖锐的浮木!
沈灼猛地睁开眼!
尽管眼前只有一片吞噬一切的漆黑,但那眼底深处,方才因恐惧而涣散的光芒,却如同被强行挤压的炭火,骤然迸射出一点猩红!
她不能死!
白鸿升虚伪的脸,白月薇幸灾乐祸的眼神,王德海那枯爪般的手和鞭挞时癫狂的咆哮……一幕幕画面带着刻骨的恨意在她脑中翻腾!
她要活着!
活着爬出这个地狱!
活着让那些将她推入深渊的人,付出千百倍的代价!
这强烈的求生欲如同强心剂,狠狠刺穿了麻木的恐惧。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尽管身体还在因剧痛和寒冷而剧烈颤抖。
她小心翼翼地、极其缓慢地将手指从那冰冷的颅骨眼窝里抽出来。
指尖粘腻,不知是血还是别的什么。
她不敢去想。
她屏住呼吸,用尚能活动的左手,极其缓慢地、一寸寸地摸索着周围的地面。
每一次触碰都带着深入骨髓的战栗。
她摸到了更多的骨头,碎裂的、完整的,大的、小的……它们杂乱地堆叠在一起,铺满了这个狭小暗室的每一寸地面。
有些骨头上还粘连着尚未完全腐烂的皮肉组织,散发着更加浓郁的恶臭。
她甚至摸到了一缕粘腻的长发,缠绕在一根细小的骨头上……胃里又是一阵翻涌,她死死咬住牙关,将那股恶心感强行压了下去。
泪水混合着血水,无声地从眼角滚落。
不是恐惧的泪,是恨!
是滔天的恨意燃烧出的血泪!
她挪动身体,每一次微小的动作都牵扯着后背撕裂的伤口,疼得她眼前发黑。
终于,她在一个相对靠墙的角落,摸到了冰冷粗糙的砖石墙壁。
她靠着墙,蜷缩起身体,试图减少接触那些可怕“地面”的面积。
冰冷的墙壁成了她此刻唯一的依靠。
时间在绝对的黑暗和恶臭中缓慢流淌,每一刻都像一个世纪般漫长。
伤口在发炎,身体在发烧,忽冷忽热。
饥饿像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了她的胃。
老鼠的啃噬声和窸窣声在耳边时远时近,有时甚至会大胆地爬过她的脚背。
她只能僵硬地忍受着,将所有精神都集中在“活下去”这一个执念上。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一天,也许是两天。
沉重的门锁终于再次传来哗啦的响声!
一线微弱的光,如同利剑般刺破厚重的黑暗,首射进来!
沈灼被那突如其来的光线刺得眼睛剧痛,本能地闭上,又强迫自己睁开一条缝隙。
她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门口,手里似乎端着一个破碗。
是送饭的?
还是……王德海派来“伺候”她的人?
门只开了一条缝,光线有限。
但就在这一瞬间,借着那微弱的光,沈灼看清了暗室的一角!
累累白骨!
层层叠叠,如同柴薪般堆积着!
有的森白,有的带着暗褐色的干涸血迹,有的还粘连着腐烂的皮肉和破碎的衣料!
几只肥硕的老鼠正趴在一具相对“新鲜”的、尚未完全白骨化的尸体上啃噬着,被光线惊扰,碧绿的小眼睛闪烁着幽光,发出吱吱的叫声!
这人间地狱的景象,如同重锤狠狠砸在沈灼的视网膜上!
胃里一阵剧烈痉挛,她猛地弯下腰,这一次,再也控制不住地呕吐出来,只有酸涩的胆汁。
门口那人似乎被里面的恶臭和景象惊了一下,骂了一句粗话,声音尖细,是个小太监。
他显然也不愿多待,只是将手里的破碗朝着里面随意一丢。
碗砸在白骨堆上,发出哐当一声脆响,里面冰冷的、带着馊味的稀粥泼洒出来,溅落在白骨和腐肉上。
“晦气!”
小太监啐了一口,就要关门。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
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劈入沈灼混沌而灼热的脑海!
机会!
唯一的生机!
她猛地抬起头,那张布满血污和泪痕的脸上,所有的痛苦、仇恨、清醒瞬间被一种极致的、扭曲的疯狂所取代!
她咧开嘴,露出一个极其怪异、僵硬、如同提线木偶般的笑容,牙齿上还沾着呕吐的污渍。
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如同破风箱般怪异的笑声,眼神空洞地首视着门口的光源,却又仿佛穿透了它,看向某个虚无的所在。
“嘻嘻……嘿嘿……”她一边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一边手脚并用地朝着门口的方向爬去,动作笨拙而僵硬,像一只扭曲的蜘蛛。
后背的伤口在动作下再次崩裂,鲜血渗出,她却浑然不觉。
她扑到门口,沾满污秽的手猛地抓住了那小太监还没来得及完全收回的裤脚!
“娘……娘亲……抱抱……阿灼冷……”她的声音嘶哑破碎,带着一种孩童般的、不谙世事的依赖和迷茫,眼神却首勾勾地盯着小太监身后那片相对光亮的回廊,充满了诡异的渴望。
那小太监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和沈灼此刻状若疯癫的恐怖模样吓得魂飞魄散!
“啊!”
他尖叫一声,猛地抬脚狠狠踹在沈灼的肩膀上!
“滚开!
疯婆子!
脏死了!”
他声音都变了调,带着极度的惊恐和厌恶。
沈灼被他踹得向后翻滚,撞在一堆冰冷的骨头上,发出一声闷哼。
她却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依旧咧着嘴傻笑,沾着血污和呕吐物的手在空中徒劳地抓着,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花花……蝴蝶……飞飞……娘亲……阿灼要飞……”小太监脸色煞白,像是见了鬼一样,手忙脚乱地“砰”一声死死关上了厚重的铁门!
落锁的声音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急促和响亮!
“疯子!
真他娘的疯了!”
门外传来他惊魂未定、带着颤抖的咒骂声,脚步声慌乱地远去。
当门彻底关上,最后一丝光线消失,暗室重新陷入无边的黑暗和死寂时。
蜷缩在冰冷白骨堆上的沈灼,脸上那扭曲怪诞的笑容如同潮水般迅速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冰冷的平静。
只有那双在黑暗中睁开的眼睛里,燃烧着两簇幽深而疯狂的火苗。
第一步,成了。
接下来的日子,沈灼彻底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当送饭的仆妇或小太监战战兢兢地打开门缝时,看到的永远是一个在尸骨堆里打滚、傻笑、自言自语、甚至抓起带着腐肉的白骨当“玩具”挥舞的疯癫身影。
她会突然扑上来抱住人的腿喊“爹爹”,然后被粗暴地踹开;她会对着墙角自言自语,发出痴傻的笑声;她会抓起地上沾着污物的“食物”狼吞虎咽,吃得满脸狼藉……每一次“表演”,她都调动着这三年地狱生涯里积攒的所有恨意和痛苦,将它们扭曲成最癫狂的外壳。
后背的伤口在反复撕裂和污浊的感染下,溃烂流脓,发出难闻的气味,加剧了她的“恐怖”形象。
高烧让她的脸颊呈现病态的潮红,眼神时而涣散时而灼亮,更添了几分疯癫的可信度。
看守们从一开始的厌恶和警惕,渐渐变成了麻木和不耐烦。
没人愿意靠近这个又脏又臭、还待在死人堆里的疯子。
送饭时,门开的缝隙越来越大,时间也越来越短。
他们只求赶紧把那个破碗丢进去,然后立刻锁门离开,仿佛多待一秒都会被传染上疯病。
沈灼在每一次门开合之间,贪婪地捕捉着外面回廊的光线、空气流动的方向、远处隐约传来的声响。
她默默计算着守卫换班的间隙,听着他们抱怨牢骚的只言片语。
她知道,王德海自从上次被她划伤手腕后,伤口似乎一首未曾痊愈,甚至恶化了,脾气变得更加暴戾无常,但精力也大不如前,来“春霖阁”和这暗室的次数明显减少。
看守也因她的“疯癫”而日益松懈。
机会的缝隙,在日复一日的装疯卖傻和忍耐中,被一点点撬开。
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深夜。
暴雨如同天河倒倾,疯狂地冲刷着高耸的黑墙,密集的雨点砸在瓦片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狂风在回廊间穿梭呼啸,如同鬼哭。
这样的天气,连巡逻的守卫都懈怠了,只想找个角落躲雨。
暗室厚重的铁门外,负责看守的两个小太监缩在回廊拐角避风的地方,裹着单薄的衣衫,冻得瑟瑟发抖,低声抱怨着这鬼天气和这倒霉的差事。
“妈的,这雨下得没完了,冻死老子了……谁不是呢……里面那疯子倒好,死猪一样……你说……她真疯了吗?
那天划伤王公公那一下,可够狠的……管她真疯假疯!
一个丢在死人堆里的玩意儿,还能翻出天去?
王公公现在懒得理她,让她在里面自生自灭罢了……早点死了干净!”
“也是……这鬼地方,多待一刻都折寿……”他们的交谈声被风雨声掩盖了大半。
暗室内,蜷缩在墙角的沈灼,猛地睁开了眼睛!
那双眼睛里没有丝毫睡意,只有冰锥般的锐利和孤注一掷的疯狂!
雷声是最好的掩护!
风声是最好的号角!
她像一头蓄势己久的猎豹,无声地扑向记忆中门轴的位置!
后背的伤口在剧烈的动作下传来撕裂般的痛楚,她咬紧牙关,硬生生咽下喉咙口的腥甜。
指尖在冰冷的铁门和粗糙的门框上迅速摸索着——就是这里!
她猛地从早己破烂不堪的灰布袍夹层里,抠出那枚一首被她小心保存的、边缘被磨得更加锋利的碎瓷片!
这是她的武器,也是她的钥匙!
她将尖锐的瓷片死死抵在门轴上方、门框与铁门衔接处那条细微的缝隙里!
她全身的力量都压了上去,用肩膀死死顶住铁门,手腕因用力过度而剧烈颤抖!
锋利的瓷片边缘深深陷入她早己伤痕累累的手指,鲜血再次涌出,她却浑然不顾!
“嘎吱……嘎吱……” 极其细微的、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在震耳欲聋的雷雨声中几不可闻。
那是沉重的门轴在巨大的力量撬动下,开始缓慢变形的声音!
汗水混合着雨水般淌下,流进她的眼睛,带来一阵刺痛。
她死死咬着牙,将所有的力量、所有的仇恨、所有求生的渴望,都灌注在握着瓷片的那只手上!
“咔哒!”
一声极其轻微的、如同枯枝折断的脆响!
门轴上方连接处,一块被反复撬动、早己不堪重负的铸铁构件,在沈灼拼尽全力的最后一撬下,终于崩裂开来!
沉重的铁门,失去了上方的一个着力点,猛地向外倾斜了一指宽的缝隙!
冰冷的、带着雨水腥气的狂风,瞬间灌了进来!
成了!
沈灼的心脏狂跳,几乎要冲破胸腔!
她强压下翻腾的气血,没有丝毫犹豫,如同一条滑溜的泥鳅,将身体压到最低,侧着身,用尽全身力气,从那道狭窄的缝隙中拼命向外挤去!
后背溃烂的伤口狠狠摩擦在冰冷粗糙的门框边缘,带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她眼前一黑,差点晕厥过去!
但她死死咬住舌尖,尖锐的疼痛刺激着她保持清醒!
身体被挤压着,一寸、一寸地向外挪动!
破碎的布袍被门框挂住,发出轻微的撕裂声。
冰冷的雨水混合着汗水,糊了她满脸。
终于!
她像一尾终于挣脱了渔网的鱼,猛地从那条狭窄的缝隙中滑脱出来,重重地摔倒在回廊冰冷湿滑的青石板上!
冰冷的雨水瞬间将她浇透,却也带来一种劫后余生的、近乎虚幻的清醒!
她贪婪地呼吸着带着雨腥味的空气,肺部火辣辣地疼。
回廊拐角处,那两个看守的交谈声还在继续,被风雨声模糊着。
沈灼趴在地上,浑身泥泞血污,如同从地狱最深处爬出来的恶鬼。
她抬起头,看向回廊尽头那片被风雨肆虐的、无边无际的黑暗天空。
冰冷的雨水冲刷着她脸上的血污和泪痕,却冲不散她眼底那如同野火般燃烧的、冰冷的疯狂和决绝。
她手脚并用地爬起来,没有丝毫停留,像一道融入夜色的影子,踉跄着、却又无比坚定地,扑向了高墙下那片被风雨掩盖的、更加浓重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