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欲老板深夜敲门听说我不行?冰冷林彻完结版小说_完结版小说禁欲老板深夜敲门听说我不行?(冰冷林彻)
我误把闺蜜吐槽老板的语音发进了公司总群。 语音里详细描述了他不行的细节,以及我添油加醋的嘲笑。 一分钟后,系统提示:管理员开启了全员禁言。 深夜,门铃狂响。 监控显示,那位被公开处刑的老板正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拎着红酒,眼底猩红。
开门,他哑声说,我们来验证一下到底行不行。手机像个烫手山芋,从我瞬间汗湿的指间滑落,“咚”地一声砸在柔软的地毯上,闷响如同丧钟。屏幕上,那个置顶的、平时死气沉沉此刻却无比恐怖的公司总群“[创达科技·全员奋进群]”里,最后一条消息,是我刚发出去的那条长达59秒的语音。绿色的进度条刺得我眼睛生疼。
下面紧跟一条系统提示,冰冷彻骨:管理员“Leo”已开启全员禁言Leo。林彻。
我的老板。那个在语音里,气详细吐槽了十分钟他如何“中看不中用”、“白瞎了那副公狗腰和帅脸关键时候居然不行!
”、以及我是如何疯狂添油加醋、笑得捶桌附和的——男主角。时间凝固了。空气被抽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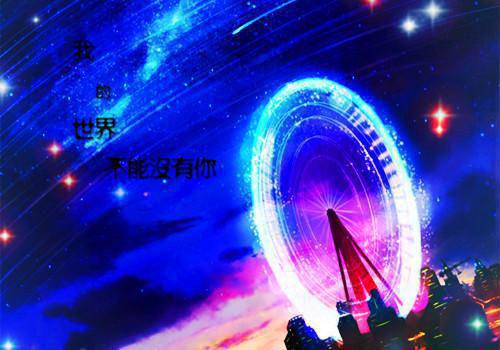
我听见自己心脏疯狂砸在胸腔里的声音,咚,咚,咚,下一秒就要从喉咙里跳出来。完了。
职业生涯,社交生命,一切的一切,都在这一秒里,彻底崩塌毁灭。“撤回!对!撤回!
” 我像是濒死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手指颤抖得几乎握不住手机,疯狂点击那条语音。
屏幕上弹出一个冷漠的灰色提示:超过2分钟的消息无法撤回。绝望的海水没顶而过,冰冷刺骨。群里死寂一片。三百多人的死寂。那种静默,比任何爆炸性的刷屏都更令人恐惧。
我能想象到屏幕后面,三百多张惊愕、憋笑、幸灾乐祸、等待着狂风暴雨的脸。
手机开始疯狂震动。屏幕上“苏晓”的名字不断跳跃。我接起来,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喂?”“姜薇!你疯了?!你发哪儿去了?!那是总群!
总群啊我的祖宗!”苏晓的尖叫几乎刺破我的耳膜,背景音里是她同样慌乱的跺脚声,“我刚发现我描述他西装纽扣扣错了的细节是不是太具体了?他肯定知道是我说的了!
完了完了!咱俩一起完了!”我张了张嘴,发不出任何声音。
眼前闪过林彻那张脸——平时总是没什么表情,眼神锐利,看人时带着一种冷静的审视,偶尔在会议上被蠢货气到,嘴角会勾起一丝极淡的冷笑,足以让整个部门噤若寒蝉。
那样一个极度注重效率、威严、且显然……自尊心极强的男人。“晓晓,”我干涩地吞咽了一下,喉咙疼得厉害,“我可能……得准备投简历了。”“投简历?
你以为辞职就完了?
林彻那个人……他那副样子像是会轻易放过公开处刑他……他那方面的人?
”苏晓压低了声音,带着哭腔,“我不管,你得跑路!立刻!马上!
买张机票飞非洲避难去吧!”电话是怎么挂断的,我不知道。我瘫在沙发上,像一条被扔上岸濒死的鱼。
关于林彻的一切:他雷厉风行地开除掉办事不力的高管;他面无表情地否决掉几个亿的方案,让对方老板下不来台;他那个“冷面阎罗”的绰号……以及苏晓,作为他短暂相亲对象的苏晓,回来跟我拍着桌子狂笑吐槽的每一个细节。
“……看着人模狗样吧?结果呢?高级餐厅吃一半接个工作电话就跑了!跑、了!
连句人话都没有!后续?没后续!微信都是我主动加的他,发十句回一个‘嗯’,这种男人不就是不行是什么?绝对有问题!”我当时是怎么笑着接话的?“噗,果然资本家都是冰冷的赚钱机器,莫得感情也莫得功能哈哈哈……”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此刻精准地回刺在我每一根神经上。时间一分一秒地爬行,每一秒都是凌迟。微信群再无任何动静,像一座巨大的、沉默的坟墓。
公司邮箱也安静得诡异。没有电话,没有质问。这种暴风雨前的死寂,几乎要把我逼疯。
我不敢想象公司里现在正上演着怎样的暗流涌动。也许私聊群里已经炸开了锅,也许有人截了图,也许……夜幕降临,我窝在沙发里,不敢开灯,不敢点外卖,甚至不敢去卫生间。任何一点声响都让我惊跳起来。手机屏幕暗下去,我又立刻按亮,徒劳地期待着也许下一秒这一切都会消失,被告知只是一个恶劣的玩笑。但什么都没有。
晚上十一点。窗外城市的霓虹模糊成一片冰冷的光晕。我蜷缩着,眼皮沉重,神经却紧绷得像一根拉到极致的弦,稍微一碰就会断裂。
就在这时——“叮咚——叮咚叮咚叮咚!”急促到几乎疯狂的门铃声炸裂了死寂的空气!
我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心脏瞬间飙到一百八,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冲到了头顶,又瞬间褪得干干净净,手脚冰凉。谁?!这个时间点?这种按铃的方式?
一股巨大的、几乎让我窒息的恐慌感攫住了我。我连滚爬爬地冲到玄关,手指抖得不像话,几乎是摸了好几次才摸到智能门锁的显示屏开关。屏幕亮起。幽暗的楼道灯光下,一张熟悉又无比恐怖的脸,占据了整个监控画面。林彻。
他穿着白天那件一丝不苟的黑色衬衫,最上面的扣子却解开了两颗,领带扯松了,斜斜地挂着。头发不似平日整齐,几缕垂落在额前。他微微垂着头,看不清全脸,但紧绷的下颌线透着一股骇人的压迫感。而他的手里……竟然拎着一瓶红酒。然后,他像是感应到我的注视,猛地抬起头。监控屏幕里,那双眼睛,透过冰冷的电子屏幕,直直地“钉”住了我。眼底是骇人的猩红。像是熬了夜,又像是压抑着某种即将彻底失控的疯狂风暴。他凑近门禁麦克风。嘶哑的,带着一丝酒精灼烧般的质感,却又冰冷得不容置疑的声音,透过门板传了进来,每一个字都砸在我的心跳上:开门,他顿了一下,那猩红的眼底掠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近乎残忍的笑意。我们来验证一下到底行不行。
……我的呼吸停了。血液凝固了。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巨大的、轰鸣的恐慌。他知道了。
他当然知道了。他找上门了。带着酒。在深夜十一点。用这种可怕的方式。验证?验证什么?
怎么验证?
幕一样在我脑海里疯狂滚动:“不行”、“中看不中用”、“莫得功能”……“不……不开!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尖利得变调,后背死死抵住冰凉的门板,仿佛这样就能挡住门外那尊煞神,“林总!你……你喝多了!请你离开!
不然我……我报警了!”门外沉默了一瞬。然后,传来一声极轻、极低的嗤笑。
比直接的威胁更让人毛骨悚然。“报警?”他的声音依旧沙哑,慢条斯理,“好啊。
正好让警察同志听听,我的员工是如何在几百人的群里,散布关于我的……不实谣言,进行人身攻击和名誉损害的。”“……”我瞬间失声。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姜薇。
”他叫我的名字,不再是公式化的“小姜”或者全名,而是某种带着齿尖摩擦感的语调,听得我脊背发凉,“我给你三秒钟。”“要么,你自己开门。”“要么,”他顿了顿,像是用指节在门板上不轻不重地叩了一下,“我可以用我的方式进来。提醒你一下,我刚好认识一个开锁很快的朋友。”酒精的味道,混合着他身上那股熟悉的、冷冽的雪松古龙水气味,似乎已经透过门缝钻了进来,无孔不入。
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绕住我的心脏,越收越紧。他是认真的。这个状态下的林彻,什么都做得出来。公开社会性死亡,和私下面对一头发疯的野兽?我哪个都不想选!“一。
”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重锤砸下。我浑身一颤。“二。”速度很快,毫无停顿。
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终结意味。我绝望地闭上眼睛,眼泪不争气地涌了出来。
手下意识地摸向了门把手。抖得不像话。那声“三”落下的瞬间。“咔哒。”门锁开了。
我猛地向后退开,仿佛打开的是潘多拉的魔盒。门被从外面不疾不徐地推开。
林彻高大的身影几乎堵住了整个门框,遮断了楼道里所有的光,投下巨大的、压迫感十足的阴影。
他身上那股混合着酒气和冷冽香气的味道更加清晰地扑面而来。他一步跨了进来。反手,“砰”地一声重重关上了门。那声响让整个玄关都震了震,也让我跟着剧烈地一抖。
密闭的空间里,只剩下我和他。空气瞬间变得稀薄而滚烫。他就那样站在我面前,微低着头,猩红的眼睛死死攫住我,像盯着猎物的猛兽。手里的那瓶红酒瓶身,在昏暗的光线下折射出幽冷的光。我僵在原地,动弹不得,连呼吸都忘了。他微微眯起眼,目光从我惨白的脸,滑到我因急促呼吸而起伏的胸口,最后落回我恐惧的眼睛。然后,他极其缓慢地,扯起一边嘴角,勾起一个毫无温度、甚至有些残忍的弧度。“现在,”他哑声开口,每一个字都裹挟着浓重的酒意和危险的气息。“实验开始。
”时间像是被冻住了。玄关顶灯惨白的光线落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让那双猩红的眼睛显得更加深不见底,里面翻滚着我完全看不懂的情绪。不是单纯的愤怒,更像是一种被彻底挑衅后、理智崩断、混杂着某种疯狂和毁灭欲的风暴。他向前逼近一步。
我尖叫一声,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向后弹去,后背重重撞在冰冷的鞋柜上,撞得上面的钥匙筐哗啦作响。“林总!你冷静点!”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双手胡乱地在身前挥舞,试图挡住他,“这是犯法的!私闯民宅!我……我真的会报警!
”他像是听到了什么极其可笑的话,喉咙里滚出一声低沉的、沙哑的哼笑。又逼近一步。
那股强大的、带着酒意的压迫感几乎让我窒息。我被迫仰头看着他,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男女之间力量的悬殊。“犯法?”他慢条斯理地重复,目光像冰冷的触手滑过我的脸颊,“比起你在三百二十七人面前诽谤顶头上司……哪个更严重?嗯?姜、薇?”最后一个名字,他几乎是咬着牙根念出来的,带着滚烫的呼吸,喷在我的额头上。我浑身一颤,牙齿开始不受控制地咯咯作响。
“我……我不是故意的……是手滑……”眼泪毫无预兆地滚落,是吓的,也是绝望的,“对不起……林总,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了……”语无伦次。除了求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手滑?”他挑眉,那双眼睛里的血色似乎更重了些,“五十九秒的语音,手滑得可真够久的。”他抬起拿着酒瓶的那只手。我吓得猛地闭上眼,缩起脖子,以为他要动手。预想中的疼痛没有到来。只听“咚”的一声闷响,是酒瓶被重重搁在鞋柜上的声音。紧接着,我的手腕被一只滚烫干燥的大手猛地攥住!“啊!
”我惊叫着想挣脱,那力道却大得惊人,像铁钳一样箍着我,轻易地将我的胳膊拉开,按在了身体两侧。他另一只手撑在了我耳边的鞋柜上,彻底将我困在了他和冰冷的柜子之间。
无处可逃。“不是分析得头头是道吗?”他低下头,鼻尖几乎要碰到我的,灼热的呼吸交织着浓烈的酒气,铺天盖地地将我笼罩,“不是笑得很大声吗?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像粗糙的砂纸磨过心脏最脆弱的薄膜。“现在怕了?”我拼命摇头,眼泪流得更凶,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恐惧像冰冷的潮水,从脚底一路蔓延到头顶。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胸膛传来的热量,以及那之下蕴含的、随时可能爆发的可怕力量。
“我……我胡说八道的……林总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计较……”我哭得喘不上气,所有的骄傲和体面在这一刻碎得干干净净。“胡说八道?”他重复着,眸色深沉得可怕,里面仿佛有黑色的漩涡在搅动,“但我这个人,不喜欢被冤枉。
”他攥着我手腕的力道收紧了几分,疼得我抽气。“特别是,”他顿了顿,目光极具侵略性地扫过我的嘴唇,锁骨,最后再次锁死我的眼睛,声音哑得不成样子,“这种关乎男人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随即更加疯狂地擂动。
他想干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
验证……他刚才说的验证……巨大的恐慌让我开始不管不顾地挣扎,膝盖下意识地就想往上顶!他似乎早预料到我的动作,身体猛地前倾,用腿和身体的重量轻易地将我死死压制在鞋柜上,动弹不得。绝对的力量压制。
绝望瞬间灭顶。“放开我!混蛋!人渣!!”我口不择言地哭骂,试图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他,声音却因为恐惧而破碎不堪。他却像是被我的骂声取悦了,嘴角那丝冰冷的弧度加深了些许。“骂,继续骂。”他低下头,滚烫的唇几乎要贴上我的耳廓,灼热的气息钻进我的耳蜗,引起一阵剧烈的战栗,“等你验证完了……再告诉我,我到底行、不、行。”最后一个字音落下,他猛地松开了钳制我手腕的手。在我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的瞬间,那只大手却毫不犹豫地探向——我的睡衣领口!
粗糙的指尖不可避免地触碰到颈侧细腻的皮肤,带着烫人的温度,和不容抗拒的力道。
“不——!!!”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尖叫,所有的血液似乎都冲向了大脑,眼前一阵发黑。
就在我以为下一秒就要彻底崩溃的时候。
“嘀嘀嘀——嘀嘀嘀——”一阵刺耳突兀的手机铃声,像一把尖刀,猛地劈开了这浓稠得令人窒息的氛围。是他的手机。响得锲而不舍,尖锐急促,在死寂的、只有我粗重喘息和哭泣声的玄关里,显得格外惊心动魄。林彻的动作顿住了。
他撑在我耳侧的手握紧了拳,手背上青筋暴起。他闭了闭眼,眉心拧成一个深刻的川字,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像是在极力压制着什么。那铃声还在响,一遍又一遍,带着一种不接不通的执拗。他眼底那片骇人的猩红和疯狂的风暴,像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干扰硬生生打断,出现了一丝短暂的凝滞和挣扎。几秒后,他极其缓慢地、极其僵硬地,松开了对我领口的钳制。身体向后微退,给了我一丝喘息的空间,但那双眼睛依旧死死地盯着我,充满了未散的欲念和暴戾,以及被强行中断的极度不耐。他深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吐出,胸口剧烈起伏。然后,他伸手从西裤口袋里掏出了手机。看也没看来电显示,直接划开接听,放到耳边。
声音沙哑得可怕,带着毫不掩饰的戾气:“说!”我瘫软在鞋柜上,像一条脱水的鱼,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泪还在不受控制地往下流,被他触碰过的皮肤像被烙铁烫过一样,残留着惊心动魄的触感。劫后余生的虚脱感席卷而来,但我丝毫不敢放松,警惕地、恐惧地看着他。电话那头似乎说了什么。林彻的眉头越皱越紧,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什么时候的事?”他冷声问,语气依旧很差,但那种针对我的、可怕的压迫感似乎收敛了一些,转变成了另一种烦躁。“……知道了。
”他沉默了几秒,极其不耐地吐出三个字,“马上到。”他挂了电话。
拇指和食指用力捏了捏眉心,然后,他抬起头。那目光再次落在我身上。复杂,深沉,翻涌着无数未竟的念头和依旧滚烫的余烬。像是在权衡,在挣扎。我吓得又是一个哆嗦,下意识地抱紧了自己。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五秒。那五秒,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最终,他像是极其艰难地做出了决定。嘴角扯起一个冰冷的、意味深长的弧度。“可惜了。
”他哑声说,目光像带着钩子,从我凌乱的衣领口一扫而过。“实验暂停。”他站直身体,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扯松的领带和衬衫袖口,恢复了那么一丝平日里衣冠楚楚的模样,虽然眼底的猩红和身上的酒气依旧昭示着他的反常。他拿起鞋柜上那瓶未开的红酒,在我惊恐未定的目光中,转身。手握上门把。“砰。”又是一声轻响。门开了,又关了。
他走了。如同来时一样突兀。我顺着鞋柜滑坐在地毯上,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只剩下无法抑制的剧烈颤抖和劫后余生的冰冷。玄关恢复死寂。
只有空气中残留的雪松与酒液混合的危险气息,颈侧皮肤上鲜明的触感,还有鞋柜表面被他手掌按过留下的细微湿痕,证明着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切,不是我的噩梦。
我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很久很久,都无法动弹。直到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显示苏晓发来的无数条询问后续的消息,我才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蜷缩起来,把脸深深埋进膝盖里。无声的眼泪,瞬间浸湿了睡裤。第二天早上,我是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和肿得像核桃一样的眼睛到的公司。
每一步都走得如同踩在刀尖上。从踏进办公楼大门的那一刻起,我就被各种或明或暗的视线包裹了。窃窃私语声在我经过时骤然响起,又在我走远后死灰复燃。那些目光里,有同情,有好奇,有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还有赤裸裸的看戏意味。我低着头,恨不得把脸埋进胸口,快步走向我的工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