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灭我满门,留我做他的皇后萧彻萧彻最新小说推荐_完本小说免费阅读他灭我满门,留我做他的皇后(萧彻萧彻)
素面端上来的时候,我胃里一阵翻搅。白瓷碗,清汤寡水,几根面条软趴趴地卧着,上面飘着两片蔫黄的菜叶。和我家被血洗那天,厨房灶台上放的那碗,一模一样。
“皇后怎么不吃?”萧彻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玩味。
他今天在宫宴上特意点了这道面。满殿的丝竹管弦都停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钉在我身上。
那些目光里有好奇,有怜悯,更多的是看好戏的刺探。我拿起银筷。手指捏得很紧,指节泛白。筷子尖碰到面条,挑起一根。滑溜溜的,像冰冷的蛇。“陛下记得很清楚。
”我开口,声音出乎意料地稳,甚至带了点笑,“连一碗面都记得分毫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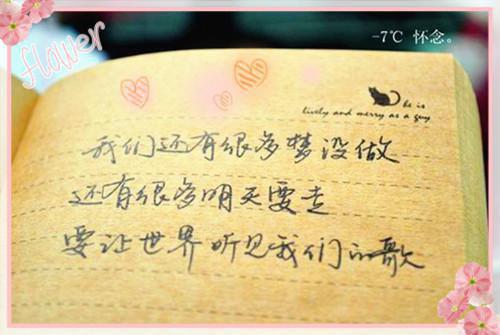
”萧彻靠在高高的龙椅上,玄色龙袍衬得他面容冷峻。他唇角微勾:“自然记得。那晚,令尊文太傅,可是连这碗面都来不及尝一口。”一股腥甜涌上喉咙。我死死咬住后槽牙。
我姓文,单名一个皎字。皎洁的皎。爹娘取的,盼我一生光明磊落。现在,这个字像个笑话。
坐在金銮殿上,穿着皇后的凤袍,脚下踩着文家一百三十七口人的血。而坐在我身边,给我点这碗素面的男人,萧彻,当朝天子,是我家满门血案的元凶。也是我的夫君。两年前。
京城的天,是灰蒙蒙的。爹下朝回来,脸色比天还灰。“皎儿,收拾细软,今晚送你出城。
”他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从未有过的疲惫。“爹,怎么了?”我心头狂跳。爹是太傅,两朝元老,门生故旧遍天下。我从没见过他这样。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有不舍,有决绝:“陛下……疑心太重了。爹,怕护不住你们了。”新帝萧彻登基不到一年。
手段狠辣,雷厉风行。朝堂上已经清洗了好几拨。爹一直中立,却还是被卷了进去。那晚,我没走成。刚收拾好包袱,前院就传来巨响。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喊杀声、惨叫声、刀剑碰撞声,瞬间撕裂了夜晚的宁静。娘把我死死按在床底下。“皎儿,别出声!记住,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她的眼泪滚烫,滴在我脸上,声音抖得不成样子。透过床底的缝隙,我看到爹穿着中衣,手里只拿着一把平时练字裁纸的小刀,冲了出去。火光映着他花白的头发和挺直的背影。
然后,是无数沉重的脚步声冲进内院。娘被拖了出去。我听见她凄厉的喊:“皎儿——!
”那声音像一把钝刀子,反复割着我的耳朵。我捂住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尝到铁锈味。
眼泪流干了,只剩下火烧一样的痛。外面安静了很久。我像个鬼一样,从床底爬出来。
院子里全是血。黏稠,暗红,在火光下泛着诡异的光。
空气里是浓得化不开的铁锈味和焦糊味。爹倒在书房门口,那把裁纸刀还紧紧握在手里,眼睛瞪得很大。娘倒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头发散乱,手指还朝着我藏身的方向伸着。
到处都是尸体。熟悉的管家伯伯,教我绣花的嬷嬷,看门的老忠叔,跑腿的小厮柱子……他们的脸,我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全没了。整个文府,静得像座巨大的坟墓。只有火舌舔舐木头发出的噼啪声。我像个木偶,在血泊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走到厨房门口。灶台上,放着一碗没动过的素面。
还冒着一点点热气。那是爹晚上饿了,吩咐厨房准备的。一个穿着玄色铁甲的将领走过来,靴子踩在血水里,发出令人作呕的声响。他脸上溅着血,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文大小姐?
”他声音冰冷。我抬起头,脸上大概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我没说话。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像在看一件物品。“陛下有旨,文氏谋逆,满门抄斩。唯留文氏女皎,押送进宫。
”谋逆?抄斩?我爹一生清正,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
巨大的荒谬感和恨意瞬间冲垮了残存的理智。我猛地扑向旁边一个士兵腰间的佩刀。
“我要杀了他——!”那将领动作更快,一把擒住我的手腕,力道大得几乎捏碎骨头。
他眼神里露出一丝不耐:“带走!”我被粗暴地拖出文府。身后,是冲天的大火,吞噬着所有我熟悉的一切。我最后看了一眼那碗孤零零的素面。宫里的日子,像被浸在冰水里。我被关在一间僻静的宫室里,有宫女看守,形同囚犯。
她们叫我“文姑娘”,眼神躲闪,带着恐惧和怜悯。萧彻没杀我。他在等什么?
欣赏我的痛苦?半个月后,一道圣旨下来,封我为“皎嫔”。太监尖细的嗓音宣读圣旨时,我跪在冰冷的地上,指甲抠着地面,抠出血痕。嫔?灭门仇人给的封号?
我恨不得撕了那卷明黄的绸布!当晚,我被“请”到了萧彻的寝宫——承乾宫。红烛高烧,锦帐重重。一派新婚的喜庆,在我眼里,全是刺目的讽刺。萧彻坐在龙床边,没穿龙袍,只着一身墨色常服。他挥退了所有宫人。殿内只剩下我们两人,死一般的寂静。他看着我,目光沉沉的,像深不见底的寒潭。“恨朕?”他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帝王的威压。
我抬起头,直视着他。恨?这字眼太轻了。“陛下留我一命,是想让我叩谢天恩?
”我声音嘶哑,每个字都像从齿缝里挤出来。他站起身,一步步走近。
他身上有淡淡的龙涎香,混合着一种冰冷的戾气。“文太傅不识时务,自取灭亡。
”他停在我面前,居高临下,眼神里没有丝毫温度,“清理门户罢了。”清理门户?!
我全身的血液都冲到了头顶,烧得我理智尽失。我猛地拔下头上的银簪,用尽全身力气朝他心口刺去!“畜生!”萧彻眼神一厉,轻而易举就攥住了我的手腕。
他的手像铁钳,捏得我骨头咯咯作响。银簪“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他另一只手猛地掐住我的脖子,将我狠狠掼在旁边的柱子上。后背撞得生疼,窒息感瞬间涌上。“想报仇?”他凑近我,冰冷的呼吸喷在我脸上,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文皎,你文家死绝了,就剩你一个。拿什么跟朕斗?用这双眼睛瞪着朕吗?”他手指收紧,我眼前发黑,肺里的空气一点点被抽干。“朕留着你,是给你机会。”他声音低沉,带着一种残忍的玩味,“让你活着,看着朕坐稳这江山,看着朕开创盛世。
让你这个文家唯一的血脉,日日夜夜,都活在朕的阴影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松开手。我像破布一样滑落在地,剧烈地咳嗽,大口喘气。“记住你的身份。
”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转身走向龙床,“做你该做的事。”那天晚上,是我人生的炼狱。
身体被撕裂的痛,远不及心里的万分之一。每一次触碰,都像在文家的血泊里打滚。
我死死咬着嘴唇,直到满口血腥,不让一丝屈辱的声音泄露出来。黑暗里,萧彻的声音毫无波澜:“哭出来,或者求饶,或许朕会轻点。”我闭上眼,把所有的眼泪和嘶吼都吞回肚子里。爹,娘,皎儿不孝。但皎儿会活着。活着,才有机会。
日子变成了一种机械的重复。萧彻偶尔会来我的“皎月宫”。大多时候是深夜,带着一身酒气或者寒气。他不会多说什么,粗暴地行使他作为帝王的权力,然后离开。
我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承受着。宫里的人渐渐摸清了风向。我这个“皎嫔”,有名无实,不过是陛下圈养的一只鸟雀,随时可能被捏死。看我的眼神,也从最初的恐惧怜悯,变成了彻底的轻视和怠慢。份例被克扣是常事。冬日里的炭火总是不够,送来的饭菜也常是冷的、馊的。宫女太监们当着我的面就敢嚼舌根。“神气什么?
全家都死绝了,也就剩个空壳子。”“嘘!小声点!好歹顶着个嫔位呢。”“嫔位?嗤,陛下怕是连她名字都记不住吧?要不是那张脸……”“脸?我看也快熬成黄脸婆了!
天天死气沉沉的,晦气!”我坐在窗边,听着外面毫不掩饰的议论,手指在冰冷的窗棂上划过。疼吗?早麻木了。活下去。这是唯一的念头。
我开始留意宫里的动向。像个幽灵一样,在允许的范围内,观察着一切。耳朵竖起来,捕捉着每一丝可能有用的信息。萧彻根基未稳。他登基手段狠辣,朝中老臣表面臣服,暗地里怨声载道。太后,他的生母,似乎也对他有些不满。尤其在他大肆清洗朝堂,牵连甚广之后。太后礼佛,喜静,住在宫苑深处的慈宁宫。这是一个机会。我开始抄佛经。
用最虔诚的态度,最工整的小楷。抄《心经》,抄《金刚经》,抄《地藏菩萨本愿经》。
然后,在合适的时机,托人“不经意”地送到慈宁宫去。送佛经的宫女,是我观察很久,确认与慈宁宫一位老嬷嬷有同乡之谊的。起初,石沉大海。我不急。继续抄。日复一日。
两个月后,慈宁宫传来话。太后见我抄的佛经“心诚”,允我初一十五去慈宁宫小佛堂上香。
第一步,成了。第一次踏进慈宁宫,檀香袅袅,庄严肃穆。太后坐在上首的软榻上,穿着一身深紫色常服,面容平和,眼神却锐利。我恭敬地行礼,低眉顺眼,不多说一个字。
上香,跪拜,然后安静地侍立在一旁。太后问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无非是“在宫里可还习惯”、“身子如何”之类的。我答得滴水不漏,只流露出恰到好处的恭谨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哀家听闻,你父亲文太傅,生前也是饱读诗书之人。”太后忽然话锋一转,目光落在我脸上。我心头猛地一跳,随即垂得更低:“是。家父……一生清正。”“清正?”太后捻着佛珠,声音听不出情绪,“清正之人,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我抬起头,眼眶瞬间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肯落下。声音带着无法掩饰的哽咽和茫然:“臣妾……不知。
雷霆雨露,俱是君恩。臣妾只恨……恨自己未能承欢父母膝下尽孝……”我适时地停住,肩膀微微颤抖,将一个家破人亡、惶恐无助又强忍悲痛的孤女形象,演得入木三分。
太后的眼神在我脸上停留片刻,那锐利似乎淡了些,化作一丝复杂。她摆摆手:“罢了。
过去的事,莫要再提了。你既到了哀家这里,就安心礼佛吧。也算为你父母……积些福报。
”“谢太后恩典。”我伏地叩首,眼泪终于滑落,滴在冰冷的地砖上。这一次,泪里有真切的悲,也有得逞的冷。萧彻对我的“安静”似乎有些意外。他来皎月宫的次数,反而多了一点。虽然依旧沉默寡言,眼神却会在我抄经或者侍弄花草时,停留片刻。
他在审视我。像看一只被拔了爪牙的困兽,能翻出什么浪花。机会很快来了。
宫里的张贵妃有孕了。她是兵部尚书之女,入宫早,位份高,性格跋扈。仗着身孕,更是气焰嚣张,连皇后都不放在眼里。一日御花园赏花,我远远地避在角落。
张贵妃却由宫人簇拥着,径直朝我这边走来。她穿着绯红的宫装,腹部微微隆起,下巴抬得高高的。“哟,这不是皎嫔妹妹吗?躲在这里做什么?”她声音又尖又利,满是刻薄,“也是,孤家寡人的,看着别人有孕承欢,心里不好受吧?
”周围的宫女太监都低下头,不敢出声。我屈膝行礼,声音平淡:“贵妃娘娘万福。
臣妾只是在此赏景,不敢打扰娘娘雅兴。”“赏景?”张贵妃嗤笑一声,目光像毒蛇一样在我平坦的小腹上扫过,“景有什么好赏的?人呐,得看命!有些人,就是没那福气,生来就是孤星克亲的命,连累全家不说,自己也是个不下蛋的……”“孤星克亲”四个字,像针一样狠狠扎进我心里。
文家一百三十七口的冤魂在耳边咆哮。我猛地抬起头,死死盯住她。
张贵妃被我眼中的狠厉惊得后退一步,随即恼羞成怒:“你看什么看?!难道本宫说错了?
你全家不就是死绝了吗?一个罪臣之女,也敢瞪本宫?!来人!给本宫掌嘴!
”她身边的嬷嬷立刻上前一步,扬手就要打下来。电光火石间,我看到旁边假山石后明黄色衣角一闪。是萧彻!他竟在附近!一个大胆的念头瞬间成型。
就在嬷嬷的巴掌即将落下的瞬间,我没有躲闪,反而往前踉跄一步,像是被推搡了一下,整个人朝着张贵妃的方向倒去!“啊——!”张贵妃发出惊恐的尖叫。
我“恰好”撞在她身上,力道不大,却足以让她重心不稳。她惊慌失措地向后倒去,下意识地想抓住什么,慌乱中手推了我一把。在外人看来,就是我扑过去撞她,她为了自保推开了我。“娘娘!”宫女们尖叫着扑上去扶张贵妃。而我,被她那一推,身体失去平衡,狠狠撞向旁边的石桌角!“砰!”一声闷响。小腹传来一阵剧痛。
我顺势摔倒在地,蜷缩起来,痛苦地呻吟。“皎嫔!”萧彻低沉的声音带着怒意响起。
他从假山后大步走出,脸色铁青。所有人都吓得跪倒在地。“陛下!是她!是她故意撞臣妾!
”张贵妃被扶起来,惊魂未定地指着我叫嚷,脸色煞白,“臣妾的孩子……孩子……”“闭嘴!”萧彻厉声喝道,目光扫过满地狼藉,最后落在我身上。我捂着肚子,脸色惨白如纸,额头渗出冷汗,身下,有刺目的红色慢慢洇开在素色的裙摆上。太医很快被召来。
诊脉的结果是:“皎嫔娘娘……小产了。受了撞击,龙胎……没能保住。
”整个宫殿一片死寂。我躺在床上,闭着眼,听着太医的话,听着萧彻压抑着怒火的呼吸声。
身下的“血”是提前准备好的鸡血囊。小腹的剧痛是我自己撞桌角撞的,但也足够真实。
张贵妃傻了,瘫软在地,语无伦次:“不可能……我没有……是她自己撞上来的……陛下!
臣妾冤枉啊!”萧彻没理她。他走到我床边,阴影笼罩下来。我睁开眼,泪水无声地流,眼神空洞绝望地看着他,声音轻得像羽毛:“陛下……我们的孩子……没了……” 我艰难地抬起手,似乎想抓住什么,又无力地垂下。那一刻,我在他深不见底的眼眸里,看到了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惊愕?怀疑?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他俯下身,宽厚的手掌带着薄茧,有些僵硬地抚上我满是冷汗的额头。这个动作,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生疏和试探。“疼吗?”他问,声音竟比平日里低哑了几分。
疼?当然疼。身体疼,心更疼。为了演这场戏,我付出的代价不小。但比起文家的血债,这点疼算什么?我闭上眼,泪水流得更凶,嘴唇颤抖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只发出压抑的、破碎的呜咽。这副惨状,足以乱真。萧彻猛地直起身,眼神瞬间恢复了帝王的冷硬,看向瘫软在地的张贵妃,如同在看一个死人。“张氏跋扈善妒,残害皇嗣,罪无可恕!褫夺贵妃封号,打入冷宫!其父教女无方,兵部尚书之职暂免,闭门思过!”雷霆之怒,顷刻降下。张贵妃凄厉的哭喊求饶声被宫人迅速拖远。
殿内再次安静下来。萧彻站在我床边,沉默了很久。空气沉重得让人窒息。“你好生休养。
”他终于开口,语气是惯常的命令式,却似乎又夹杂了一点别的东西。说完,他转身大步离开。直到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殿外,我才缓缓睁开眼。眼底一片冰冷清明,哪里还有半分悲痛绝望。身下的“血”还在蔓延,小腹的钝痛提醒着我刚才的惨烈。
但我心里,却燃起了一簇冰冷的火焰。孩子?我和他的孩子?真是天大的笑话!这场戏,值了。张贵妃倒台,她父亲兵部尚书的势力受挫,朝中格局微妙变化。更重要的是,我在萧彻心里,终于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血仇符号。那瞬间的触碰和问询,证明“小产”这个意外,撬动了他冰冷心防的一道缝隙。哪怕只是一道缝隙,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