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子妃的化学谋略》沈言南胤已完结小说_质子妃的化学谋略(沈言南胤)火爆小说
我一直以为丈夫午夜的疏离,只是我们婚姻渐冷的证据。我错了。致命的不是冷漠,而是他带回来的那股味道。那股味道第一次钻进我鼻子里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死了。现在,我只想亲手把它挖出来,看看它腐烂的样子。1凌晨三点。
门锁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哒”声。他回来了。我躺在床上,身体僵硬,眼睛死死闭着,连呼吸都放到了最轻。黑暗中,我能听到他蹑手蹑脚脱下外套的摩擦声,然后是浴室门被轻轻带上的声音。很快,水声响了起来。就是现在。我像个小偷一样,悄无声息地滑下床。冰冷的木地板冻得我脚心一抽,我赤着脚,一步一步挪到卧室的单人沙发旁。他的黑色大衣就像一头蜷缩的野兽,瘫在那里,带着深夜的寒气。我的心跳得像要砸穿胸口。手抖得不成样子,但我还是伸了出去,抓住了那件大衣冰冷潮湿的衣领。我把它凑到脸前,闭上眼,猛地吸了一口气。
那味道瞬间灌满了我的肺!一股浓到发腻的甜香,像是无数朵夜来香被捣烂后,在阴沟里腐烂发酵,甜得让人恶心。但这还不是全部,在那股腐朽的甜味之下,还藏着一丝铁锈味。不,不是铁锈。是血。是那种干涸了很久的、陈旧的血腥味。
“呕……”我干呕了一下,猛地把大衣推开。脑子里像有根弦,“啪”的一声断了。
两个画面闪电般刺进我的脑海:大学宿舍的门被推开,那股陌生的香水味;冰冷的钢琴键,妈妈那张写满失望的脸。骗子。他在骗我。这味道不对劲,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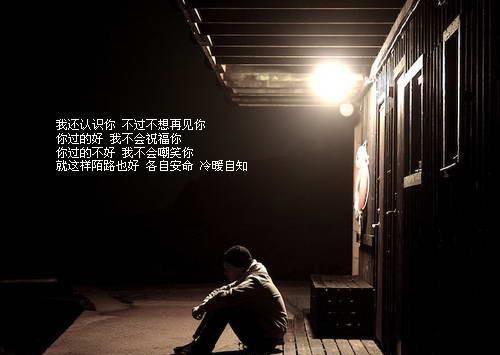
我踉跄着后退,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浑身发抖。水声还在哗哗地响,像是在嘲笑我。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伸出去,在身边的沙发扶手上徒劳地抚摸着,一遍又一遍,试图抚平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褶皱。秩序。我需要秩序。可我的人生已经彻底失控了。
浴室的水声停了。这个认知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我猛地站起来,把大衣扔回原处,连滚带爬地回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黑暗中,我只能听到自己疯狂的心跳声。
我不能再等了。不能再骗自己了。我要知道他去了哪里,见了谁,身上这股鬼味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明天晚上,我就要跟着他。我要亲眼去看,无论看到的是另一个女人,还是地狱。2第二天,天就漏了。豆大的雨点砸在窗户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像无数根手指在急躁地敲击。也好,我想,这样混乱的天气,正好能藏住一个混乱的我。我几乎一整天都在恍惚中度过。给花浇水的时候,水从花盆里溢出来,漫了一地,我却盯着水流发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像生了锈的齿轮,一遍遍地转动:今晚,一切都会有答案。沈夜下班回来时,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他换下湿透的鞋,把滴水的雨伞放在门边,然后给了我一个疏离的拥抱,身上带着好闻的、干净的皂香。我的胃里一阵翻搅。就是这副样子,这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样子,骗了我这么多年。晚上十一点,他像往常一样放下书,说:“我出去一趟。”我点点头,没看他,手指紧紧攥着沙发的扶手,指甲都快嵌进皮质里。
“外面雨大,早点回来。”我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他“嗯”了一声,门开了,又关上。
我立刻从沙发上弹起来,冲到窗边。他的黑色轿车像一头沉默的野兽,滑出车位,汇入雨幕中的车流,很快消失不见。我穿上最不起眼的黑色风衣,平底鞋,抓起一把大黑伞,冲了出去。我没有开车,我怕车灯会暴露我。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车门“砰”地关上,把我关进一个充满着陈年烟味和廉价香薰的狭小空间里。黏腻的皮质座位套紧贴着我的风衣,收音机里嘈杂的流行乐刺得我耳膜生疼。一切都肮脏、混乱、失序。我的家,那个被我打理得一尘不染、连书架上的书都按颜色和尺寸排列的完美空间,此刻感觉像另一个星球。我正从我一手构建的秩序世界,坠入一个无法掌控的、肮脏的未知里。“师傅,别跟太近,”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沙哑,“就在前面那辆黑色轿车后面……隔着两三辆车的距离就好。”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了然的同情。我不在乎。我现在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只想抓住那根能让我沉到底的稻草。车最终停在了一个十字路口。沈夜的车停在最前面,等着红灯。九十秒。我死死盯着他车子的轮廓。他在等谁?那个女人会从哪个方向来?
是坐上他的车,还是他会下车去找她?可他什么都没做。他没有看手机,没有不耐烦地敲击方向盘。他只是……停在那里。然后,我看到了。他微微侧过头,脸朝着路边人行道的方向。那个姿态很奇怪,不是在看什么东西,更像是在……听。
雨声那么大,车流那么吵,他却像置身于一个绝对安静的空间,捕捉着什么遥远的回响。
路灯的光从他侧脸划过,那一瞬间,我发誓我看到了。
他的瞳孔……不是在因为光线变化而收缩,而是在以一种极细微的频率,像雷达一样飞速扩张和扫描。那不是眼睛。那是一个冰冷的感官接收器。
这个念头毫无征兆地窜进我的脑海,我浑身的血液好像瞬间冻住了。被背叛的愤怒,像被一盆冰水迎头浇下,瞬间熄灭,只剩下冰冷的灰烬。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原始、更深刻的恐惧。我一直以为我面对的是一个不忠的丈夫,一个我还能理解的、属于人类范畴的骗子。可眼前这个人,这个我同床共枕了五年的男人,他此刻的姿态,让我感到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陌生和战栗。绿灯亮了。
他的车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开往任何一家酒店,或者高档公寓区。他拐了个弯,驶向了城市的另一端——那个以混乱、老旧著称的西城区。最终,他在一条几乎没有路灯的后巷入口停了下来。巷子口像一张漆黑的巨兽的嘴。他下了车,没有打伞,径直走了进去,高大的身影瞬间就被黑暗吞没了。我的出租车停在街角。
司机问:“小姐,还跟吗?”我看着那个黑洞洞的巷口,雨水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冰冷刺骨。我的手在抖,牙齿在打颤。理智在尖叫,让我快跑,离这个诡异的男人越远越好。
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的新婚之夜。沈夜握着我的手,无比认真地对我说:“晚晚,我们之间,永远不能有谎言。”那句话,曾是我整个世界的基石。现在,基石没了。
他亲手把它砸得粉碎。我的人生已经是一片废墟了。现在,我要走进这片废墟,捡起最锋利的那一块,看看它到底能不能……彻底杀死我。我把钱扔给司机,哑着嗓子说:“不用了。”然后,我推开车门,撑开伞,深吸了一口混合着雨水和霉味的空气,一步一步,走向那条巷子。地狱的门,就在前面。
而我,亲手推开了它。3巷子很窄,像一道被城市遗忘的伤疤。我的伞边刮到粗糙的墙壁,发出刺耳的“沙沙”声。空气里一股酸臭味,是垃圾桶和霉菌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雨水把它搅得更浓,直往我鼻子里钻。这里不像偷情的地方。我的心跳得更快了,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一种说不出的、更原始的不安。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十几步,拐过一个堆满废纸箱的角落。然后,我听到了哭声。不是那种大声的嚎啕,而是一种被压抑到极致的、小兽般的呜咽,断断续续,充满了绝望。巷子尽头,一个穿着单薄连衣裙的女孩蜷缩在墙角,一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捂着脸,整个身体都在剧烈地颤抖。我立刻躲回纸箱后面,心脏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是她吗?
就是她吗?可沈夜没有靠近她。他站在离女孩十几米远的阴影里,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
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肩膀,他却一动不动。然后,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那件让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事情。一缕缕灰色的东西,从那个哭泣的女孩身上飘了出来。它不是烟,也不是水汽。
它更像……更像夏天滚烫路面上的那种热气,但它是灰色的,带着一种看得见的、冰冷的绝望。那些灰色的雾气像有生命一样,在空中盘旋、聚合,然后,朝着沈夜的方向,慢慢地飘了过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
沈夜微微仰起头。他张开嘴,不是说话,只是微微张开。那些灰色的雾气,就像受到了某种无形的吸引力,汇成一股细流,被他……吸了进去。
就在雾气靠近他的一瞬间,一股浓烈的味道顺着湿冷的空气,钻进了我的鼻腔。
就是这个味道!那股浓到发腻的、腐朽的甜香!我的胃在翻江倒海,我干呕了一下,用手死死捂住嘴,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原来不是香水。根本不是什么该死的香水!
这股鬼味道,是……是这个女孩心碎的味道。我浑身的血液都凉了。我看着我的丈夫,那个和我同床共枕了五年的男人,像一个怪物一样,吞噬着另一个人的痛苦。他抬起手,似乎想擦一下嘴角。就在那一刻,巷口昏暗的路灯光,刚好落在他抬起的手腕上。那里,戴着一块银色的手表。那块我送给他的,结婚三周年纪念日手表。
“轰——”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彻底炸开了。
那个戴着我送的信物、代表着我们爱情与时间承诺的男人,和眼前这个以悲伤为食的非人怪物,两个影像以一种最残忍、最荒谬的方式,重叠在了一起。
我以为我会尖叫,会崩溃,会转身就跑。可我没有。我只是像被钉在了原地,无法动弹,无法呼吸,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看到沈夜的脸上,没有丝毫享受或满足的表情。恰恰相反,他的眉头紧紧皱着,脸上是一种无法掩饰的痛苦。他吞咽那些灰色雾气的动作,不像是在进食,更像是在吞咽淬毒的玻璃碎片。他的身体在细微地颤抖,脸色比巷口的灯光还要苍白。他很虚弱。这个认知,比他是个怪物这件事,更让我感到恐惧。
终于,女孩的哭声停了。她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挂掉电话,失魂落魄地站起来,拖着脚步,从巷子的另一头离开了。巷子里只剩下沈夜一个人。他痛苦地弯下腰,喉咙里发出一声被死死压抑住的、不似人类的呜咽。那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空洞,像一头濒死的野兽。然后,他缓缓直起身。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下意识地……朝着我来时的方向,也就是我们家的方向,望了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怪物的残忍,没有捕食者的冷酷。只有一种深可见骨的、想要回家的疲惫。那一瞥,像一把钥匙,瞬间锁死了我所有想要逃跑的念头。一个纯粹的怪物是可怕的。
但一个会将家视为归宿的怪物,是一种无法逃避的、与我命运相连的恐怖。
我的人生已经是一片废墟了。现在,我要回家。我要走到这片废墟的中心,面对面地看着那个亲手摧毁了它的人。我要他亲口告诉我,我嫁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4我比他先到家。我没有脱掉湿透的风衣,水珠顺着衣角滴滴答答地落在玄关的地板上,晕开一小滩一小滩的污渍。我看着它们,第一次没有去拿拖把的冲动。我走到客厅,然后是卧室,书房,厨房,卫生间……“啪”、“啪”、“啪”,我打开了家里所有的灯。
整个屋子被照得通亮,亮得像一个手术台,无影灯下,所有肮脏和病变都无处可藏。
我就站在这片惨白的光线中央,等着。十分钟后,门锁响了。沈夜走了进来,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注意到了这满屋子不正常的灯光。“晚晚,怎么了?”他关上门,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他的头发还在滴水,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那件黑色大衣上,还残留着雨水和巷子里那股腐朽甜香混合在一起的鬼味道。他被我的眼神看得有些不自在,走过来,想碰我的肩膀。我后退了一步。一个很小的动作,却像一道无形的墙,立在我们中间。他的手僵在了半空中。“你……”他似乎想问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巷子里的那个女孩,”我终于开口了,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害怕,“她的眼泪,味道好吗?”这句话像一颗子弹,精准地击中了他。沈夜的身体猛地一震,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他眼中的震惊和慌乱,就像被打碎的玻璃,再也拼凑不起来。“你……你都看到了?”他的声音在发抖。“我看到了灰色的雾,”我一字一句,像在法庭上陈述证词,“我看到你把它们吸了进去。我还闻到了那个味道,那个你每次晚归带回来的,让我恶心想吐的味道。”他张了张嘴,想辩解,想撒谎,但看着我这张没有表情的脸,他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他那副冷静自持的、完美的壳,在我面前,寸寸龟裂。“晚晚,我……”他痛苦地闭上眼,再睁开时,里面已经是一片彻底的绝望。他向后踉跄了一步,靠在了墙上,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
“我是个怪物。”他终于说了出来,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我不是人。我是魅魔。
我们靠吸食人类强烈的情绪为生……悲伤、绝望、痛苦……这些是我们的食物。”魅魔。
这个词砸进我的脑子里,没有引起任何波澜。我的大脑已经停止了思考,只是作为一个接收器,被动地接收着这些荒谬的信息。原来如此。所有的不合理,在这一刻,都有了一个最荒谬、却也最合理的解释。“所以,你从不和我吵架,不是因为你脾气好,”我继续说,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是因为我的愤怒和痛苦,对你来说,也是食物,对吗?你怕不小心……吃了我?”沈夜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他把脸埋进手掌里,发出一声压抑的呜咽。“不……不是的……比那更糟……”他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看着我,那里面是我从未见过的、几乎要溢出来的恐惧和自我厌恶。
“晚晚,你爱我吗?”他哑着嗓子问。我的心猛地一抽。这个问题,比他承认自己是怪物,更让我感到刺骨的寒冷。我没有回答。“你的爱……对我来说,是毒药。”他一字一句,残忍地剖开了最后一个,也是最骇人的真相。“我们魅魔,可以吸收任何负面情绪,唯独爱不行。纯粹的、不求回报的爱,会在我们体内生根发芽,长成……长成一株寄生的藤蔓。”“它缠绕着我的能量核心,越长越密,越收越紧。
你越爱我,它就长得越快。它让我变得虚弱,让我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有效地从外界吸收能量。
我每天晚上出去,吞食那些陌生人的痛苦,可大部分能量都被它吸走了。
我……我正在被你的爱,活活饿死。”“轰——”世界在我耳边炸开了。
我以为我嫁给了一个不爱我的男人,结果,是我太爱他了。我以为我们的婚姻是一场骗局,结果,它是一场缓慢的、用爱意精心布置的谋杀。我以为我是受害者,结果,我才是那个最残忍的凶手。我的人生,我引以为傲的、充满秩序的完美人生,不是一片废墟。
它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笑话。绝望像潮水一样将我们两个人淹没。客厅里亮得刺眼,却比任何黑暗都要冰冷。我们就像两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面对面站着,等待着那注定到来的结局。就在这时,客厅那面巨大的落地窗,毫无征兆地,像水面一样,荡起了一圈涟漪。我和沈夜都惊恐地看了过去。一个穿着剪裁考究的黑色西装的男人,就那么从“水面”里,一步一步,从容地走了出来。他就好像不是走进一个房间,而是走进自家的后花园。他很高,比沈夜还要高,一头银灰色的长发随意地束在脑后,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居高临下的微笑。他走进来的那一瞬间,整个房间的温度骤然下降。
“啧啧啧,”那个男人环顾了一下我们惨白的脸,目光最后落在了虚弱地靠着墙的沈夜身上,“看看这是谁?我们曾经最骄傲的同族,现在居然被一个人类女人的‘爱’,折磨成了这副可怜的样子。”沈夜的瞳孔猛地收缩,他死死地盯着那个男人,声音里充满了戒备和憎恨:“卡戎!你怎么会找到这里!”“你身上的味道太臭了,沈夜,”被称作卡戎的男人嫌恶地皱了皱鼻子,“那股被人类情感污染的、腐烂的甜味,隔着半个城市都能闻到。真是……我们一族的耻辱。”卡戎一步步向我们走来,皮鞋踩在木地板上,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却像踩在我的心脏上。“不过没关系,”他微笑着,露出一口森白的牙,“我会帮你清理干净的。我会把你,连同你体内那株可笑的藤蔓,一起吞噬掉。也算是……废物利用了。”血淋淋的杀意,像冰冷的毒蛇,缠住了我的脖子,让我无法呼吸。我看着卡戎那双不带任何感情的、捕食者般的眼睛,又回头看了看脸色惨白、连站都快站不稳的沈夜。恐惧。极致的恐惧,像电流一样贯穿了我的四肢百骸。我应该尖叫,应该逃跑,应该躲到离这两个怪物最远的地方去。可是,我没有。就在卡戎抬起手,指尖开始凝聚出一团不祥的黑雾时,我的身体,先于我的大脑,做出了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