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命仙途:开局偷了天道的挂(楚寒舟赵虎)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_完结小说逆命仙途:开局偷了天道的挂楚寒舟赵虎
时间: 2025-09-13 14:43:01
幕府外那惊鸿一瞥,如同烧红的烙铁,在我心中烙下了无比清晰焦灼的印记。
扶苏眉宇间那沉郁的忧色,蒙恬沉稳面容下隐约的思虑,都与我知道的那场正在逼近的灾难紧密相连。
回到那堆满简牍的角落,我不再感到茫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巨大压力催逼出的、近乎偏执的专注。
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的目光再次落回那些堆积如山的竹简木牍上。
系统赋予我的,不仅仅是语言,似乎还有对秦朝文书制度一种潜意识的熟悉。
我很快弄明白,我负责的远不止是简单的卒籍核对。
各类经由我们这里汇总、抄录或转呈的文书五花八门:军械损耗报备、粮秣转运记录、各地驿传往来摘要、甚至还有部分刑狱判决的副本。
这里是一个信息的中转站,虽然处理的都是基层琐务,却像毛细血管末梢,能微弱地感知到整个庞大帝国的脉搏。
而信息,正是我能利用的唯一武器。
我开始以一种近乎苛刻的态度对待这些文书。
不再仅仅是机械地核对数字、誊抄记录。
我利用现代数据处理的一些基本逻辑——归类、对比、趋势分析——去审视这些古老的文字。
例如,我会将连续几个月的粮秣消耗记录并排对比,刻意用红赭石在简牍边缘做出极细微的标记,提示某个月份的消耗异常偏高,并在附注的木谒上,用极其恭谨、基于职责的口吻写道:“谨按:七月丙寅批粟米较往月增三成,然同期在营戍卒数录并无显增,疑为转运损耗或批录有误,乞上官明察。”
又或者,看到一份来自遥远郡县的驿传文书,记录着某地降雨导致道路中断,文书延迟。
我会在转呈时,额外附上一片小小的木牍,上面写着:“此件自琅琊传来,历时廿三日。
查同期咸阳至上郡驿传,快马不过旬日可达。
各地驿传速率差异甚巨,紧要军情恐有延误之险,伏请将军留意通传之效。”
我的目的,并非真的要立刻解决这些“问题”。
而是要通过这种看似尽职尽责、实则刻意凸显矛盾的方式,在那些最终会看到这些文书的蒙恬幕僚心中,种下几个关键词:“异常”、“核查”、“信息延误”、“沟通不畅”。
尤其是关于通讯和信息真实性的暗示,我希望它们能像细微的冰针,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那封致命的伪诏传来时,能刺破他们心中可能存在的、对咸阳来令毫无保留的信任。
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且风险暗藏的过程。
我不能做得太明显,不能提出超越我这个身份该有的见解。
每一次附上额外的木谒,我都要反复斟酌措辞,确保它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底层小吏出于对工作的死板认真,甚至带着点急于表现的味道,而非有什么深远的洞察。
偶尔,会有上一级的吏员对我的“多事”投来不耐烦的目光,呵斥我:“林凡,做好分内事便可,何须多此一举!”
每逢此时,我便立刻躬身,做出惶恐状,讷讷地解释:“小人愚钝,唯恐记录有差,误了将军大事……” 姿态放得极低,理由也冠冕堂皇。
多数时候,上级吏员忙于事务,懒得与我这般微末之人计较,嘟囔几句便也作罢。
但我能感觉到,并非所有努力都石沉大海。
有一次,我故意将一份关于边境哨探回报“胡骑异动”的记录,与一份来自咸阳、强调要稳定优先的指令文书放在同一案几上呈送。
几天后,我无意间听到两位幕僚模样的官员低声交谈。
“……近来下面报上的文书,倒是比以往更详实了些,尤其是关于讯息传递和粮秣核验的。”
“嗯,有个叫……林凡的史卒?
似乎颇为细心,几次提示虽是小节,却也并非全无道理。
尤其是关于驿传速差之事,确需留意。”
“哦?
倒是难得。
如今各处皆求稳怕事,肯多费心思者不多了……”我的心跳骤然加速,又强迫自己立刻平静下来。
不能得意,不能引人注目。
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步,甚至可能毫无作用。
但至少,我的名字,以这样一种“细心”、“较真”的印象,极其微弱地进入了更高一层的信息处理者的视野。
这或许在未来某个需要信任的瞬间,能起到一丝作用。
文书这条线布下了,但我深知其力量有限。
那日见到扶苏的状态,让我意识到另一条或许更能触及核心的路径——他的健康与心境。
一个忧思过度、身体孱弱的公子,更容易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做出绝望的选择。
我需要接触医官。
这个机会来得比我想象的要快。
北地风寒,营中时有人染上咳疾。
我那日刻意在整理文书时,不断轻声咳嗽,面色也憋得有些发红。
果然引起了那位曾有一面之缘、名叫石夫的医官的注意。
他背着药囊路过,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
“可是染了风寒?”
他声音平和,带着医者特有的沉稳。
我连忙起身,恭敬地回答:“有劳石夫先生动问,确是有些咳嗽,不妨事。”
他走近些,示意我伸出手腕,搭指诊脉。
他的手指粗糙而温暖。
“脉象浮紧,确是风寒初起。
我予你些柴胡、生姜,自己煎服,莫要加重了。”
“多谢先生。”
我感激地道谢,随即状似无意地感叹,“唉,如今这时节,营中染病者甚多。
听闻就连公子殿下,近日也似有不适,真是令人忧心。”
石夫正在取药的手微微一顿,抬眼看了看我,眼神里多了些审视:“你如何得知?”
我心里一紧,知道这话有些冒失了,连忙解释:“小人前日去幕府呈送文书,远远瞧见公子面色似有倦怠,故而猜测……是小人多嘴了。”
我低下头,做出失言惶恐的样子。
石夫沉默片刻,似乎并未深究,只是淡淡道:“公子乃万金之躯,自有御医调理,非我等可妄议。
管好自身便是。”
他将几味草药包好递给我。
我接过药,却不死心,又压低声音,仿佛只是随口一提:“先生说的是。
只是小人曾听乡间老者言,忧思伤脾,郁结伤肝,久则耗损元气,非药石所能完全奏效。
心结还需心药医,通畅开怀最为紧要……想必公子殿下之恙,亦需宽心静养才是。”
我说得极其模糊,引用的也是民间俗语,完全撇清了自己。
石夫听着,目光再次落在我脸上,这一次,停留的时间稍长了一些。
他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些什么,但我只是一脸诚恳和些许对贵人的天然关切。
最终,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背起药囊转身离开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中忐忑。
我不知道这番话是否起到了作用,是否能在石夫心中留下一点印象。
或许下次他去为扶苏诊视时,会下意识地多留意一下这位公子的心境?
或许会在开具药方时,多加上一句“请殿下宽心静神”的劝慰?
我不知道。
我能做的,只有这些微小到近乎徒劳的尝试。
每一天,我都在文书工作中小心翼翼地埋设我的“钉子”,同时密切关注着任何来自咸阳方向的讯息,任何关于始皇巡幸队伍动向的只言片语。
空气中的紧张感似乎与日俱增。
边境的胡骑骚扰似乎频繁了些,粮秣调动的指令更加急促,各种流言开始在底层军吏中悄悄蔓延,又被迅速压制。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像沙漏般无情。
我知道,那最终的时刻正在逼近。
或许明天,或许下一刻,那改变一切的讯息就会如同丧钟般敲响。
我握紧了手中冰冷的简牍,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
我能做的准备,只有这些了。
扶苏眉宇间那沉郁的忧色,蒙恬沉稳面容下隐约的思虑,都与我知道的那场正在逼近的灾难紧密相连。
回到那堆满简牍的角落,我不再感到茫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巨大压力催逼出的、近乎偏执的专注。
我不能坐以待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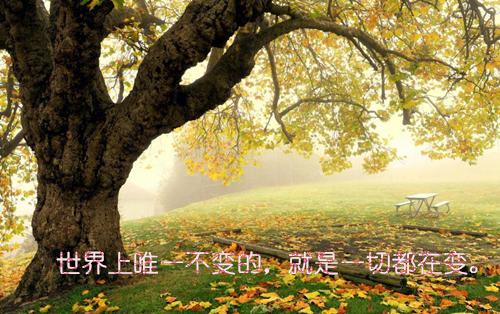
我的目光再次落回那些堆积如山的竹简木牍上。
系统赋予我的,不仅仅是语言,似乎还有对秦朝文书制度一种潜意识的熟悉。
我很快弄明白,我负责的远不止是简单的卒籍核对。
各类经由我们这里汇总、抄录或转呈的文书五花八门:军械损耗报备、粮秣转运记录、各地驿传往来摘要、甚至还有部分刑狱判决的副本。
这里是一个信息的中转站,虽然处理的都是基层琐务,却像毛细血管末梢,能微弱地感知到整个庞大帝国的脉搏。
而信息,正是我能利用的唯一武器。
我开始以一种近乎苛刻的态度对待这些文书。
不再仅仅是机械地核对数字、誊抄记录。
我利用现代数据处理的一些基本逻辑——归类、对比、趋势分析——去审视这些古老的文字。
例如,我会将连续几个月的粮秣消耗记录并排对比,刻意用红赭石在简牍边缘做出极细微的标记,提示某个月份的消耗异常偏高,并在附注的木谒上,用极其恭谨、基于职责的口吻写道:“谨按:七月丙寅批粟米较往月增三成,然同期在营戍卒数录并无显增,疑为转运损耗或批录有误,乞上官明察。”
又或者,看到一份来自遥远郡县的驿传文书,记录着某地降雨导致道路中断,文书延迟。
我会在转呈时,额外附上一片小小的木牍,上面写着:“此件自琅琊传来,历时廿三日。
查同期咸阳至上郡驿传,快马不过旬日可达。
各地驿传速率差异甚巨,紧要军情恐有延误之险,伏请将军留意通传之效。”
我的目的,并非真的要立刻解决这些“问题”。
而是要通过这种看似尽职尽责、实则刻意凸显矛盾的方式,在那些最终会看到这些文书的蒙恬幕僚心中,种下几个关键词:“异常”、“核查”、“信息延误”、“沟通不畅”。
尤其是关于通讯和信息真实性的暗示,我希望它们能像细微的冰针,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那封致命的伪诏传来时,能刺破他们心中可能存在的、对咸阳来令毫无保留的信任。
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且风险暗藏的过程。
我不能做得太明显,不能提出超越我这个身份该有的见解。
每一次附上额外的木谒,我都要反复斟酌措辞,确保它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底层小吏出于对工作的死板认真,甚至带着点急于表现的味道,而非有什么深远的洞察。
偶尔,会有上一级的吏员对我的“多事”投来不耐烦的目光,呵斥我:“林凡,做好分内事便可,何须多此一举!”
每逢此时,我便立刻躬身,做出惶恐状,讷讷地解释:“小人愚钝,唯恐记录有差,误了将军大事……” 姿态放得极低,理由也冠冕堂皇。
多数时候,上级吏员忙于事务,懒得与我这般微末之人计较,嘟囔几句便也作罢。
但我能感觉到,并非所有努力都石沉大海。
有一次,我故意将一份关于边境哨探回报“胡骑异动”的记录,与一份来自咸阳、强调要稳定优先的指令文书放在同一案几上呈送。
几天后,我无意间听到两位幕僚模样的官员低声交谈。
“……近来下面报上的文书,倒是比以往更详实了些,尤其是关于讯息传递和粮秣核验的。”
“嗯,有个叫……林凡的史卒?
似乎颇为细心,几次提示虽是小节,却也并非全无道理。
尤其是关于驿传速差之事,确需留意。”
“哦?
倒是难得。
如今各处皆求稳怕事,肯多费心思者不多了……”我的心跳骤然加速,又强迫自己立刻平静下来。
不能得意,不能引人注目。
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步,甚至可能毫无作用。
但至少,我的名字,以这样一种“细心”、“较真”的印象,极其微弱地进入了更高一层的信息处理者的视野。
这或许在未来某个需要信任的瞬间,能起到一丝作用。
文书这条线布下了,但我深知其力量有限。
那日见到扶苏的状态,让我意识到另一条或许更能触及核心的路径——他的健康与心境。
一个忧思过度、身体孱弱的公子,更容易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做出绝望的选择。
我需要接触医官。
这个机会来得比我想象的要快。
北地风寒,营中时有人染上咳疾。
我那日刻意在整理文书时,不断轻声咳嗽,面色也憋得有些发红。
果然引起了那位曾有一面之缘、名叫石夫的医官的注意。
他背着药囊路过,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
“可是染了风寒?”
他声音平和,带着医者特有的沉稳。
我连忙起身,恭敬地回答:“有劳石夫先生动问,确是有些咳嗽,不妨事。”
他走近些,示意我伸出手腕,搭指诊脉。
他的手指粗糙而温暖。
“脉象浮紧,确是风寒初起。
我予你些柴胡、生姜,自己煎服,莫要加重了。”
“多谢先生。”
我感激地道谢,随即状似无意地感叹,“唉,如今这时节,营中染病者甚多。
听闻就连公子殿下,近日也似有不适,真是令人忧心。”
石夫正在取药的手微微一顿,抬眼看了看我,眼神里多了些审视:“你如何得知?”
我心里一紧,知道这话有些冒失了,连忙解释:“小人前日去幕府呈送文书,远远瞧见公子面色似有倦怠,故而猜测……是小人多嘴了。”
我低下头,做出失言惶恐的样子。
石夫沉默片刻,似乎并未深究,只是淡淡道:“公子乃万金之躯,自有御医调理,非我等可妄议。
管好自身便是。”
他将几味草药包好递给我。
我接过药,却不死心,又压低声音,仿佛只是随口一提:“先生说的是。
只是小人曾听乡间老者言,忧思伤脾,郁结伤肝,久则耗损元气,非药石所能完全奏效。
心结还需心药医,通畅开怀最为紧要……想必公子殿下之恙,亦需宽心静养才是。”
我说得极其模糊,引用的也是民间俗语,完全撇清了自己。
石夫听着,目光再次落在我脸上,这一次,停留的时间稍长了一些。
他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些什么,但我只是一脸诚恳和些许对贵人的天然关切。
最终,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背起药囊转身离开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中忐忑。
我不知道这番话是否起到了作用,是否能在石夫心中留下一点印象。
或许下次他去为扶苏诊视时,会下意识地多留意一下这位公子的心境?
或许会在开具药方时,多加上一句“请殿下宽心静神”的劝慰?
我不知道。
我能做的,只有这些微小到近乎徒劳的尝试。
每一天,我都在文书工作中小心翼翼地埋设我的“钉子”,同时密切关注着任何来自咸阳方向的讯息,任何关于始皇巡幸队伍动向的只言片语。
空气中的紧张感似乎与日俱增。
边境的胡骑骚扰似乎频繁了些,粮秣调动的指令更加急促,各种流言开始在底层军吏中悄悄蔓延,又被迅速压制。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像沙漏般无情。
我知道,那最终的时刻正在逼近。
或许明天,或许下一刻,那改变一切的讯息就会如同丧钟般敲响。
我握紧了手中冰冷的简牍,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
我能做的准备,只有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