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门嫡女:重生之凤鸣九霄(楚倾凰萧夜恒)热门网络小说推荐_免费完结版小说将门嫡女:重生之凤鸣九霄(楚倾凰萧夜恒)
时间: 2025-09-16 01:07:54
建元二年的清明来得早,秣陵城外的柳梢刚抽绿,陶弘景就被父亲陶贞宝拽着上了路。
驴车碾过带泥的石板路,车板上捆着的拓碑工具叮当作响——昨夜州府来人,说城东谢安旧宅的废墟里挖出块残碑,碑上有字,让陶贞宝这等精于古文字的去辨辨。
"阿父,谢家不是早在元嘉年间就败了?
"弘景扒着车帘,看路边扫墓人烧的纸钱灰飘成黄蝶。
陶贞宝正低头磨墨锭,闻言叹了口气:"谢安石当年淝水破敌,何等风光。
可你看这世道,昨日朱门,今日荒冢。
"他把磨好的墨汁倒进瓦砚,"听说那碑是被盗墓贼挖出来的,他们以为谢宅地下有窖藏,结果只刨出这块破石头。
"驴车拐过两道河湾,远远看见一片断垣残壁。
原本该是影壁的地方塌了大半,露出的夯土上还留着箭簇的锈痕。
十几个民夫正围着块半埋的青石碑,见陶贞宝来了,都纷纷让开。
弘景跳下车,一眼就看见碑上的字——不是常见的碑文格式,只有西个擘窠大字,被一道斜劈的剑痕从中间剖开,字迹却仍透着劲挺:"华阳洞天"。
"奇怪。
"陶贞宝蹲下身,手指拂过碑面的青苔,"这字是东晋笔法,可这剑痕......倒像是近年新劈的。
"他从行囊里取出宣纸,刚要覆上去拓印,却发现碑石裂缝里卡着些碎玉——不是殉葬的玉器,是些玉佩残片,上面刻着"谢"字纹。
弘景绕到碑后,看见背面也有字,却是些模糊的星图,北斗七星的位置被人用朱砂重描过。
他伸手去摸那朱砂,指尖刚碰到石面,突然觉得掌心一烫——是那颗星状印记在发热。
与此同时,碑上的剑痕里竟渗出些水珠,顺着字迹往下淌,在地上积成个小小的水洼。
"阿景别乱碰!
"陶贞宝回头看见,忙把他拉开,"这地方阴气重。
"他自顾自地拓碑,宣纸覆在碑上,用软毛刷轻轻拍打着。
弘景却盯着那水洼看——水里没有倒映出天空,反而晃着些奇怪的影子,像有人在水底走动。
日头偏西时,拓片终于干了。
陶贞宝把拓片卷好,对民夫们嘱咐了几句,让他们把残碑暂时搬到附近的土地庙里。
弘景跟在后面,总觉得后背发凉,像有双眼睛在盯着他。
路过一片塌了的游廊时,他踢到个硬东西,弯腰拾起,是面巴掌大的铜镜,镜面蒙着绿锈,镜背刻着缠枝莲纹——看着像是汉代的旧物,不知被哪个盗墓贼遗落在这里。
"阿父你看。
"他把铜镜递过去。
陶贞宝接过,用衣角擦了擦镜面:"这是个老物件,可惜碎了。
"弘景凑过去看,果然见镜面有道裂纹,像被人摔过。
可就在这时,夕阳的光正好照在镜面上,反射的光斑落在弘景额头上。
陶贞宝突然"咦"了一声:"阿景,你额间怎么......"弘景忙摸自己的额头,什么也没摸到。
他抢过铜镜照了照——镜里的自己脸色有些苍白,额间却没有任何东西。
可陶贞宝明明看见,刚才那光斑里,有道淡紫色的痕,像片小小的柳叶,恰好印在眉心偏左的位置。
"许是眼花了。
"陶贞宝摇摇头,把铜镜揣进怀里,"天色晚了,咱们得赶在关城门前进城。
"父子俩刚坐上驴车,弘景突然回头——只见那片断垣后面,不知何时站了个穿青布衫的老人,正望着他们的方向。
可等他揉了揉眼睛再看,老人又不见了,只有那尊残碑在暮色里,像个沉默的影子。
回到家时,己是掌灯时分。
弘景洗漱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总想起那残碑上的字,还有镜中一闪而过的紫痕。
后半夜,他悄悄爬起来,溜到父亲的书房——陶贞宝把拓片放在书案上,还没来得及收进箱底。
弘景借着月光展开拓片。
"华阳洞天"西个字在月下泛着青光,那道剑痕尤其清晰,像是要从纸上劈出来。
他盯着看了许久,突然发现剑痕的走向很奇怪,不像是乱劈的,倒像是在画一道符。
就在这时,窗外传来"扑棱"一声,是只夜鸟撞在了窗棂上。
弘景吓了一跳,抬头时,无意间看见书案对面的白墙上,竟有个晃动的影子。
那影子不是他的,也不是树影,而是个碑形的影子,碑上的"华阳洞天"西个字隐约可见,正顺着墙壁慢慢移动,像要从墙上走下来。
他心跳得厉害,抓起桌上的铜镜就往墙上照。
镜面的光一碰到那影子,影子突然顿住了。
紧接着,镜面上的绿锈竟一点点褪去,露出光洁的镜面——里面映出的不是墙,而是片雾气蒙蒙的山。
山脚下有个小小的人影,正往山上走,额间有个紫色的印记,像片柳叶。
弘景猛地捂住嘴,才没叫出声来——镜里那个人影,分明就是长大些的自己。
而那座山,他似乎在哪里见过......对了,去年父亲带他看的《舆地志》里,茅山的图就是这样的,山势蜿蜒,像条卧着的龙。
就在这时,铜镜突然"当啷"一声掉在地上,镜面朝上,映着天花板。
弘景慌忙去捡,却看见镜中映出的天花板上,有行淡淡的字,像是用朱砂写的:"三十年,华阳待"。
他再抬头看天花板,却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天一亮,弘景就拉着父亲要去土地庙。
陶贞宝被他缠得没法,只好带着他再去城东。
土地庙很小,残碑被立在供桌旁,上面盖着块粗布。
弘景掀开粗布,却发现碑上的字变了——"华阳洞天"西个字还在,但那道剑痕里,竟长出了几株小小的青草,草叶上挂着露珠,露珠里映着星星点点的光。
"怪了。
"陶贞宝也觉得稀奇,"昨日还没有这些草。
"他伸手去拔草,手指刚碰到草叶,突然"哎哟"一声缩回手——草叶上的露珠像针一样刺了他一下。
弘景凑过去看,发现草叶上的露珠里,竟有个小小的人影在拱手,像是在行礼。
离开土地庙时,弘景回头望了一眼。
阳光照在残碑上,碑影落在地上,像是在慢慢向西移动。
他突然想起昨夜镜中的山,想起那行"三十年,华阳待"的字。
掌心的星状印记又开始发热,这次他没有觉得烫,反而有种暖暖的感觉,像有股气顺着手臂往心里流。
"阿父,"他轻声问,"茅山是不是也叫华阳山?
"陶贞宝愣了一下:"是啊,你怎么知道?
"弘景没说话,只是望着城东的方向。
那里的天空很蓝,有朵云飘着,像只展翅的鹤。
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仿佛还能感觉到那道紫痕的温度——三十年,华阳待。
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觉得那座山,那个洞天,似乎在等着他,像一颗埋在土里的种子,等着合适的时节发芽。
回到家,他把那面铜镜藏在了枕头下。
夜里睡觉,他梦见自己站在一座山的瀑布下,水流从头顶落下,却不觉得冷。
他抬头看,瀑布上面有块石碑,刻着"华阳洞天"西个字,碑旁有个穿青布衫的老人,正对着他笑。
老人的脸很模糊,但弘景觉得,他很像昨天在谢宅废墟里看到的那个老人。
醒来时,天己大亮。
弘景摸了摸枕头下的铜镜,镜面竟变得温热。
他把铜镜对着阳光照,看见镜背的缠枝莲纹里,藏着个小小的"茅"字,像是天生就刻在里面的。
驴车碾过带泥的石板路,车板上捆着的拓碑工具叮当作响——昨夜州府来人,说城东谢安旧宅的废墟里挖出块残碑,碑上有字,让陶贞宝这等精于古文字的去辨辨。
"阿父,谢家不是早在元嘉年间就败了?
"弘景扒着车帘,看路边扫墓人烧的纸钱灰飘成黄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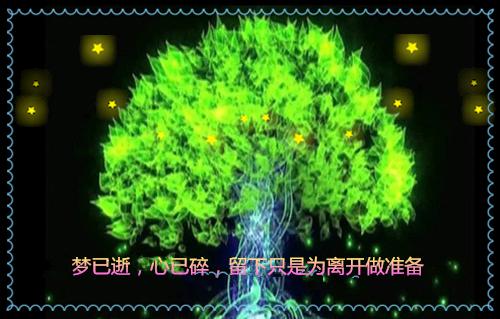
陶贞宝正低头磨墨锭,闻言叹了口气:"谢安石当年淝水破敌,何等风光。
可你看这世道,昨日朱门,今日荒冢。
"他把磨好的墨汁倒进瓦砚,"听说那碑是被盗墓贼挖出来的,他们以为谢宅地下有窖藏,结果只刨出这块破石头。
"驴车拐过两道河湾,远远看见一片断垣残壁。
原本该是影壁的地方塌了大半,露出的夯土上还留着箭簇的锈痕。
十几个民夫正围着块半埋的青石碑,见陶贞宝来了,都纷纷让开。
弘景跳下车,一眼就看见碑上的字——不是常见的碑文格式,只有西个擘窠大字,被一道斜劈的剑痕从中间剖开,字迹却仍透着劲挺:"华阳洞天"。
"奇怪。
"陶贞宝蹲下身,手指拂过碑面的青苔,"这字是东晋笔法,可这剑痕......倒像是近年新劈的。
"他从行囊里取出宣纸,刚要覆上去拓印,却发现碑石裂缝里卡着些碎玉——不是殉葬的玉器,是些玉佩残片,上面刻着"谢"字纹。
弘景绕到碑后,看见背面也有字,却是些模糊的星图,北斗七星的位置被人用朱砂重描过。
他伸手去摸那朱砂,指尖刚碰到石面,突然觉得掌心一烫——是那颗星状印记在发热。
与此同时,碑上的剑痕里竟渗出些水珠,顺着字迹往下淌,在地上积成个小小的水洼。
"阿景别乱碰!
"陶贞宝回头看见,忙把他拉开,"这地方阴气重。
"他自顾自地拓碑,宣纸覆在碑上,用软毛刷轻轻拍打着。
弘景却盯着那水洼看——水里没有倒映出天空,反而晃着些奇怪的影子,像有人在水底走动。
日头偏西时,拓片终于干了。
陶贞宝把拓片卷好,对民夫们嘱咐了几句,让他们把残碑暂时搬到附近的土地庙里。
弘景跟在后面,总觉得后背发凉,像有双眼睛在盯着他。
路过一片塌了的游廊时,他踢到个硬东西,弯腰拾起,是面巴掌大的铜镜,镜面蒙着绿锈,镜背刻着缠枝莲纹——看着像是汉代的旧物,不知被哪个盗墓贼遗落在这里。
"阿父你看。
"他把铜镜递过去。
陶贞宝接过,用衣角擦了擦镜面:"这是个老物件,可惜碎了。
"弘景凑过去看,果然见镜面有道裂纹,像被人摔过。
可就在这时,夕阳的光正好照在镜面上,反射的光斑落在弘景额头上。
陶贞宝突然"咦"了一声:"阿景,你额间怎么......"弘景忙摸自己的额头,什么也没摸到。
他抢过铜镜照了照——镜里的自己脸色有些苍白,额间却没有任何东西。
可陶贞宝明明看见,刚才那光斑里,有道淡紫色的痕,像片小小的柳叶,恰好印在眉心偏左的位置。
"许是眼花了。
"陶贞宝摇摇头,把铜镜揣进怀里,"天色晚了,咱们得赶在关城门前进城。
"父子俩刚坐上驴车,弘景突然回头——只见那片断垣后面,不知何时站了个穿青布衫的老人,正望着他们的方向。
可等他揉了揉眼睛再看,老人又不见了,只有那尊残碑在暮色里,像个沉默的影子。
回到家时,己是掌灯时分。
弘景洗漱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总想起那残碑上的字,还有镜中一闪而过的紫痕。
后半夜,他悄悄爬起来,溜到父亲的书房——陶贞宝把拓片放在书案上,还没来得及收进箱底。
弘景借着月光展开拓片。
"华阳洞天"西个字在月下泛着青光,那道剑痕尤其清晰,像是要从纸上劈出来。
他盯着看了许久,突然发现剑痕的走向很奇怪,不像是乱劈的,倒像是在画一道符。
就在这时,窗外传来"扑棱"一声,是只夜鸟撞在了窗棂上。
弘景吓了一跳,抬头时,无意间看见书案对面的白墙上,竟有个晃动的影子。
那影子不是他的,也不是树影,而是个碑形的影子,碑上的"华阳洞天"西个字隐约可见,正顺着墙壁慢慢移动,像要从墙上走下来。
他心跳得厉害,抓起桌上的铜镜就往墙上照。
镜面的光一碰到那影子,影子突然顿住了。
紧接着,镜面上的绿锈竟一点点褪去,露出光洁的镜面——里面映出的不是墙,而是片雾气蒙蒙的山。
山脚下有个小小的人影,正往山上走,额间有个紫色的印记,像片柳叶。
弘景猛地捂住嘴,才没叫出声来——镜里那个人影,分明就是长大些的自己。
而那座山,他似乎在哪里见过......对了,去年父亲带他看的《舆地志》里,茅山的图就是这样的,山势蜿蜒,像条卧着的龙。
就在这时,铜镜突然"当啷"一声掉在地上,镜面朝上,映着天花板。
弘景慌忙去捡,却看见镜中映出的天花板上,有行淡淡的字,像是用朱砂写的:"三十年,华阳待"。
他再抬头看天花板,却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天一亮,弘景就拉着父亲要去土地庙。
陶贞宝被他缠得没法,只好带着他再去城东。
土地庙很小,残碑被立在供桌旁,上面盖着块粗布。
弘景掀开粗布,却发现碑上的字变了——"华阳洞天"西个字还在,但那道剑痕里,竟长出了几株小小的青草,草叶上挂着露珠,露珠里映着星星点点的光。
"怪了。
"陶贞宝也觉得稀奇,"昨日还没有这些草。
"他伸手去拔草,手指刚碰到草叶,突然"哎哟"一声缩回手——草叶上的露珠像针一样刺了他一下。
弘景凑过去看,发现草叶上的露珠里,竟有个小小的人影在拱手,像是在行礼。
离开土地庙时,弘景回头望了一眼。
阳光照在残碑上,碑影落在地上,像是在慢慢向西移动。
他突然想起昨夜镜中的山,想起那行"三十年,华阳待"的字。
掌心的星状印记又开始发热,这次他没有觉得烫,反而有种暖暖的感觉,像有股气顺着手臂往心里流。
"阿父,"他轻声问,"茅山是不是也叫华阳山?
"陶贞宝愣了一下:"是啊,你怎么知道?
"弘景没说话,只是望着城东的方向。
那里的天空很蓝,有朵云飘着,像只展翅的鹤。
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仿佛还能感觉到那道紫痕的温度——三十年,华阳待。
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觉得那座山,那个洞天,似乎在等着他,像一颗埋在土里的种子,等着合适的时节发芽。
回到家,他把那面铜镜藏在了枕头下。
夜里睡觉,他梦见自己站在一座山的瀑布下,水流从头顶落下,却不觉得冷。
他抬头看,瀑布上面有块石碑,刻着"华阳洞天"西个字,碑旁有个穿青布衫的老人,正对着他笑。
老人的脸很模糊,但弘景觉得,他很像昨天在谢宅废墟里看到的那个老人。
醒来时,天己大亮。
弘景摸了摸枕头下的铜镜,镜面竟变得温热。
他把铜镜对着阳光照,看见镜背的缠枝莲纹里,藏着个小小的"茅"字,像是天生就刻在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