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被网暴?我靠普法送人入狱(苏晓婷林潜)在线免费小说_完结小说免费阅读开局被网暴?我靠普法送人入狱苏晓婷林潜
我穿越成战地医女那天,救了个浑身插满箭矢的男人。拆开他被血浸透的战甲时,我手抖了——左胸那道旧疤,属于三日前率铁骑踏平我药王谷、屠我满门的敌国战神。
他染血的匕首抵在我后腰,气息微弱却狠戾:“救活本王,否则这营帐里外的伤兵,一个不留。”三个月后,世上唯一能救舅父性命的,竟是他师门失传的“鬼门金针术” 。
他捻着金针,笑着看我:“嫁我,便救他。”新婚夜,我将淬毒银钗抵在他喉间:“即便与你拜了天地,我也永不会爱你。
”他却握着我的手按向左胸那道疤,眼神滚烫:“本王知道。你第一针缝上这里时,种下的就不是恨。”1意识被剧烈的爆炸声撕碎,最后的感知是实验室刺目的白光和皮肤上灼烧般的剧痛。再睁眼,呛入肺腑的是混杂着血腥、硝烟和草药苦涩的气味,耳边是连绵不绝的呻吟、嘶吼,还有远处沉闷的、一下下撞击着耳膜的轰隆声。我躺在一张硬邦邦的、散发着霉味的草席上,身上套着件粗麻布的古装,触手所及,是冰冷潮湿的泥土地面。“江影!还愣着干什么!
快搭把手!又抬下来一批!”一个沙哑焦急的女声炸响在耳边。我被人粗暴地拽起,塞进一盆浑浊的血水里。冰冷的液体激得我一颤,属于另一个人的记忆碎片如同崩堤的洪水,凶猛地灌入我撕裂般的脑海。黎江影,十七岁,南辰国药王谷最后的传人之一。三日前,药王谷因拒绝为北凛国大军提供伤药,被北凛战神厉王霍斯年率铁骑踏平,满门屠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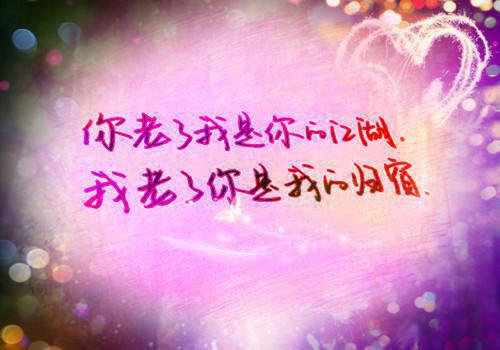
原主被师兄拼死护送出谷,昏迷后又被途经的南辰伤兵营所救,因略通医术,便被留在这地狱般的战地医帐里帮忙。而我,二十一世纪顶尖外科医生黎江影,就在这一刻,成了她。“医女!这个!这个快不行了!”嘶吼声将我的神智猛地拽回现实。
两个浑身是血、甲胄破损的兵士踉跄着抬着一个血人,重重扔在我面前那张唯一还算完整的木板上。那几乎不能算是一个人,更像是一团被暴力撕碎的血肉。玄色铁甲早已被鲜血和污垢染得看不出原貌,上面深深嵌着四五支断箭,箭杆狰狞地支棱着。最致命的一处紧挨着左胸心脉,随着他微弱到几乎察觉不到的呼吸,一股股暗红的血还在缓慢地往外渗,带着不祥的黑色。
浓烈的铁锈味和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
没有时间给我消化穿越的震惊或者沉浸在原主的悲恸里。医生的本能瞬间压倒了一切。
我扑到木板前,剪开那与皮肉紧紧黏连、被血浸透的战袍。手下触到的胸膛宽阔而坚硬,疤痕交错,新旧叠覆,每一道都诉说着这具身体主人从何等惨烈的厮杀中幸存。
我的动作快而稳,脑海中原主关于草药、针灸的记忆与我现代外科的清创、缝合技术飞速融合,形成一种超越这个时代的急救本能。柳叶刀在我手中精准地起出箭镞,剜去腐肉,结扎血管。
汗水顺着我的额角滑落,混进他身上的血污里。清理到左胸一处极深的旧伤时,我的指尖猛地一顿。
那道疤痕…形状、位置…记忆的某个闸门轰然被冲开——冲天而起的烈焰,师尊将我死死按在焦黑的药柜之下,他的血滴在我脸上,温热而粘稠。
“江影…别出声…活下…” 谷外,黑压压的北凛铁骑如同嗜血的蚁群,为首的男人端坐于高头战马之上,玄甲覆面,煞气冲天。他手中的长戟尚在滴血,左胸心口处的铠甲,有一道明显的、崭新的破损痕迹,破口之下,隐约可见皮肉翻卷。
那破口的位置,与眼前这道早已愈合却依旧狰狞的旧疤,分毫不差!是他!
率铁骑踏平药王谷,屠我师门,手上沾满我至亲鲜血的刽子手!北凛战神,厉王霍斯年!
我竟然…我竟然在救他?!巨大的荒谬感和刻骨的仇恨如同冰锥,狠狠刺穿我的心脏,冻僵了我的四肢百骸。呼吸骤然停止,指尖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捏着的止血纱布飘然掉落在污浊的地面上。杀了他!现在!就在此刻!只要手稍微一偏,将那刀尖送入他的心口!或者,干脆扯掉那些暂时维系着他脆弱生命的管线!为师门报仇!
为师尊报仇!恨意如同毒焰,疯狂灼烧着我的理智。
就在我的手指即将遵循那毁灭的冲动时——一只冰冷如同铁钳的手猛地攥住了我的手腕!
力道之大,几乎要瞬间捏碎我的骨头!我骇然低头,正正撞入一双不知何时睁开的眼睛里。
深邃,漆黑,如同万年不化的寒冰,又像是淬了最毒锋芒的匕首。
没有丝毫伤重者的涣散和迷茫,只有绝对清醒的、野兽般的警醒和冷冽到极致的杀伐之气。
那瞳孔深处清晰地倒映出我瞬间惨白、写满惊骇与未散恨意的脸。
“你…”我的喉咙像是被铁锈堵住,挤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霍斯年的脸色灰败,唇色苍白干裂,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濒死的嘶哑,但他开口,每一个字却都像裹着冰碴,狠狠地、清晰地砸进我的耳膜,不容错辨:“别声张。”下一刻,一个冰冷、坚硬、带着粘腻血液触感的东西,悄无声息地抵在了我的后腰。那形状,分明是匕首的尖端!尖锐的刺痛感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料传来,杀意刺骨。“救活本王,”他盯着我,瞳孔缩紧,如同锁定猎物的深渊巨兽,气息微弱,却字字狠戾,“否则,这营帐里外的伤兵,一个…不留。”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冻结。
他不是在开玩笑。我毫不怀疑,若我此刻有丝毫异动,或者他最终死了,这整个伤兵营,顷刻间就会变成真正的人间炼场。仇恨在我的胸腔里疯狂冲撞,几乎要撕裂我。可目光所及,是周围那些同样伤痕累累、奄奄一息的南辰士兵,他们信任地看着我,喊着“黎医女”…我的手死死攥成拳,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刺痛让我勉强维持住最后一丝摇摇欲坠的镇定。我垂下眼,避开他那慑人的目光,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别动,伤口会裂。”然后,我重新拿起针线,继续那场漫长而煎熬的手术。每一针,每一线,都像缝在我自己的心上。
他的血灼烫我的手指,他的呼吸喷薄在我的颈侧,那柄抵在我腰后的匕首,如同死神的凝视,从未离开。……2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在惊惧与仇恨的双重煎熬中度过。霍斯年被秘密转移,我再也未曾见过他,但那句“屠尽”的威胁和那双冰冷嗜血的眼睛,却成了我每一个夜晚的梦魇。我尽力救治着伤兵,试图用忙碌麻痹自己,将那个可怕的秘密死死压在心底。直到一匹快马疯狂地冲入营地,带来了几乎让我崩溃的消息——留守后方小镇的舅父,听闻药王谷噩耗后急火攻心,引发了严重的心疾,已是药石罔效,危在旦夕!我几乎是连滚爬爬地告了假,疯了一样赶回那个临时安置的家。看到榻上舅父面如金纸、气若游丝的模样,我整个人都凉了。镇上最好的老郎中来了一波又一波,都是摇头叹息。“心脉衰竭,油尽灯枯之兆啊…除非…”“除非什么?!”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死死抓住老郎中的衣袖。
老郎中苦笑:“除非…能用传说中的‘鬼门金针术’强行激发心脉生机,或可争得一线希望。
但这金针术乃北凛国不传之秘,据说早已失传…当世恐怕…恐怕唯有…”他后面的话没说,但我已经知道了。北凛战神,厉王霍斯年。师从北凛神秘国手,尽得其真传,尤其是一手起死回生的金针绝技,虽鲜少示人,却并非无迹可寻。
命运像是一个最残忍的玩笑师,又一次将他推到了我的面前。这一次,不是他需要我救他的命。而是我,要求他,救我在世上仅存的、最后一位亲人。
巨大的绝望和屈辱感如同潮水,瞬间将我淹没。我跪在舅父榻前,看着他微弱起伏的胸膛,指甲抠进地面,直至出血。别无选择。我甚至没有时间犹豫。……厉王临时驻跸的行馆,守卫森严,透着与他本人如出一辙的冷硬肃杀之气。我被带进书房时,他正临窗而立。
三个月不见,他身上的重伤似乎已然痊愈,墨色锦袍衬得他身姿挺拔如松,只是脸色依旧带着几分失血后的苍白,却更添了几分阴鸷冷厉的气质。
窗外天光落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投下深刻的阴影。他手中把玩着几枚细如牛毛的金针,金光在他指尖流转,跳跃着冰冷而精准的光泽。听到动静,他缓缓转过身。目光落在我身上,像是冰冷的蛇信扫过,带着审视,还有一丝…早已料到的玩味。“求本王救他?”他开口,语调平淡无波,听不出丝毫情绪。我挺直脊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用尽全身力气才压下转身就逃的冲动和汹涌的恨意。“是。”我的声音干涩得厉害,“请王爷施以援手,救我舅父。任何代价…民女愿付。”“任何代价?”他微微挑眉,重复着这四个字,指尖的金针转得更慢,那细微的光芒几乎要刺痛我的眼睛。他放下金针,缓步走近我,高大的身影带来极强的压迫感,目光如实质般烙在我脸上,带着一种几乎残忍的审视。“可以。”他顿了顿,清晰地,一字一句地,将条件砸向我:“嫁我。便救他。”空气瞬间凝固。我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冻结,连心跳都停了半拍。“你——”屈辱和暴怒瞬间冲垮了理智,让我眼前发黑,几乎站不稳。他却像是很满意我的反应,唇角勾起一丝极淡的、冰冷的弧度,不再看我,重新拈起那枚金针,仿佛刚才说出的不是一个足以将我彻底摧毁的条件,而只是一句寻常的交易。“三日后,本王要看到花轿。”没有半分转圜的余地。
所有的挣扎、所有的恨意、所有的骄傲,在舅父孱弱断续的呼吸声面前,被碾得粉碎。
我闭上眼睛,身体抑制不住地细微颤抖,齿尖深深陷进下唇,尝到了那浓郁的血腥味。
一个字,仿佛耗尽了轮回转世所有的气力,从我颤抖的齿缝间挤出来。“……好。
”……厉王纳妃,即便是在战时,排场也足以震动整个边城。唢呐喧天,红绸铺地,十里红妆。可我坐在剧烈摇晃的花轿里,只觉得像是一口正在被抬往坟冢的棺材。
凤冠霞帔沉重地压在我的头上、身上,如同无形的枷锁。新房布置得奢华却冰冷,触目所及皆是刺目的红。红烛高烧,淌下的烛泪像是血滴凝固。我一把扯下碍事的盖头,坐在铺着龙凤喜被的榻边,像一尊被抽空了灵魂的木偶,等待着最后的审判。袖中,那支我精心淬炼了数月、喂了见血封喉剧毒的银钗,冰凉地贴着小臂,那点冰冷的触感,是我唯一能感受到的“活着”的迹象。外面的喧嚣终于渐渐散去。沉稳而清晰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门外。吱呀一声,门被推开。带着一身清冷酒气的男人走了进来。
大红色的喜服穿在他身上,不见半分暖意,反而更衬得他眉眼深邃冷峻,周身都散发着迫人的寒气。他挥退了身后试图跟进来的侍从,反手关上了门。厚重的门板,隔绝了外面的一切。他一步步走到我面前,高大的身影投下的阴影,彻底将我笼罩其中,遮住了所有跳动的烛光。我闻到了他身上浓郁的酒气,还有那股子仿佛浸入骨血的、冰冷的铁锈味。他伸出手,似乎想挑起我的下巴。
就在他指尖即将触碰到我的瞬间——我动了!
积蓄了整整一日的、数月的、乃至两世为人的所有恨意、屈辱和绝望,在这一刻轰然爆发!
速度快到极致,袖中毒钗滑入掌心,幽蓝的寒光划破满室暖红的烛光,带着同归于尽的决绝,直直刺向他的咽喉!“霍斯年!”声音嘶哑得不像我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血海里捞出,淬着最深的毒汁和恨意!“我嫁你,只为救我舅父!你听清楚!即便与你拜了天地,喝了合卺酒,我也永不会爱你!永不!”银钗尖端那点幽蓝的寒芒,距离他凸起的喉结,只剩毫厘之距!我的手因极致的激动和仇恨而剧烈颤抖,繁复的嫁衣袖口滑落,露出一段细白却绷紧了决绝力量的手腕。烛火噼啪一声爆开一朵灯花。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霍斯年垂眸,视线落在那几乎要触碰到他皮肤的毒钗上,又缓缓抬起,目光沉静地落在我因激动而涨红、写满刻骨恨意的脸上。他的眼底,没有预料中的惊怒,没有被打扰的戾气,甚至没有丝毫意外。
反而…掠过一丝极深极暗的、扭曲的…笑意?然后,他低低地笑出了声。
笑声从喉咙深处溢出,带着酒后的沙哑和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了然与玩味。
浑不在意那淬毒的钗尖随时可能夺去他的性命。在我骤然收缩的瞳孔注视下,他抬起手,慢条斯理地,一颗一颗地,解开了身上那件大红色喜服的襟口。布料向两侧滑落,露出其下坚实壁垒般的胸膛和线条分明的腹肌。他握住我颤抖的、紧攥着毒钗的手腕。
他的手掌滚烫,力道大得惊人,不容我有丝毫抗拒,却又古怪地控制着,并未弄痛我。然后,他引着我的手,引着那淬着见血封喉剧毒的钗尖,缓缓地、不容后退地,抵上了他左胸心口的位置。那里,肌肤之下,心脏在沉稳地跳动。而肌肤之上,正是我当初在伤兵营那盏昏暗油灯下,一针一线,亲手为他缝合留下的那道伤口。疤痕粉嫩,尚未完全褪去,在我超越时代的缝合技艺下,愈合得平整而规整,在跳跃的烛光下,清晰无比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与记忆中药王谷外,他铠甲上那道破口,以及更久之前那道旧疤,完美地重合在一起。他的目光如同最深的寒潭,死死锁着我,眼底翻涌着我看不懂的、剧烈而滚烫的暗流。“本王知道。”他开口,声音低沉得如同耳语,却带着一种洞穿一切、近乎残忍的温柔和笃定,狠狠撞入我的耳膜,撞碎我所有伪装的盔甲。
“你第一针缝上这里时,”“种下的就不是恨。”心跳在耳膜里擂鼓,震得我指尖发麻。
那支淬毒的银钗还抵在他心口的疤痕上,幽蓝的锋芒几乎要刺破他温热的皮肤。他说什么?
种下的不是恨?荒谬!滔天的恨意几乎要冲破我的天灵盖!我手腕猛地用力,想要将那毒钗狠狠送进去——可他握着我手腕的力道如铁箍,纹丝不动。不是强行压制,而是一种…一种绝对的、游刃有余的控制。
他的拇指甚至轻轻摩挲了一下我腕间剧烈跳动的脉搏,激起我一阵战栗。“放开!
”我从齿缝里挤出声音,眼眶灼烫,却流不出一滴泪。所有的水分似乎都被仇恨蒸干了。
霍斯年非但没放,反而就着这个姿势,又向前逼近了半步。毒钗的尖端正正抵住那道疤,微微陷进皮肉。我甚至能感觉到他心脏沉稳有力的搏动,透过钗身传递到我的指尖,一下,又一下,烫得骇人。“黎江影,”他唤我的名字,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奇异的、近乎叹惋的腔调,“药王谷的血案,非我所愿,却因我而起。这笔债,我认。”我瞳孔骤缩,难以置信地瞪着他。认?他轻飘飘一个“认”字,就能抵过我谷中上下百余条性命?抵过我师尊的血?“但你救我那一刻,”他继续道,目光如深潭,牢牢锁着我,不容我移开视线,“眼神里的东西,骗不了人。
你不是他们口中只知道救人的菩萨,你的针线里,有恨,有怕,但也有…别的。”别的?
什么别的?难道是我身为医者,面对生命垂危时那该死的、无法彻底泯灭的本能?
那瞬间的犹豫,竟被他解读成了“别的”?“你胡说八道!”我声音发颤,试图抽回手,却徒劳无功,“我恨不能将你千刀万剐!”“是吗?”他唇角那点冰冷的弧度又扬起了些许,带着洞悉一切的残忍,“那为何现在不动手?钗上有毒,见血封喉。
你手腕力道只需再进三分,便能为你药王谷报仇雪恨。”他盯着我,目光锐利如刀,剖开我层层叠叠的伪装:“你在犹豫什么?黎江影。”我在犹豫什么?
舅父苍白的面容倏地闪过脑海。是啊,我在犹豫什么?杀了他,舅父怎么办?
世上还有谁能施展鬼门金针术?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仇恨和现实如同两把钝锯,来回拉扯着我的神经。“因为……”我嘴唇哆嗦着,几乎发不出声音,“…我舅父…”“哦?
”他挑眉,仿佛才想起这件事,语气里却听不出丝毫意外,“对了,还有这个交易。
”他猛地松开了我的手。力道骤然撤去,我手臂一软,银钗“哐当”一声掉落在铺着大红鸳鸯的被褥上,那点幽蓝的光芒在喜庆的红色中显得格外刺眼。失去支撑,我踉跄着后退一步,跌坐在冰冷的脚踏上,大口喘着气,像是离水的鱼。霍斯年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慢条斯理地将敞开的喜服重新拢好,遮住那道疤痕和心口处被钗尖压出的细微红点。“放心,”他语气恢复了那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平淡,“本王既答应了你,便不会食言。
明日便去为你舅父施针。”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地上狼狈的我,和那支落在喜被上的毒钗。
“至于你……”他声音里听不出情绪,“今晚就睡这里。记住你的身份,厉王妃。”说完,他竟不再看我,转身走向房间另一侧的软榻,和衣躺了下去,背对着我。红烛依旧高烧,流着泪。我坐在冰冷的地上,看着那支近在咫尺的毒钗,又看向软榻上那个毫无防备背对着我的男人,全身的血液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杀意未消,却已失了最佳的时机。而他最后那句话,像一道新的枷锁,重重扣了下来。厉王妃。
多么讽刺的身份。那一夜,我睁着眼直到天明。软榻上的人呼吸平稳,似乎早已入睡。
可我总觉得,那双深邃的眼睛,在黑暗中一直醒着。……3第二天,霍斯年果然如约出现在了舅父暂居的小院。他换了一身墨色常服,摒退了所有闲杂人等,只让我在一旁打着下手。看到舅父面如金纸的模样,他眉头几不可查地蹙了一下。
取出金针时,他整个人气质都为之一变,之前的冷厉和慵懒尽数收敛,只剩下一种全神贯注的、近乎神圣的虔诚。金针在他指尖仿佛有了生命,细如毫芒,闪烁着柔和的金光。下针时,快、准、稳,认穴之精准,力道之精妙,让我这个自诩得了药王谷真传又融合了现代医学的人,都看得心惊肉跳,暗自叹服。
这绝不是单凭杀戮能练就的技艺。
这是需要无数次的钻研、实践和极致的天赋才能达到的境界。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怎么会拥有这样一双救人的手?我的心绪更加混乱。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时辰。
当最后一枚金针取出时,霍斯年的额角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脸色比之前更苍白了几分。
而榻上的舅父,虽然依旧昏迷,但脸上那层死灰般的颜色却褪去了不少,呼吸也变得明显有力悠长起来。我扑到床边,颤抖着手指搭上舅父的腕脉。虽然依旧虚弱,但那原本如同游丝、随时会断绝的脉象,竟然真的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狂喜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冲上心头,我猛地转头看向霍斯年。
他正慢条斯理地擦拭着金针,动作有些微不可察的迟缓。“三日一次,连续施针三次,辅以我开的方子静养,性命可保无虞。”他语气平淡地交代,仿佛只是完成了一项寻常的任务。“多谢…”两个字脱口而出,随即又被我猛地咬住嘴唇。
我在谢什么?谢他履行这场卑鄙交易吗?霍斯年似乎看穿了我的矛盾,唇角扯起一个微妙的弧度,没说什么,将金针收回盒中,起身朝外走去。“王爷!
”我下意识叫住他。他脚步一顿,没有回头。“…你的伤,刚才运针,是否牵扯到了?
”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他刚才苍白的脸色和细微的迟缓,没有逃过我的眼睛。那处旧伤,毕竟离心脉太近。霍斯年沉默了片刻,背影似乎僵硬了一瞬。然后,他低低地笑了一声,笑声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死不了。”说完,他便大步离开,再也没有回头。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口,心里乱得像一团麻。接下来的日子,我留在小院照顾舅父。霍斯年果真每隔三日便来一次,每次施针后脸色都会差一些,但依旧冷着一张脸,话很少,施针完毕便离开,从不逗留。舅父在第二次施针后醒转了过来,虽然身体依旧极度虚弱,但眼神已经恢复了清明。他看着霍斯年离开的背影,枯瘦的手抓住我,气息微弱地问:“影儿…那位是…?”我喉咙发紧,半晌,才低声道:“是…治好您的神医。”“神医…”舅父浑浊的眼里闪过一丝迷茫,终究太过虚弱,又昏睡过去。我替他掖好被角,心口堵得发慌。第三次施针结束,霍斯年离开时,脚步明显虚浮了一下,扶了下门框才站稳。“王爷!”我再次脱口而出。
他侧过头,阳光从他身后照来,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看不清表情。“明日,搬回行馆。”他丢下这句话,声音有些沙哑,“你是厉王妃,总住在外头,不成体统。
”命令的口吻,不容置疑。我捏紧了拳头,却没有像之前那样立刻涌起反抗的念头。
这些日子,他看着舅父一点点好转,看着他不惜耗费心神甚至可能牵动旧伤也要完成承诺…那些冰冷的恨意下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悄然松动。但药王谷的冲天火光,依旧夜夜入梦。……回到行馆,身份已然不同。下人们恭敬地称我“王妃”,我却觉得无比刺耳。霍斯年给了我应有的体面,却并未限制我的自由,我依旧可以每日去小院照顾舅父。只是行馆里的气氛,日渐紧张。
北凛国内似乎传来了什么不好的消息,霍斯年书房里的灯常常亮到深夜,来往的将领神色凝重。我隐约听到些风声,似乎与他力主和谈、反对继续南下征伐有关,触怒了北凛朝中的主战派。一天深夜,我被一阵极其轻微却密集的脚步声惊醒。
不是寻常护卫巡逻的节奏!一种不好的预感攫住我。我悄声下床,摸到门边,透过缝隙向外看。只见月色下,无数黑影正悄无声息地潜入行馆,手中的兵刃反射着幽冷的光!目标明确地直扑霍斯年所在的主院!是刺杀!
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几乎没有任何思考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