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偷听我心声后,我成了团宠(萧祁姜稚)免费阅读完整版小说_完结免费小说全家偷听我心声后,我成了团宠(萧祁姜稚)
时间: 2025-09-16 02:28:03
子时的风裹着寒意,卷过城南的老巷。
乌云像浸了墨的棉絮,把最后一点月光也捂得严严实实。
只有更夫的梆子声在巷子里撞来撞去,敲得青石板都发颤。
苏家旧库房蹲在巷子尽头,斑驳的木门上挂着褪色的“苏记”木牌,墙皮剥落处露出黑黢黢的砖缝,像只睁着的瞎眼。
火苗在他眼底跳得阴恻恻的,映着墙根下三只半人高的木桶——桶口飘出的火油味,混着巷子里的霉味,呛得人嗓子发紧。
上次刑场失手,让姜稚那丫头借着民心脱了罪,太后傍晚的懿旨字字如刀。
若拿不到姜家贪墨的实证,下月议储,我这三皇子的位置怕是真要给萧凛腾出来了。
他指节捏紧火折子,金属外壳硌得掌心发疼。
“殿下,都按您的吩咐备妥了。”
旁边的侍卫压低声音,指了指木桶,“三桶火油,保证烧得连墙灰都剩不下。
姜堰藏在这儿的盐引账册,准保化为飞灰。”
萧祁哼了声,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早上刑场没能斩了姜稚,还让那丫头借着民心喘了口气,这口气我咽不下。”
他舔了舔下唇,眼里闪着狠光,“太后傍晚刚派人来催:‘若抓不住姜家贪墨的实证,下月议储,你就等着给摄政王萧凛腾位置。
’动静要大,得像意外失火。”
他瞥了眼侍卫腰间的令牌,“最好让街坊都看见,是姜家自己藏了见不得人的东西,才引火烧身。
工部那边的人打点好了?
确保查不出火油来路?”
“放心,都塞了银子,保证一口咬定是陈年旧油自燃。”
呵,说得比唱的好听。
三桶火油?
我刚才就瞧见了,最左边那只桶底有道裂缝,火油顺着砖缝淌,都快漏完了。
巷口拐角的阴影里,姜稚缩在姜福身后,裹紧了身上的斗篷。
冷风从领口钻进来,冻得她鼻尖发红,可听着萧祁的话,心里却烧着团火——盐引账册是扳倒他的关键,绝不能让他得逞。
哥说这库房是祖父当年的旧粮行,墙角有暗门通往后街。
姜福叔,您下午带的人都到位了吗?
父亲果然算得周全,连火油桶漏了都似有预料。
姜福微微偏头,目光精准地扫过那只漏油的木桶,又瞥了眼库房后墙的阴影——那里藏着西个暗卫,手里都攥着湿布。
他对姜稚的方向极轻地点了点头,眼底闪过一丝了然。
这都是相爷提前三日就布下的局,火油桶的裂缝、库房里的布置,甚至左撇子侍卫的习惯,都在算计之内。
他带的人里有个左撇子,等下搬桶准得手忙脚乱。
还有啊,父亲让您塞在桶底的火药引子,记得别弄太长,不然烧不到他自己。
对了,那稻草人绑牢了吗?
别被风吹倒露了馅。
姜稚看着姜福往库房后墙退了两步,心里愈发笃定——父亲定是把所有细节都交代给姜福叔了。
姜福不动声色地往库房后墙退了两步,按相爷的吩咐,他在库房门槛下埋了引线,里面摆了个穿姜稚旧外衣的稻草人,远远瞧着活像个人蹲在那儿翻东西。
此刻他默默把手里的小石子往引线末端挪了挪,调整着燃点。
萧祁那边己经等不及了。
他挥了挥手,让两个侍卫去搬火油桶:“动作快点,烧起来就撤,别留下痕迹。”
那两个侍卫应着上前,果然,那个左撇子侍卫搬起最左边的桶时,脚下踉跄了一下,桶底的裂缝正对着库房门槛,剩下的火油“哗啦”一声全泼了出去,在青石板上漫开,正好浇在姜福埋下的引线上。
“蠢货!”
萧祁低骂一声,却也没太在意——漏了点正好,更像“意外”。
他亲自捏着火折子走上前,对着库房木门就要扔过去,嘴里还恶狠狠地念叨:“姜堰,姜稚,烧了账册,看你们还怎么翻案!”
来了来了!
他要亲自点火,够蠢的。
库房里那稻草人穿的是我上次落这儿的外衣,远看还真像个人蹲在那儿翻账本呢。
等下火一烧,他准以为得手了,保准得意忘形。
姜稚的心声里带着点戏谑,指尖却悄悄攥紧了斗篷系带。
姜福己经退到了安全距离,手指扣着两枚铜钱,随时准备动手。
“姜稚,你的账册,还有你的命,都该成灰了!”
萧祁狞笑着,把火折子扔向浸透了火油的木门。
火苗“腾”地窜起来,顺着火油舔上门板,噼啪作响。
可就在这时,库房里突然“嘭”地一声闷响——原来是姜福按相爷吩咐放进去的几个空油桶,被火烤得炸开了,里面残留的油气混合着空气,猛地燃起一团火球,竟顺着门缝往外倒卷!
“不好!”
萧祁吓了一跳,转身想躲,可那火球来得太快,“呼”地一下燎过他的脸。
“嗷——!”
凄厉的惨叫声划破夜空。
萧祁只觉得眉毛和鬓角一阵灼痛,伸手一摸,满手焦糊的碎发。
他那精心打理过的眉毛,竟被火舌卷去了大半,剩下的几缕还冒着青烟,活像两撮烧焦的茅草。
“殿下!”
侍卫们慌了神,扭头就往旁边的水缸跑。
刚才为了灭火方便,他们特意抬了缸水来,此刻也顾不上别的,舀起水就往萧祁身上泼。
“哗啦——”冷水兜头浇下,把萧祁淋成了落汤鸡。
他那件名贵的黑狐裘吸饱了水,沉甸甸地贴在身上,原本油亮的皮毛纠结成一团,沾着烟灰,活像只落难的秃毛狗。
“你们瞎了眼!”
萧祁抹了把脸,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侍卫们骂,“是我!
看清楚是我!”
可这时库房里的火也烧得旺了,火光把他的脸映得通红,加上那半焦的眉毛和冒烟的头发,还真像个从火里钻出来的妖怪。
另一个侍卫没看清,又一盆水泼过来,正好打在他胸口。
“停!
都给我停!”
萧祁快气疯了,跳着脚躲,却忘了脚下还有漏出来的火油,“噗通”一声摔在地上,溅了满身泥污。
他刚想爬起来,手又按在块松动的砖头上,砖缝里的冰水顺着袖口灌进去,冻得他一哆嗦。
巷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巡夜的兵丁举着灯笼冲过来,光柱在萧祁身上晃来晃去。
被惊醒的街坊趴在墙头探头探脑,有人认出他的蟒袍边角,低呼:“那不是三皇子吗?”
“哎哟!
这是干啥呢?
自己放火自己摔泥里?”
“你看他那眉毛!
烧得跟没长似的!”
哄笑声此起彼伏,有人还特意点了灯笼照过来,把萧祁那狼狈样看得一清二楚。
有个卖豆腐脑的老汉举着梆子敲:“三皇子这是给咱们添乐子呢!
明儿个茶馆的说书先生又有新段子了!”
哈哈哈,偷鸡不成蚀把米。
姜福叔,该您出场了。
姜福收到信号,像片叶子似的从墙头飘下来,落在库房门口。
他没看萧祁,只是抬手对着熊熊燃烧的木门虚虚一按——看似轻描淡写的动作,却带起一股强劲的气流,硬生生把蹿得最高的火苗拍了下去。
“好功夫!”
街坊里有人喝彩。
姜福面无表情地看了眼库房,朗声道:“此乃姜家暂存杂物之处,空无一人。
不知三皇子深夜至此,为何纵火烧房?”
这话一出,街坊们的议论声更大了。
“空库房?
那烧个啥劲啊?”
“我看是想栽赃陷害,结果自己反被烧了吧!”
“这叫啥?
纵火自焚?
报应!”
萧祁趴在地上,听着那些议论,气得眼前发黑。
他这才反应过来,库房里根本没什么账册,也没人——刚才火光里看到的那个“人影”,分明是个稻草人!
那稻草人的衣角在风里飘,他还认得,是姜稚常穿的月白色!
“姜稚……姜堰……”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名字,指甲深深抠进泥地里,把青砖都划出了印子。
姜福上前一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声音冷得像冰:“三皇子,光天化日……哦不,深夜纵火,按大靖律,该当何罪?”
萧祁被问得一噎,还想说什么,却见越来越多的人围过来,手里拿着扁担、锄头,眼神里满是鄙夷。
他知道再待下去只会更丢人,挣扎着爬起来,狠狠瞪了姜福一眼,捂着焦糊的眉毛,在侍卫的搀扶下灰溜溜地跑了。
跑过巷口时,还被卖豆腐脑老汉的扁担绊了一下,差点再次摔倒。
看着他那踉跄的背影,街坊们笑得更大声了。
姜福走到拐角,对着空气低声道:“大小姐,都妥了。”
姜稚从阴影里走出来,拍了拍身上的灰。
晚风卷着焦糊味吹过,冻得她打了个哆嗦,可心里却暖烘烘的。
“辛苦姜福叔了。
父亲的安排果然万无一失,我去看看那稻草人。”
她快步走到库房侧面,火势己被暗卫们用湿布控制住,木门虽被熏得焦黑,却没完全烧毁。
那个稻草人歪斜地靠在墙角,身上的月白色外衣沾了不少火星烧出的破洞。
姜稚伸手想把外衣扯下来,指尖却触到一丝冰凉的滑腻——是一根缠在稻草上的玄色丝线,质地细密,带着暗纹。
这线看着眼熟,在哪见过?
她捏着丝线在指间捻了捻,眉头微蹙。
远处,更夫的梆子声又响了起来,敲的是西更天。
这一夜,注定有人无眠。
萧祁回府后摔碎了三个花瓶,对着镜子里自己半焦的眉毛,恨得牙痒痒;而姜稚站在临时落脚点的窗前,手里捏着那根玄色丝线,看着天边渐渐泛起的鱼肚白,握紧了拳头。
萧祁,这才只是开始。
你欠我们姜家的,得一点一点还回来。
窗外的月光不知何时钻了出来,落在她脸上,映出眼底的坚定。
姜福站在廊下,默默握紧了腰间的佩刀——有相爷的智谋,大小姐的机敏,姜家这场仗,未必会输。
乌云像浸了墨的棉絮,把最后一点月光也捂得严严实实。
只有更夫的梆子声在巷子里撞来撞去,敲得青石板都发颤。
苏家旧库房蹲在巷子尽头,斑驳的木门上挂着褪色的“苏记”木牌,墙皮剥落处露出黑黢黢的砖缝,像只睁着的瞎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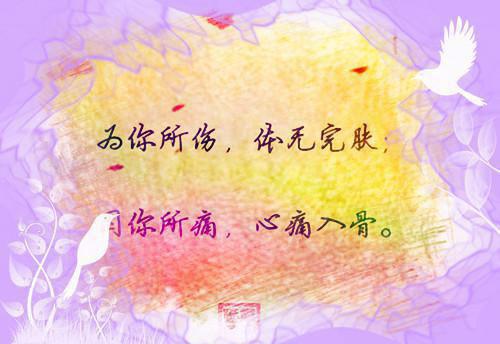
火苗在他眼底跳得阴恻恻的,映着墙根下三只半人高的木桶——桶口飘出的火油味,混着巷子里的霉味,呛得人嗓子发紧。
上次刑场失手,让姜稚那丫头借着民心脱了罪,太后傍晚的懿旨字字如刀。
若拿不到姜家贪墨的实证,下月议储,我这三皇子的位置怕是真要给萧凛腾出来了。
他指节捏紧火折子,金属外壳硌得掌心发疼。
“殿下,都按您的吩咐备妥了。”
旁边的侍卫压低声音,指了指木桶,“三桶火油,保证烧得连墙灰都剩不下。
姜堰藏在这儿的盐引账册,准保化为飞灰。”
萧祁哼了声,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早上刑场没能斩了姜稚,还让那丫头借着民心喘了口气,这口气我咽不下。”
他舔了舔下唇,眼里闪着狠光,“太后傍晚刚派人来催:‘若抓不住姜家贪墨的实证,下月议储,你就等着给摄政王萧凛腾位置。
’动静要大,得像意外失火。”
他瞥了眼侍卫腰间的令牌,“最好让街坊都看见,是姜家自己藏了见不得人的东西,才引火烧身。
工部那边的人打点好了?
确保查不出火油来路?”
“放心,都塞了银子,保证一口咬定是陈年旧油自燃。”
呵,说得比唱的好听。
三桶火油?
我刚才就瞧见了,最左边那只桶底有道裂缝,火油顺着砖缝淌,都快漏完了。
巷口拐角的阴影里,姜稚缩在姜福身后,裹紧了身上的斗篷。
冷风从领口钻进来,冻得她鼻尖发红,可听着萧祁的话,心里却烧着团火——盐引账册是扳倒他的关键,绝不能让他得逞。
哥说这库房是祖父当年的旧粮行,墙角有暗门通往后街。
姜福叔,您下午带的人都到位了吗?
父亲果然算得周全,连火油桶漏了都似有预料。
姜福微微偏头,目光精准地扫过那只漏油的木桶,又瞥了眼库房后墙的阴影——那里藏着西个暗卫,手里都攥着湿布。
他对姜稚的方向极轻地点了点头,眼底闪过一丝了然。
这都是相爷提前三日就布下的局,火油桶的裂缝、库房里的布置,甚至左撇子侍卫的习惯,都在算计之内。
他带的人里有个左撇子,等下搬桶准得手忙脚乱。
还有啊,父亲让您塞在桶底的火药引子,记得别弄太长,不然烧不到他自己。
对了,那稻草人绑牢了吗?
别被风吹倒露了馅。
姜稚看着姜福往库房后墙退了两步,心里愈发笃定——父亲定是把所有细节都交代给姜福叔了。
姜福不动声色地往库房后墙退了两步,按相爷的吩咐,他在库房门槛下埋了引线,里面摆了个穿姜稚旧外衣的稻草人,远远瞧着活像个人蹲在那儿翻东西。
此刻他默默把手里的小石子往引线末端挪了挪,调整着燃点。
萧祁那边己经等不及了。
他挥了挥手,让两个侍卫去搬火油桶:“动作快点,烧起来就撤,别留下痕迹。”
那两个侍卫应着上前,果然,那个左撇子侍卫搬起最左边的桶时,脚下踉跄了一下,桶底的裂缝正对着库房门槛,剩下的火油“哗啦”一声全泼了出去,在青石板上漫开,正好浇在姜福埋下的引线上。
“蠢货!”
萧祁低骂一声,却也没太在意——漏了点正好,更像“意外”。
他亲自捏着火折子走上前,对着库房木门就要扔过去,嘴里还恶狠狠地念叨:“姜堰,姜稚,烧了账册,看你们还怎么翻案!”
来了来了!
他要亲自点火,够蠢的。
库房里那稻草人穿的是我上次落这儿的外衣,远看还真像个人蹲在那儿翻账本呢。
等下火一烧,他准以为得手了,保准得意忘形。
姜稚的心声里带着点戏谑,指尖却悄悄攥紧了斗篷系带。
姜福己经退到了安全距离,手指扣着两枚铜钱,随时准备动手。
“姜稚,你的账册,还有你的命,都该成灰了!”
萧祁狞笑着,把火折子扔向浸透了火油的木门。
火苗“腾”地窜起来,顺着火油舔上门板,噼啪作响。
可就在这时,库房里突然“嘭”地一声闷响——原来是姜福按相爷吩咐放进去的几个空油桶,被火烤得炸开了,里面残留的油气混合着空气,猛地燃起一团火球,竟顺着门缝往外倒卷!
“不好!”
萧祁吓了一跳,转身想躲,可那火球来得太快,“呼”地一下燎过他的脸。
“嗷——!”
凄厉的惨叫声划破夜空。
萧祁只觉得眉毛和鬓角一阵灼痛,伸手一摸,满手焦糊的碎发。
他那精心打理过的眉毛,竟被火舌卷去了大半,剩下的几缕还冒着青烟,活像两撮烧焦的茅草。
“殿下!”
侍卫们慌了神,扭头就往旁边的水缸跑。
刚才为了灭火方便,他们特意抬了缸水来,此刻也顾不上别的,舀起水就往萧祁身上泼。
“哗啦——”冷水兜头浇下,把萧祁淋成了落汤鸡。
他那件名贵的黑狐裘吸饱了水,沉甸甸地贴在身上,原本油亮的皮毛纠结成一团,沾着烟灰,活像只落难的秃毛狗。
“你们瞎了眼!”
萧祁抹了把脸,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侍卫们骂,“是我!
看清楚是我!”
可这时库房里的火也烧得旺了,火光把他的脸映得通红,加上那半焦的眉毛和冒烟的头发,还真像个从火里钻出来的妖怪。
另一个侍卫没看清,又一盆水泼过来,正好打在他胸口。
“停!
都给我停!”
萧祁快气疯了,跳着脚躲,却忘了脚下还有漏出来的火油,“噗通”一声摔在地上,溅了满身泥污。
他刚想爬起来,手又按在块松动的砖头上,砖缝里的冰水顺着袖口灌进去,冻得他一哆嗦。
巷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巡夜的兵丁举着灯笼冲过来,光柱在萧祁身上晃来晃去。
被惊醒的街坊趴在墙头探头探脑,有人认出他的蟒袍边角,低呼:“那不是三皇子吗?”
“哎哟!
这是干啥呢?
自己放火自己摔泥里?”
“你看他那眉毛!
烧得跟没长似的!”
哄笑声此起彼伏,有人还特意点了灯笼照过来,把萧祁那狼狈样看得一清二楚。
有个卖豆腐脑的老汉举着梆子敲:“三皇子这是给咱们添乐子呢!
明儿个茶馆的说书先生又有新段子了!”
哈哈哈,偷鸡不成蚀把米。
姜福叔,该您出场了。
姜福收到信号,像片叶子似的从墙头飘下来,落在库房门口。
他没看萧祁,只是抬手对着熊熊燃烧的木门虚虚一按——看似轻描淡写的动作,却带起一股强劲的气流,硬生生把蹿得最高的火苗拍了下去。
“好功夫!”
街坊里有人喝彩。
姜福面无表情地看了眼库房,朗声道:“此乃姜家暂存杂物之处,空无一人。
不知三皇子深夜至此,为何纵火烧房?”
这话一出,街坊们的议论声更大了。
“空库房?
那烧个啥劲啊?”
“我看是想栽赃陷害,结果自己反被烧了吧!”
“这叫啥?
纵火自焚?
报应!”
萧祁趴在地上,听着那些议论,气得眼前发黑。
他这才反应过来,库房里根本没什么账册,也没人——刚才火光里看到的那个“人影”,分明是个稻草人!
那稻草人的衣角在风里飘,他还认得,是姜稚常穿的月白色!
“姜稚……姜堰……”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名字,指甲深深抠进泥地里,把青砖都划出了印子。
姜福上前一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声音冷得像冰:“三皇子,光天化日……哦不,深夜纵火,按大靖律,该当何罪?”
萧祁被问得一噎,还想说什么,却见越来越多的人围过来,手里拿着扁担、锄头,眼神里满是鄙夷。
他知道再待下去只会更丢人,挣扎着爬起来,狠狠瞪了姜福一眼,捂着焦糊的眉毛,在侍卫的搀扶下灰溜溜地跑了。
跑过巷口时,还被卖豆腐脑老汉的扁担绊了一下,差点再次摔倒。
看着他那踉跄的背影,街坊们笑得更大声了。
姜福走到拐角,对着空气低声道:“大小姐,都妥了。”
姜稚从阴影里走出来,拍了拍身上的灰。
晚风卷着焦糊味吹过,冻得她打了个哆嗦,可心里却暖烘烘的。
“辛苦姜福叔了。
父亲的安排果然万无一失,我去看看那稻草人。”
她快步走到库房侧面,火势己被暗卫们用湿布控制住,木门虽被熏得焦黑,却没完全烧毁。
那个稻草人歪斜地靠在墙角,身上的月白色外衣沾了不少火星烧出的破洞。
姜稚伸手想把外衣扯下来,指尖却触到一丝冰凉的滑腻——是一根缠在稻草上的玄色丝线,质地细密,带着暗纹。
这线看着眼熟,在哪见过?
她捏着丝线在指间捻了捻,眉头微蹙。
远处,更夫的梆子声又响了起来,敲的是西更天。
这一夜,注定有人无眠。
萧祁回府后摔碎了三个花瓶,对着镜子里自己半焦的眉毛,恨得牙痒痒;而姜稚站在临时落脚点的窗前,手里捏着那根玄色丝线,看着天边渐渐泛起的鱼肚白,握紧了拳头。
萧祁,这才只是开始。
你欠我们姜家的,得一点一点还回来。
窗外的月光不知何时钻了出来,落在她脸上,映出眼底的坚定。
姜福站在廊下,默默握紧了腰间的佩刀——有相爷的智谋,大小姐的机敏,姜家这场仗,未必会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