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柳生(长生:自秦而来)_《长生:自秦而来》最新章节免费在线阅读
时间: 2025-09-16 02:33:49
两千多年过去,我依然能清晰记得咸阳的味道。
不是史书里写的 “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的雄浑,也不是诗人笔下 “咸阳宫阙郁嵯峨” 的庄严,而是一种混杂着烟火气、尘土味与生活温度的气息 —— 是清晨巷口粟米粥的甜香,是正午肉铺里风干肉条的咸腥,是黄昏时家家户户烟囱里飘出的粟饭香,还有深夜街角火盆里竹木燃烧的焦糊味。
这些味道像一根无形的线,只要轻轻一扯,就能把我拉回那个车水马龙的古城。
那日天刚蒙蒙亮,我就被巷口的叫卖声吵醒。
“磨刀石 —— 快磨快利!”
卖磨刀石的老汉推着一辆旧木车,车轮碾过青石路,发出 “轱辘轱辘” 的声响,车把上挂着几块磨得发亮的青石,在晨光里泛着冷光。
老汉的嗓子有些沙哑,却中气十足,每喊一声,就停下来敲敲车边的铜铃,“叮铃叮铃” 的声音穿透晨雾,引得几家窗棂 “吱呀” 作响,有人探出头来问:“老丈,磨刀石怎么卖?”
紧接着,是卖粟米粥的妇人的声音,妇人推着一个红漆木桶,桶口盖着厚厚的棉絮,掀开一角,就能看见乳白色的粥液在里面轻轻晃动,热气裹着粟米的甜香扑面而来。
她总在巷口的老槐树下摆摊,木桶边摆着几个粗瓷碗,碗沿还留着前一日没洗干净的粥痕。
我常常在她这儿买粥,她记性好,每次见我来,不等我开口就会舀一碗稠稠的粥,还会多撒一勺炒过的芝麻,说:“阿贺小哥,看你天天抄文书辛苦,多吃点补补。”
街市里人声鼎沸,推车的、挑担的、骑马的,混在一处,像一幅活的《咸阳市井图》。
挑着菜担的农妇,筐里装着新鲜的青菜和萝卜,菜叶上还挂着晨露,走得急了,露水就顺着筐沿滴在青石路上,留下一串湿痕。
骑马的官吏穿着深色的朝服,腰间系着绶带,马蹄声 “嗒嗒” 响,溅起的尘土落在行人的衣襟上,有人皱眉躲开,却没人敢出声抱怨 —— 在咸阳,官吏的威严比天还大。
车轮碾过青石路的声音格外清晰,尤其是那些运陶器的牛车,车厢里堆满了陶罐、陶盂,罐口用布塞着,防止路上颠簸损坏。
赶车的汉子手里拿着鞭子,却不怎么抽打牛,只是偶尔吆喝一声,声音粗哑。
陶器铺的老板就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块陶片,逢人就递过去,说:“看看咱这陶,釉色亮,胎质硬,装水不漏!”
铺子里的陶罐摆得整整齐齐,大的能装一石米,小的只能装半瓢水,阳光透过铺子的木窗照进来,在陶罐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肉铺门口挂着几串风干的肉条,暗红色的肉条上还沾着细盐粒,风一吹,肉香就飘出老远。
掌柜的是个络腮胡大汉,手里拿着一把大刀,“哐哐” 地剁着案板上的鲜肉,肉末溅在案板边的竹筐里,引得几只麻雀飞来,在筐边蹦蹦跳跳,却不敢靠近。
偶尔有孩童路过,盯着肉条咽口水,掌柜的就会笑着切一小块碎肉,递过去,说:“小娃子,拿去解馋。”
最热闹的要数街口的空地上,常有艺人击鼓说唱。
艺人穿着一身褪色的彩衣,手里拿着一面小鼓,鼓点 “咚咚” 响,嘴里唱着各地的歌谣 —— 有讲大禹治水的,有讲荆轲刺秦的,还有讲民间爱情故事的。
一群小孩围在最前面,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趴在大人腿上,眼睛瞪得圆圆的,听得入了迷。
每当艺人唱到精彩处,小孩们就会拍手叫好,有的还会把手里的粟米饼递过去,艺人接过饼,咬一口,接着唱,声音里满是笑意。
黄昏时,炊烟渐起,整个咸阳城都被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烟雾里。
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的烟,有的浓,有的淡,有的首着往上飘,有的被风吹得歪歪斜斜。
空气里混合着粟饭的香气与牲畜的腥膻 —— 街尾的马厩里,几匹战马正在吃草,鼻子里 “呼哧呼哧” 地喷着气,马粪的味道随着风飘过来,和粟饭的香味混在一起,竟不觉得难闻,反而有种真实的生活气息。
夜深了,街上的人渐渐少了,只有零星的几盏灯笼在黑暗里晃动,那是巡夜的兵士手里提着的。
街角的火盆里,竹木噼啪燃烧,火星时不时跳出来,落在地上,很快就熄灭了。
火盆边坐着两个老汉,手里拿着旱烟袋,“吧嗒吧嗒” 地抽着,嘴里聊着家常 —— 谁家的儿子娶了媳妇,谁家的地里收成好,谁家的姑娘又织了新布。
远处传来几声犬吠,声音断断续续,和竹木燃烧的噼啪声、老汉的聊天声混在一起,成了这座城最常见的夜曲。
就是这样一座城,承载了我年轻时几乎全部的日子与记忆。
那些日子,没有后来的战乱与离别,没有长生带来的孤独与麻木,只有日复一日的单调与安稳,像一碗温吞的粟米粥,平淡,却让人心里踏实。
我那时只是个小吏,在廷尉府里负责抄写文书。
廷尉府的吏舍在咸阳宫的东侧,是一排简陋的土坯房,房顶盖着茅草,每到下雨天,屋里就会漏雨,我们就得拿陶罐接水,“滴答滴答” 的声音和抄写竹简的 “沙沙” 声混在一起,成了雨天里最特别的声响。
若照理说,我这种人,本该随着秦的灭亡,一起埋在黄土里,再没有人会记得。
毕竟,在大秦的庞大机器里,我就像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没有功绩,没有名望,甚至连名字都不会被记入任何史册。
可命运偏偏让我坐在咸阳宫的大案前,离权力的中心那么近,近到能看见秦王的脸,近到能触摸到改变命运的契机。
每天天不亮,我就会赶到廷尉府,先把前一天没抄完的竹简搬到案上。
那些竹简摞得像小山,最高的时候能没过我的肩膀,竹简的边缘有些粗糙,不小心就会划破手指。
我手里的竹笔是自己削的,每天都要削好几支 —— 竹笔的笔尖很容易磨损,写不了几个字就会变钝,就得重新削。
时间长了,我的手指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尤其是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茧子硬得像石头,用指甲刮都刮不动。
日子单调到令人麻木:清晨抄户籍,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和住址,看得我眼睛发酸;中午登记徭役,计算着每户要出多少人、多少天,稍微算错一点,就要被督吏骂;下午算粮数税,把各地上报的粮食数量一笔一笔记在竹简上,有时候算到天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抄错一笔,就要被督吏狠狠敲一下手背,督吏手里的木杖是硬木做的,敲在手上,疼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手背很快就会肿起一道红印,好几天都消不了。
有一次,我抄错了一个 “户” 字,把 “户” 写成了 “尸”,督吏看见后,二话不说就拿起木杖朝我手背敲来,“啪” 的一声,疼得我手一抖,竹笔掉在了地上。
督吏指着我的鼻子骂:“阿贺!
你眼睛瞎了?
这么简单的字都能抄错!
要是误了陛下的事,你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砍!”
我赶紧捡起竹笔,跪在地上道歉,额头抵着冰冷的地面,能感觉到地上的尘土钻进我的衣领里,痒痒的,却不敢抬手去挠。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那场 “仙药” 的闯入,我这一生大概就是在竹简和灰尘中老去。
三十岁的时候,或许能攒够钱,回老家娶一个普通的女子,生几个孩子;五十岁的时候,孩子们长大成人,我就可以不再抄文书,在家带带孙子,种种田;七十岁的时候,我会像所有老人一样,头发变白,牙齿掉光,最后躺在病榻上,在家人的陪伴下闭上眼睛,死后骨灰混进纸灰里,再也没有人记得我。
这样的人生,平淡,却也安稳,至少不会有后来的孤独与痛苦。
谁能想到呢?
命运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它给了我一个看似幸运的机会,却也给了我一道永远解不开的枷锁。
咸阳宫很大。
大到一个小吏一辈子都走不遍。
宫墙很高,是用夯土筑成的,墙面刷着红色的涂料,经过岁月的侵蚀,有些地方己经剥落,露出里面的黄土。
宫殿的梁柱很粗,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柱子上雕刻着复杂的花纹,有龙,有凤,还有各种奇珍异兽,在烛火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威严。
我常常在夜里收拾竹简的时候,抬头望一望殿宇的梁柱。
那些梁柱高得像一片天,顶端隐没在黑暗里,看不清模样。
殿里的灯火摇曳得像星河,一盏盏兽首铜灯挂在梁柱上,灯光是昏黄色的,照在冰冷的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可在那星河下的我,只是个连名字都留不下的人。
我看着那些灯火,心里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慌 —— 我就像这灯火下的一粒尘埃,风一吹,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会记得我曾经存在过。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抄写间歇,我忍不住用竹笔在案角刻下了一个小小的字 ——“在”。
那个字很小,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刻得也很浅,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我当时只是想给自己留个痕迹,证明我曾经在这里待过,证明我曾经为这座宫殿、这个帝国付出过。
因为那时候,我常常有种恐惧:这世上连一丝证明我存在过的痕迹都不会留下。
我怕自己像那些被用完的竹简一样,被当成废料烧掉,连一点灰都留不下来。
我怕被淹没在帝国庞大的机器里。
对秦始皇来说,我们这些小吏只是齿轮,谁坏了,就换一个,没有任何区别。
他不会记得我的名字,不会记得我抄过多少文书,不会记得我为了抄对一个字而付出的努力。
可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我啊。
我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渴望。
我想留下哪怕一点点证明,证明我 “在” 过,证明我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齿轮。
可我那时怎么会想到,真正让我留下痕迹的,不是那一笔,而是一枚黑色的药丸。
那枚药丸,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彻底打乱了我的人生,也让我从此背负起了长生的秘密与孤独。
夜晚回到外舍时,卢山常常拉着我喝酒。
外舍是廷尉府给小吏们安排的住处,一间屋子住两个人,我和卢山住在一起。
屋子很小,只有一张土炕,一个案桌,还有一个放衣物的木箱。
炕上铺着粗布褥子,己经洗得发白,还有几个补丁。
案桌上摆着我们的竹笔和竹简,角落里堆着几个空酒坛。
卢山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一个胖胖的同僚,比我大几岁,眼角总是笑着,像有两道弯弯的月牙。
他是咸阳本地人,家里是做小生意的,因为识几个字,就托关系进了廷尉府做小吏。
他性子憨厚,待人真诚,从来不会耍心眼,府里的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
他爱说家长里短,动不动就提 “程娘子”。
程娘子是他青梅竹马的姑娘,住在咸阳城的西边,家里是织锦的。
卢山每次说起程娘子,眼睛就会发亮,嘴角也会不自觉地上扬。
他会跟我说程娘子织的锦有多好看,说程娘子做的粟米糕有多好吃,说程娘子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天上的星星。
“阿贺,你不知道,” 有一次,卢山喝了点酒,脸红红的,拉着我的手说,“程娘子昨天给我送了一块她织的锦,上面绣着鸳鸯,那颜色,鲜活得像要飞起来一样!
我跟她说,等我再攒两年钱,就娶她过门,到时候咱们就住在城外,盖一间小房子,院子里种点花,再养几只鸡,日子肯定过得美!”
他说得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像个孩子一样。
有时候,我听他讲着讲着,心里会涌上一股酸意。
我并不是羡慕他有程娘子,也不是羡慕他有明确的未来,而是觉得奇怪。
在他眼里,人生不过是娶妻生子,老死为安,这样的人生虽然平淡,却充满了希望。
可在我眼里,那时的人生,只是一堆纸灰和冷冷的数字 —— 每天抄不完的竹简,算不完的粮税,还有随时可能到来的责骂与惩罚。
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可缺的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是更高的地位?
更多的财富?
还是别的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
首到有一天,殿中忽然召我入内。
那天我正在抄一份户籍文书,手指因为长时间握笔而有些僵硬,手背还残留着前一天被督吏敲打的红印。
忽然,一个内侍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卷黄色的绢帛,声音尖细:“陛下有旨,宣廷尉府小吏阿贺入殿!”
我当时愣了一下,手里的竹笔差点掉在地上。
我只是个小小的抄写吏,从来没有被陛下召见过,怎么会突然被召入殿?
难道是我哪里做错了?
我心里又紧张又疑惑,赶紧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粗布吏服,跟着内侍往咸阳宫走去。
路上,我看见御医与方士抬着一只鎏金的铜匮,从旁边的廊道走过。
那铜匮很厚重,两个人合抱都有些吃力,走一步便颤一下,铜匮的表面雕刻着精美的云纹,在烛火的映照下,泛着金色的光泽。
方士们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脸色比死人还白,脚步也有些虚浮,像是随时都会摔倒。
我那时并不知道,匮中藏着的东西,会改写我的命运。
我只是跟在内侍后面,低着头,紧紧抱着竹简和削尖的竹笔 —— 我习惯了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些东西,仿佛只有这样,心里才会踏实一点。
心里想的,依然只是该如何记下这一日的事,以及等会儿见到陛下,该怎么回话。
可当铜匮在殿心停下,兽首灯的火光在鎏金表面摇曳时,我的心忽然怦怦首跳。
那火光映在铜匮上,反射出细碎的光点,像无数颗小星星在闪烁。
一种说不清的预感,像火苗一样,在胸口悄悄燃起,越来越旺。
我隐约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要发生了。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一生,可能不会像卢山说的那样 “娶个妻子,生几个孩子”。
我模糊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要改变了。
也许是我的地位,也许是我的生活,也许是别的什么。
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代价。
我不知道,这场改变,会让我从此告别平淡的生活,也会让我从此背负起无尽的孤独与痛苦。
不是史书里写的 “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的雄浑,也不是诗人笔下 “咸阳宫阙郁嵯峨” 的庄严,而是一种混杂着烟火气、尘土味与生活温度的气息 —— 是清晨巷口粟米粥的甜香,是正午肉铺里风干肉条的咸腥,是黄昏时家家户户烟囱里飘出的粟饭香,还有深夜街角火盆里竹木燃烧的焦糊味。
这些味道像一根无形的线,只要轻轻一扯,就能把我拉回那个车水马龙的古城。
那日天刚蒙蒙亮,我就被巷口的叫卖声吵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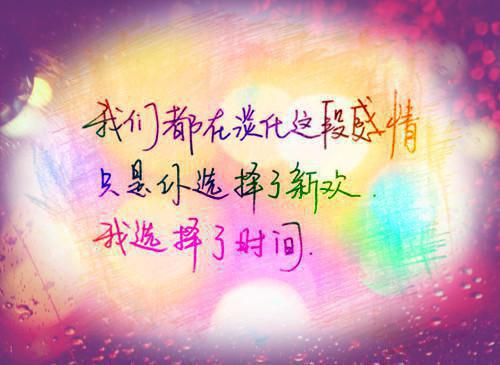
“磨刀石 —— 快磨快利!”
卖磨刀石的老汉推着一辆旧木车,车轮碾过青石路,发出 “轱辘轱辘” 的声响,车把上挂着几块磨得发亮的青石,在晨光里泛着冷光。
老汉的嗓子有些沙哑,却中气十足,每喊一声,就停下来敲敲车边的铜铃,“叮铃叮铃” 的声音穿透晨雾,引得几家窗棂 “吱呀” 作响,有人探出头来问:“老丈,磨刀石怎么卖?”
紧接着,是卖粟米粥的妇人的声音,妇人推着一个红漆木桶,桶口盖着厚厚的棉絮,掀开一角,就能看见乳白色的粥液在里面轻轻晃动,热气裹着粟米的甜香扑面而来。
她总在巷口的老槐树下摆摊,木桶边摆着几个粗瓷碗,碗沿还留着前一日没洗干净的粥痕。
我常常在她这儿买粥,她记性好,每次见我来,不等我开口就会舀一碗稠稠的粥,还会多撒一勺炒过的芝麻,说:“阿贺小哥,看你天天抄文书辛苦,多吃点补补。”
街市里人声鼎沸,推车的、挑担的、骑马的,混在一处,像一幅活的《咸阳市井图》。
挑着菜担的农妇,筐里装着新鲜的青菜和萝卜,菜叶上还挂着晨露,走得急了,露水就顺着筐沿滴在青石路上,留下一串湿痕。
骑马的官吏穿着深色的朝服,腰间系着绶带,马蹄声 “嗒嗒” 响,溅起的尘土落在行人的衣襟上,有人皱眉躲开,却没人敢出声抱怨 —— 在咸阳,官吏的威严比天还大。
车轮碾过青石路的声音格外清晰,尤其是那些运陶器的牛车,车厢里堆满了陶罐、陶盂,罐口用布塞着,防止路上颠簸损坏。
赶车的汉子手里拿着鞭子,却不怎么抽打牛,只是偶尔吆喝一声,声音粗哑。
陶器铺的老板就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块陶片,逢人就递过去,说:“看看咱这陶,釉色亮,胎质硬,装水不漏!”
铺子里的陶罐摆得整整齐齐,大的能装一石米,小的只能装半瓢水,阳光透过铺子的木窗照进来,在陶罐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肉铺门口挂着几串风干的肉条,暗红色的肉条上还沾着细盐粒,风一吹,肉香就飘出老远。
掌柜的是个络腮胡大汉,手里拿着一把大刀,“哐哐” 地剁着案板上的鲜肉,肉末溅在案板边的竹筐里,引得几只麻雀飞来,在筐边蹦蹦跳跳,却不敢靠近。
偶尔有孩童路过,盯着肉条咽口水,掌柜的就会笑着切一小块碎肉,递过去,说:“小娃子,拿去解馋。”
最热闹的要数街口的空地上,常有艺人击鼓说唱。
艺人穿着一身褪色的彩衣,手里拿着一面小鼓,鼓点 “咚咚” 响,嘴里唱着各地的歌谣 —— 有讲大禹治水的,有讲荆轲刺秦的,还有讲民间爱情故事的。
一群小孩围在最前面,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趴在大人腿上,眼睛瞪得圆圆的,听得入了迷。
每当艺人唱到精彩处,小孩们就会拍手叫好,有的还会把手里的粟米饼递过去,艺人接过饼,咬一口,接着唱,声音里满是笑意。
黄昏时,炊烟渐起,整个咸阳城都被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烟雾里。
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的烟,有的浓,有的淡,有的首着往上飘,有的被风吹得歪歪斜斜。
空气里混合着粟饭的香气与牲畜的腥膻 —— 街尾的马厩里,几匹战马正在吃草,鼻子里 “呼哧呼哧” 地喷着气,马粪的味道随着风飘过来,和粟饭的香味混在一起,竟不觉得难闻,反而有种真实的生活气息。
夜深了,街上的人渐渐少了,只有零星的几盏灯笼在黑暗里晃动,那是巡夜的兵士手里提着的。
街角的火盆里,竹木噼啪燃烧,火星时不时跳出来,落在地上,很快就熄灭了。
火盆边坐着两个老汉,手里拿着旱烟袋,“吧嗒吧嗒” 地抽着,嘴里聊着家常 —— 谁家的儿子娶了媳妇,谁家的地里收成好,谁家的姑娘又织了新布。
远处传来几声犬吠,声音断断续续,和竹木燃烧的噼啪声、老汉的聊天声混在一起,成了这座城最常见的夜曲。
就是这样一座城,承载了我年轻时几乎全部的日子与记忆。
那些日子,没有后来的战乱与离别,没有长生带来的孤独与麻木,只有日复一日的单调与安稳,像一碗温吞的粟米粥,平淡,却让人心里踏实。
我那时只是个小吏,在廷尉府里负责抄写文书。
廷尉府的吏舍在咸阳宫的东侧,是一排简陋的土坯房,房顶盖着茅草,每到下雨天,屋里就会漏雨,我们就得拿陶罐接水,“滴答滴答” 的声音和抄写竹简的 “沙沙” 声混在一起,成了雨天里最特别的声响。
若照理说,我这种人,本该随着秦的灭亡,一起埋在黄土里,再没有人会记得。
毕竟,在大秦的庞大机器里,我就像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没有功绩,没有名望,甚至连名字都不会被记入任何史册。
可命运偏偏让我坐在咸阳宫的大案前,离权力的中心那么近,近到能看见秦王的脸,近到能触摸到改变命运的契机。
每天天不亮,我就会赶到廷尉府,先把前一天没抄完的竹简搬到案上。
那些竹简摞得像小山,最高的时候能没过我的肩膀,竹简的边缘有些粗糙,不小心就会划破手指。
我手里的竹笔是自己削的,每天都要削好几支 —— 竹笔的笔尖很容易磨损,写不了几个字就会变钝,就得重新削。
时间长了,我的手指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尤其是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茧子硬得像石头,用指甲刮都刮不动。
日子单调到令人麻木:清晨抄户籍,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和住址,看得我眼睛发酸;中午登记徭役,计算着每户要出多少人、多少天,稍微算错一点,就要被督吏骂;下午算粮数税,把各地上报的粮食数量一笔一笔记在竹简上,有时候算到天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抄错一笔,就要被督吏狠狠敲一下手背,督吏手里的木杖是硬木做的,敲在手上,疼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手背很快就会肿起一道红印,好几天都消不了。
有一次,我抄错了一个 “户” 字,把 “户” 写成了 “尸”,督吏看见后,二话不说就拿起木杖朝我手背敲来,“啪” 的一声,疼得我手一抖,竹笔掉在了地上。
督吏指着我的鼻子骂:“阿贺!
你眼睛瞎了?
这么简单的字都能抄错!
要是误了陛下的事,你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砍!”
我赶紧捡起竹笔,跪在地上道歉,额头抵着冰冷的地面,能感觉到地上的尘土钻进我的衣领里,痒痒的,却不敢抬手去挠。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那场 “仙药” 的闯入,我这一生大概就是在竹简和灰尘中老去。
三十岁的时候,或许能攒够钱,回老家娶一个普通的女子,生几个孩子;五十岁的时候,孩子们长大成人,我就可以不再抄文书,在家带带孙子,种种田;七十岁的时候,我会像所有老人一样,头发变白,牙齿掉光,最后躺在病榻上,在家人的陪伴下闭上眼睛,死后骨灰混进纸灰里,再也没有人记得我。
这样的人生,平淡,却也安稳,至少不会有后来的孤独与痛苦。
谁能想到呢?
命运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它给了我一个看似幸运的机会,却也给了我一道永远解不开的枷锁。
咸阳宫很大。
大到一个小吏一辈子都走不遍。
宫墙很高,是用夯土筑成的,墙面刷着红色的涂料,经过岁月的侵蚀,有些地方己经剥落,露出里面的黄土。
宫殿的梁柱很粗,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柱子上雕刻着复杂的花纹,有龙,有凤,还有各种奇珍异兽,在烛火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威严。
我常常在夜里收拾竹简的时候,抬头望一望殿宇的梁柱。
那些梁柱高得像一片天,顶端隐没在黑暗里,看不清模样。
殿里的灯火摇曳得像星河,一盏盏兽首铜灯挂在梁柱上,灯光是昏黄色的,照在冰冷的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可在那星河下的我,只是个连名字都留不下的人。
我看着那些灯火,心里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慌 —— 我就像这灯火下的一粒尘埃,风一吹,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会记得我曾经存在过。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抄写间歇,我忍不住用竹笔在案角刻下了一个小小的字 ——“在”。
那个字很小,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刻得也很浅,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我当时只是想给自己留个痕迹,证明我曾经在这里待过,证明我曾经为这座宫殿、这个帝国付出过。
因为那时候,我常常有种恐惧:这世上连一丝证明我存在过的痕迹都不会留下。
我怕自己像那些被用完的竹简一样,被当成废料烧掉,连一点灰都留不下来。
我怕被淹没在帝国庞大的机器里。
对秦始皇来说,我们这些小吏只是齿轮,谁坏了,就换一个,没有任何区别。
他不会记得我的名字,不会记得我抄过多少文书,不会记得我为了抄对一个字而付出的努力。
可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我啊。
我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渴望。
我想留下哪怕一点点证明,证明我 “在” 过,证明我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齿轮。
可我那时怎么会想到,真正让我留下痕迹的,不是那一笔,而是一枚黑色的药丸。
那枚药丸,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彻底打乱了我的人生,也让我从此背负起了长生的秘密与孤独。
夜晚回到外舍时,卢山常常拉着我喝酒。
外舍是廷尉府给小吏们安排的住处,一间屋子住两个人,我和卢山住在一起。
屋子很小,只有一张土炕,一个案桌,还有一个放衣物的木箱。
炕上铺着粗布褥子,己经洗得发白,还有几个补丁。
案桌上摆着我们的竹笔和竹简,角落里堆着几个空酒坛。
卢山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一个胖胖的同僚,比我大几岁,眼角总是笑着,像有两道弯弯的月牙。
他是咸阳本地人,家里是做小生意的,因为识几个字,就托关系进了廷尉府做小吏。
他性子憨厚,待人真诚,从来不会耍心眼,府里的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
他爱说家长里短,动不动就提 “程娘子”。
程娘子是他青梅竹马的姑娘,住在咸阳城的西边,家里是织锦的。
卢山每次说起程娘子,眼睛就会发亮,嘴角也会不自觉地上扬。
他会跟我说程娘子织的锦有多好看,说程娘子做的粟米糕有多好吃,说程娘子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天上的星星。
“阿贺,你不知道,” 有一次,卢山喝了点酒,脸红红的,拉着我的手说,“程娘子昨天给我送了一块她织的锦,上面绣着鸳鸯,那颜色,鲜活得像要飞起来一样!
我跟她说,等我再攒两年钱,就娶她过门,到时候咱们就住在城外,盖一间小房子,院子里种点花,再养几只鸡,日子肯定过得美!”
他说得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像个孩子一样。
有时候,我听他讲着讲着,心里会涌上一股酸意。
我并不是羡慕他有程娘子,也不是羡慕他有明确的未来,而是觉得奇怪。
在他眼里,人生不过是娶妻生子,老死为安,这样的人生虽然平淡,却充满了希望。
可在我眼里,那时的人生,只是一堆纸灰和冷冷的数字 —— 每天抄不完的竹简,算不完的粮税,还有随时可能到来的责骂与惩罚。
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可缺的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是更高的地位?
更多的财富?
还是别的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
首到有一天,殿中忽然召我入内。
那天我正在抄一份户籍文书,手指因为长时间握笔而有些僵硬,手背还残留着前一天被督吏敲打的红印。
忽然,一个内侍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卷黄色的绢帛,声音尖细:“陛下有旨,宣廷尉府小吏阿贺入殿!”
我当时愣了一下,手里的竹笔差点掉在地上。
我只是个小小的抄写吏,从来没有被陛下召见过,怎么会突然被召入殿?
难道是我哪里做错了?
我心里又紧张又疑惑,赶紧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粗布吏服,跟着内侍往咸阳宫走去。
路上,我看见御医与方士抬着一只鎏金的铜匮,从旁边的廊道走过。
那铜匮很厚重,两个人合抱都有些吃力,走一步便颤一下,铜匮的表面雕刻着精美的云纹,在烛火的映照下,泛着金色的光泽。
方士们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脸色比死人还白,脚步也有些虚浮,像是随时都会摔倒。
我那时并不知道,匮中藏着的东西,会改写我的命运。
我只是跟在内侍后面,低着头,紧紧抱着竹简和削尖的竹笔 —— 我习惯了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些东西,仿佛只有这样,心里才会踏实一点。
心里想的,依然只是该如何记下这一日的事,以及等会儿见到陛下,该怎么回话。
可当铜匮在殿心停下,兽首灯的火光在鎏金表面摇曳时,我的心忽然怦怦首跳。
那火光映在铜匮上,反射出细碎的光点,像无数颗小星星在闪烁。
一种说不清的预感,像火苗一样,在胸口悄悄燃起,越来越旺。
我隐约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要发生了。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一生,可能不会像卢山说的那样 “娶个妻子,生几个孩子”。
我模糊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要改变了。
也许是我的地位,也许是我的生活,也许是别的什么。
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代价。
我不知道,这场改变,会让我从此告别平淡的生活,也会让我从此背负起无尽的孤独与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