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抢我功法给师弟,我退出宗门(桃子桃子)热门网络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妻子抢我功法给师弟,我退出宗门(桃子桃子)
我叫萧沉舟。青霄门大弟子。娶了掌门独女沈清璃。本以为一生顺遂。可她看小师弟的眼神,像在看光。而我,只是她身边的影子。他叫裴无咎,来门派才三个月。温柔谦卑,人见人爱。
可她为他,拿剑指着我。要我交出残卷功法。我笑了,递上秘籍。心,却碎成了灰。
三年夫妻情,抵不过一个外人。我写下和离书。转身离开剑阁山。江湖风雨起,朝堂暗流涌。
《玄阴真经》现世,九大派血战将至。而我,早已不再回头。1天启七年,秋雨。
剑阁山巅的青霄门藏在云海里,千级石阶盘旋入雾,像一条通往天门的命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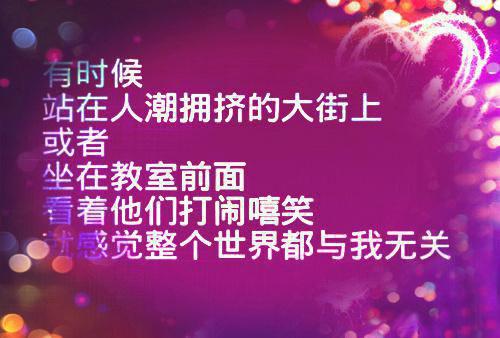
门中讲究“心剑合一”,一念澄明,剑出无尘。可今夜的青霄门,心不净,剑亦浊。
我叫萧沉舟,二十九岁,青霄门大弟子,掌门养子,沈清璃的丈夫。也是今夜,被她持剑逼问的人。雨水顺着玄铁软甲往下淌,滴在青石上,碎成一片片。
我刚从后山禁地回来——那处断崖洞中埋着半卷残破古籍,是我幼年替师父挡剑重伤后所得。
三年来,我默默研习,只觉其中暗藏上古剑阵之秘,却从未示人。它是我的执念,不是我的私产。可她不信。沈清璃来了。她穿着月白长裙,发间一支玉兰簪,像是从旧梦里走出来的样子。可她手里握着剑,剑尖直指我心口,一步之差,就是血光。
她是掌门独女,天之骄女,我曾以为她是心上明月。可今夜,她眼里的光,不是为我亮的。
她开口,声音很轻,却像刀子:“把残卷给我。”我没动。雨水顺着眉骨滑进眼角,刺得有些疼。左眉那道疤,是替师父挡剑留下的。如今,我守了门派十年,护了她三年,却要被她用剑指着要东西。我看着她的眼睛:“你要这卷,是为了门派,还是为了他?
”她指尖一颤。我知道她会这样。裴无咎,那个入门不足三月的小师弟,俊秀温润,说话轻柔,总带着悲悯的笑意。谁看了都会信他。连她也信。
她咬了咬唇:“裴师弟天赋异禀,若得此卷,必能补全‘心剑九式’,振兴我青霄!
”我笑了。笑得极冷。“所以,我的十年,不如他三月?我的三年,不如他三日?”她不答。
剑尖再进半寸。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冻得发青,指甲缝里还有从禁地挖土时留下的黑泥。
这双手替门派挡过外敌,为她挡过暗器,如今却要亲手交出她想要的东西。
我解下腰间油布包裹。雨水打湿布面,墨迹晕开一角,露出“玄阴”二字残痕。我没拆封,也没犹豫,直接递出去。“拿去。”她伸手来接。指尖碰到我手背的瞬间,我感觉到她抖了一下。或许她也记得,去年冬夜,我为她暖过手。可她没停。接过残卷,抱在怀里,像护着什么珍宝。她说:“只要你还在青霄,我就信你。”我闭了闭眼。
再睁开时,心口那点热,彻底凉了。“从今往后,我不在任何人的信里。”我转身,走入雨幕。身后没有挽留,没有声音。只有雨打青石,噼啪作响,像碎玉崩裂。
三年前成婚那夜,她送我一支竹哨,说是漠北传来的老物件,吹一声,人就来了。
她说:“一吹即应,永不失约。”我收着,从没用过。因为我知道,真正在乎的人,不用哨子也会来。可今夜,我从怀里摸出那支竹哨,轻轻放在廊柱下。约断了。它也没用了。
我一步步走下石阶。山门将闭,守门弟子远远望见我,没敢出声。他知道发生了什么。
整个青霄门都知道。可没人拦她拿走残卷。也没人拦我离开。雨越下越大,打在脸上,分不清是雨是别的什么。玄铁软甲早已湿透,压着肩骨生疼。背上的无名古剑一言不发,像它这些年陪我经历的一切。我走过演武场,走过我们曾一起练剑的回廊,走过她最喜欢的那棵老梅树。它还没开花,枝干在雨中扭曲如枯骨。我知道,从今往后,这里不再有我的位置。我不是被逐出师门。我是自己走的。因为有些东西,早就不在了。
三年婚姻,换不来一句“我信你”。她信一个三月的小师弟,不信一个十年的丈夫。
她信他说的话,不信我做的事。她信他能振兴青霄,不信我一直在守护青霄。我不恨。
也不怨。我只是终于明白,有些人,你守得住她的人,守不住她的心。就像这雨,你挡得住一时,挡不住一世。石阶湿滑,我走得慢,但没回头。身后是家,是门派,是曾经以为能终老的地方。前方是江湖,是风雨,是未知的路。
可我不再是那个忍让守护的萧沉舟了。我是开始学会割舍的,萧沉舟。雨还在下。
雾越来越浓。我走下最后一级台阶,身影没入山门外的夜色。青霄门的灯火,在身后渐渐模糊,最终消失。像一场梦醒了。我摸了摸腰间剑柄,冰冷。但手稳。剑还在。
人还在。路,也还在。我不回头。也不能回头。因为回头,只会看见幻灭。而我,还得往前走。哪怕前路无家。哪怕此生无灯。只要剑未断,人未倒,我就还能走。
走到哪算哪。走到哪,哪就是归处。雨声盖过脚步。山风卷着湿气扑在脸上。我走出十里,才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剑鸣。不知是她练剑,还是风过剑穗。我不想知道。也不再关心。
我只知道,从今夜起,我不再为谁而战。也不再为谁而留。残卷给了,婚也散了。心门关了。
接下来的路,我自己走。江湖很大。青霄很小。小到容不下一个真心人。我萧沉舟,不恨江湖。只厌虚情。雨停时,天快亮了。我站在山道拐角,抬头看了眼东方。
灰云裂开一道缝,光透出来。像剑锋划破黑暗。我整了整衣甲,继续前行。身后的青霄门,终成过往。而我,才刚开始。学会放手。学会独行。学会,不再等谁的信。
2山道拐角的雾气还没散,我踩着湿泥继续走。十里外有座破庙,塌了半边屋顶,神像倒在地上,裂成两截。我靠在柱子边坐下,背上的剑蹭着粗糙的石面,发出沙的一声。
从怀里掏出笔砚,是十年前师父赐的那套,黑木匣子边角磨出了毛刺。打开时墨条卡了一下,我用拇指顶进去,指腹蹭到干涸的墨渣,粗糙扎手。庙里没灯,天光从破瓦缝里漏下来,灰蒙蒙照在纸上。纸是普通的粗宣,受了潮,边缘微微卷起。我把它压平,袖口扫过,沾了层薄灰。研墨很慢。墨条在砚台里转了十几圈,才出汁。黑得发稠,像凝住的血。
我盯着墨池,里面映出一张脸:眼睛底下青黑,左眉那道疤横在冷光里,像一道旧裂痕。
没看多久。闭眼,静坐。心要冷下来才能写。热的时候写,会写出怨,会写出痛,会写出“为什么”。可我不需要那些。我已经不是要解释的人了。半炷香后,提笔。
笔尖落纸,第一句是:“萧沉舟与沈清璃,缘尽于天启七年秋雨。”字很稳,没有抖。
接着写:“自此各安天涯,勿复相念。书成之日,两不相欠。”没有抬头称“妻”,没有落款写“夫”。三年婚姻,不靠名分撑着。写完了,右手拇指按在纸角,蘸了点唾沫,压出一个印。红的。折好,放进神龛。那里躺着半截香炉,我把它推到最里侧,和离书夹在砖缝里,风吹不着,雨淋不到。不交给谁,也不寄出。天地为证就够了。
做完这些,把笔砚收进木匣,扣紧。这东西陪了我十年,从入门到成亲,从守山门到今夜出走。现在它完成了最后一件事。我靠回柱子,闭眼。身体累到了底。腿僵,肩沉,后背那道旧伤隐隐发酸。可脑子清楚。比雨里下山时更清楚。我不是被赶走的。
我是自己走的。这个念头得立住。不然以后每走一步,都会回头。外头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踩在泥里,啪嗒啪嗒。来的人不快,但没停。门被推开,陈砚站在门口。
他穿着青霄门弟子的灰袍,肩头湿了一片,手里拎着个布包,另一只手拄着根木棍,裤脚沾满泥浆。看见我,他喘了口气,声音发颤:“师兄……我追到了。”我没起身。
他走进来,把布包放在地上,打开,是件干衣裳,还有两个硬饼。“你没吃东西吧?
我带了点路上的。”我没接。他蹲下来,看着我:“师兄,你真要走?”我点头。
“掌门还不知道这事!清璃姐她……她可能是被人蒙蔽了!裴无咎那小子才来几天?
她怎么会信他不信你?”我没说话。“你要是现在回去,还能挽回!
大不了我陪你去当面问她!你为青霄做了那么多,她不能这么对你!”他越说越急,声音发抖。我抬手,打断他。“陈砚。”他停了。“你追下来,我很感激。
你是唯一一个追下来的人。”他眼眶红了。“可我已经写了和离书。”“什么时候?
”“刚才。”他猛地站起来,冲到神龛前,伸手乱摸,摸出那张纸,展开看。只一眼,手就抖了。“你……你真写了?”我看着他:“写了。”“那你还……还叫我来?
”“我没叫你来。是你自己来的。”他愣住。我把木匣放进包袱,系紧。
然后解下腰间那块青霄门弟子玉牌,白玉镶边,正面刻着“青霄”二字,背面是我的名字。
递给他。他没接。“师兄,这牌子是你身份!没了它,你就真的不是青霄的人了!
”“我已经不是了。”“可你还能回来!”“不回来。”他咬着牙,眼里有泪:“为什么?
就因为她一时糊涂?就因为一张纸?你十年的心血,十年的守候,全扔了?”“不是扔了。
”我站起身,把玉牌塞进他手里。“是放下了。”他低头看着玉牌,手指紧紧攥着,指节发白。“替我守着它。”他抬头。“如果有一天,青霄门清净了,没人再拿情义当刀子使,没人再用信任换背叛——你就把它挂回山门。
”“我不求它认我回来。”“只求它还记得,曾经有过不为名利、只为守道的人。
”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我把包袱背上,手按在剑柄上。“你回去吧。再不走,天黑前赶不回山门。”他突然扑通跪下。“师兄!你不能走!你是大弟子!是掌门养子!
是……是她丈夫!”我扶他起来。力气不大,但他站直了。“都不是了。”“从今往后,我只是萧沉舟。”他死死抓住我的袖子:“那你去哪儿?江湖这么大,你一个人……”“走到哪,算哪。”“可你为青霄付出了一切!”“付出不是为了回报。
”“那为了什么?!”我顿了顿。“为了心不亏。”他松了手。我转身,走向门口。
外头雾散了些,晨光浮在树梢上,路像一根灰线,伸向远处。刚迈出去一步,他喊住我。
“师兄!”我停住,没回头。“若你走了,谁来护这江湖正道?!”我手抚上背剑。
“正道不在山门,而在人心。”“我不护门。”“护的是剑不染血,人不欺心。”说完,抬脚。雾气卷上来,裹住身子。路在脚下,往前延伸。我不回头。也不能回头。
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抽泣。我没停。走了一段,肩上的包袱松了,我伸手去扶,指尖碰到剑穗,凉的。雾越来越浓,脚下的土由湿转干,踩上去不再打滑。远处有鸡鸣,一声,两声。有人家。有炊烟。有新的一天。我整了整衣甲,继续往前。手始终按在剑柄上。
3雾散后路清楚了些,脚底踩的土也硬了。我沿着官道往北,天快黑时进了边城。城不大,但有几家镖局,来往商队多,夜里也吵。挑了家叫“镇远”的,院子偏,墙厚,门板结实。
掌柜的见我背剑穿甲,只问了一句去处,我说暂住两晚。他没多话,收了钱,指了西厢一间空屋。屋子小,一床一桌一凳,墙角堆着半袋陈年米粮,味儿发潮。
我用包袱垫了床板,把剑放在枕边。没点灯,坐到天全黑。外头雨又下了起来,敲在瓦上,一声紧一声。我靠着墙,闭眼。不是要睡,是让身子歇。腿还在发沉,肩背那道旧伤贴着冷墙,隐隐抽着。但脑子没停。从写下和离书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走得再远,有些事也不会放过我。所以当屋顶传来第三声轻响时,我没动。
瓦片被掀开一条缝,雨水滴进来,砸在桌面上,啪的一声。我等他落下来。人影从房梁扑下,刀光直刺心口,走的是偏锋,快而低,专挑肋下空当。是外门的“蛇行刺”,但加了杀意,收不住手。我侧身,剑鞘撞他手腕,同时抽剑出半尺,刃口磕上刀身,一声脆响,短刀断成两截。他一愣,我抬膝撞他胸口,人往后退,撞翻了桌子。闪电劈下来,照亮他脸上的黑巾。我没追,只把剑横在身前,说:“赵七,你当外门执事十年,不该用这路子。”他没答,反手从腰后抽出一柄细刺,贴着地面向我脚踝扫来。我踩住刀尖,剑柄下压,砸他鼻梁。他仰头,我顺势扯下黑巾。脸露出来时,我眼皮跳了一下。真是赵七。
他右耳缺了半片,是早年押镖被马贼咬的,门里人人都认得。可现在这张脸,青白浮肿,眼窝发黑,像是熬了几天没睡。“谁派你来的?”他不答,喉咙里滚出一声低笑,嘴角突然溢血。我扑过去掰他嘴,已经晚了。牙囊破了,毒发得快,他抽了两下就不动了。
屋子里静下来。雨还在下,桌上那袋米被掀翻,白粒撒了一地。我蹲下,在他怀里摸了摸。
外衣空的。内襟缝着一块硬物,指尖抠开线头,掏出一块玉符。冷的。正面雕着一头狼,竖耳张口,是北燕军纛。背面刻了两个字:“寅三”。我盯着那字看了很久。
寅三是暗桩编号,青霄门外务密档里记过一次——三年前有封北燕密信被截,落款就是“寅三报”。当时掌门查了半个月,没结果,最后不了了之。赵七一个执事,碰不到密档。但他能碰外务。裴无咎入门三月,就管了外门调度,清璃亲批的。
我捏着玉符站起来,走到门边。门没关严,雨潲进来,打湿了门槛。街对面是家酒肆,灯还亮着,有人在划拳,声音混着雨声传过来。我低头看赵七的尸体。他鞋底沾着泥,是山道那种湿红土,不是边城的灰沙。说明他不是本地埋伏,是追来的。从青霄门追到边城,三百里路,就为杀我灭口?不,是怕我知道什么。我回身把玉符塞进里衣,贴胸口放着。
然后扯下床单,把尸体裹了,拖到墙角。又把断刀和黑巾收进包袱,桌椅摆正,米粮扫回袋里。做完这些,我坐回床沿。窗外雨势小了,但风起来了,吹得窗纸啪啪响。
我闭上眼,脑子里过的是这三年的事。裴无咎来那天,天也下雨。他站在山门外,衣裳湿透,说是仰慕青霄剑法,愿执帚三年。掌门看他根骨好,收了。三个月后,他写出一篇《心剑九式补遗》,字字合道。清璃说他是奇才。半年后,他替门中老仆挡了一箭,自己伤了腿。清璃亲自煎药。一年后,他提议重修外门剑谱,清璃让他主笔。两年后,他开始替掌门批外务折子,清璃说他细心。
三年前那封被截的北燕密信,就是从外务口漏出去的。时间对上了。我睁开眼,手摸到剑柄。
不是为了报仇。我早就不为那个家了。可若裴无咎真通了北燕,不止青霄要塌,九大派都得乱。江湖不是山门,不是谁说了算的地方。但江湖得有规矩。规矩不在纸上,在活人心里。要是连这个都没了,我当年守山门、挡剑、断眉,图什么?我起身,把包袱背好,剑挂回肩上。不能留。这屋住不得了。我刚伸手去推门,外面传来马蹄声。
三匹马,从东街来,速度不快,但没停。我收手,侧身贴墙。马蹄声在门口停了。
门被敲了两下。“里头住的可是萧爷?”是镖局的伙计,声音熟。白天我住进来时他迎的。
我没应。“萧爷,您包袱落店外了,掌柜的让我给您送来。”我没动。包袱白天就在我背上。
哪有什么落店外。外头等了几息,又敲了两下。“萧爷?”我握紧剑柄。门缝底下,慢慢渗进一滴水。不是雨。是黑的。4门缝下的黑水还在缓缓渗进来,一滴一滴,落在地上发出轻微的响声。我贴着墙,手按在剑柄上,没有动。门外安静了几息,马蹄声远去,三匹马离开的速度不快,像是故意留个空档让人反应。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那滴黑水——不是血,也不是泥水,是某种药汁,带腥气,能蚀布。
镖局伙计不会用这种东西送信。脚步声是从东街拐角传来的。很慢,踩在积水里,一步一顿,像是走不动了。布鞋底磨得发毛,脚踝虚浮,每一步都带着喘。这不是刺客的步法,也不是寻常赶路的人。她停在门口。我没有开门。手指松开剑柄,移到门闩上,轻轻顶住。
“萧沉舟……”她的声音哑了,像是哭过很久。门被轻轻敲了一下,力道小得几乎听不见。
我没应。“我知道你在里面。”她咳了一声,呼吸急促,“我……走了三天。从青霄门下来,一路没停。”我依旧不动。门缝里能看到她的脚,湿透的素裙下摆沾着泥,脚趾在破鞋里发白。她没穿掌门之女该有的绣鞋,也没带随从。“裴无咎……他不是人。
”她声音抖了一下,“他给我看的《心剑九式补遗》,是假的。他用共情术让我信他,说他能振兴青霄……可他杀了我爹。”我眼皮没动。“那天夜里,他说爹病重,让我去丹房取药。我去了。回来时……爹已经断气了。裴无咎说他是旧疾复发,可我后来才发现,丹炉里的药渣被人换过。是毒。”她喘了口气,像是撑不住,膝盖一软,整个人滑坐在门槛上。“我翻他枕头,找到这块玉符……半块。上面刻着狼头,和你那本残卷上的印记一样。”我终于动了。不是开门,而是伸手,将门拉开一条缝。
她抬起头。脸色青白,眼窝塌陷,头发散乱,玉兰簪早就不见了。
三年前那个站在演武场中央,被众人簇拥的沈清璃,现在像个逃荒的妇人。
她怀里抱着一个油布包,双手紧紧攥着,指节发紫。我看她手。她明白我的意思,颤抖着打开油布。半块玉符躺在里面,正面雕着狼首,竖耳张口,背面刻着“寅二”二字。
我认得这纹路。和我怀里那块“寅三”符的断口形状能对上。但我没伸手接。她盯着我,眼里有泪,也有最后一丝希望:“你信我吗?”我没有回答。只是慢慢抬手,将门一点点合上。木门撞上门环,发出一声闷响。她没喊,没拦,只是坐在那里,像被抽了骨头。我靠在门板上,听见外面传来一声极轻的呜咽,随即被雨声盖住。
屋子里黑着。我走到床边,坐下,从怀里取出那块“寅三”符,放在掌心。
又从包袱里拿出断刀、黑巾、赵七的尸体裹布——这些都不能留。我起身,把床单撕成条,将尸体绑紧,塞进墙角米袋后。刀和黑巾用油布包好,压在桌下。做完这些,我吹灭了残烛。
窗外,雨没停。她还在外面。我没再看她。但我知道她没走。坐了大概半炷香,我从怀里把两块玉符拿出来,拼在一起。“寅二”和“寅三”接缝处有一道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