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集之衣劫秦世襄秦绍远热门小说阅读_完本完结小说民间故事集之衣劫秦世襄秦绍远
一件染血的戏服, 一个枉死的名伶, 一段纠缠两代人的诅咒。一民国二十七年,秋,天津卫。梨园行当里最近出了件蹊跷事。
名角儿筱玉楼刚在《贵妃醉酒》里唱罢最后一句"好似嫦娥下九重",人还没回到后台,就直挺挺地倒在了戏台上。等班主和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扶起,才发现人已经没了气息,嘴角却挂着一丝诡异的笑。
最邪门的是他那身戏服——那件价值不菲、绣着百鸟朝凤的贵妃宫装,前襟不知何时染上了一片暗红,像极了干涸的血迹,却寻不到半点伤口。
“是猝痧症中风。”请来的老郎中把了脉,摇摇头,“这行当辛苦,日夜颠倒,常有的事。”班主心里明镜似的,筱玉楼才二十五,身子骨健朗得很,哪来的猝痧症?
可他不敢声张,戏班子最怕这种晦气事。草草办了白事,将那件染血的戏服连同筱玉楼的其他行头一并打了包,塞进箱底,盼着日子久了,人们自然就忘了。然而有些事,偏偏忘不掉。戏班子有个跑龙套的小伙子,名叫栓子,平时负责给角儿们打理行头。筱玉楼头七那晚,栓子梦见角儿穿着那件染血的宫装,站在他床前,也不说话,只伸出一根水葱似的手指,直直指着他。栓子惊醒后一身冷汗,总觉得戏箱里有什么动静。他战战兢兢地打开箱子,一股陈旧血腥气混着胭脂水粉味儿扑面而来——那件戏服竟自己摊开了,前襟那片暗红在月光下仿佛活了过来,隐隐流动。栓子吓得魂飞魄散,第二天就卷铺盖跑了,临走前逢人便说筱老板死得冤,那戏服吸了他的魂,成了精了。流言蜚语像秋后的野火,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戏班子生意一落千丈,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班主没法子,只能咬牙清理旧物,那箱“不祥”的行头,被他一狠心,贱卖给了一个走街串巷的旧货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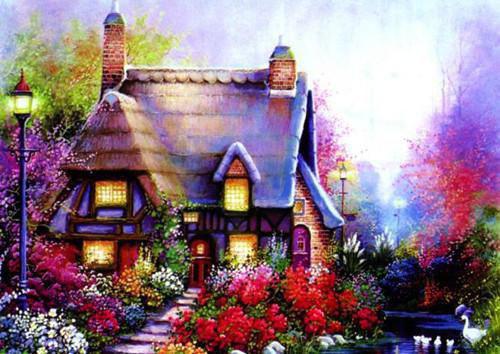
二旧货郎姓冯,人称冯挑子。他是个不信邪的,只觉得捡了个大便宜——那箱行头料子好、绣工精,光是上面缀的珍珠亮片抠下来也能卖不少钱。他乐滋滋地挑着担子,一路晃悠到了城西的估衣街,打算找个相熟的铺子脱手。估衣街鱼龙混杂,两旁挤满了收购和贩卖旧衣物的铺摊。
空气里弥漫着樟脑、霉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无数陌生人的体息。在这里,一件件曾经贴身的衣物,带着原主人的命运印记,流转于陌生人的手中。
冯挑子走进常打交道的“张记估衣铺”。掌柜老张头拿起那件最扎眼的贵妃戏服,对着光仔细瞅了瞅那片暗红,眉头拧成了疙瘩。“老冯,这衣裳…哪来的?透着股邪性啊。
”“嗨!能哪来的?梨园行里收来的,角儿唱戏出汗染的胭脂红呗!”冯挑子故作轻松,声音却有点发虚,“您老给个价,合适就出您这儿了。”老张头沉吟片刻,伸出三根手指。
冯挑子心里嫌低,却又不敢久留这东西,生怕晦气缠身,便咬咬牙成交了。
那件戏服随后被老张头挂在了铺子最不起眼的角落,标了个不高不低的价,指望着哪个不懂行又图便宜的主顾赶紧把它请走。三半个月后,一个穿着体面、面色却有些惶惑的中年男人走进了张记估衣铺。他叫秦世襄,是本地一所中学的国文教员。近日家中连遭变故,老母病重,急需用钱,偏他又是个好面子的文人,不肯向亲友借贷,便想着偷偷当掉几件暂时穿不着的旧衣裳应应急。铺子里各式旧衣琳琅满目,秦世襄却一眼就被角落里那件戏服吸引住了。并非因为它华美——事实上,它蒙着尘,显得有些黯淡——而是因为一种难以言喻的熟悉感。他鬼使神差地走过去,伸手触摸那冰凉的绸缎。指尖划过那片暗红时,他竟微微一颤,仿佛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
“掌柜的,这…这件怎么卖?”他听见自己问。老张头抬眼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那戏服,报了价,还好心添了一句:“这位先生,这衣裳…来历有点说不清,您要是自个儿穿,最好再掂量掂量。”秦世襄却像没听见后半句。价钱出乎意料地合适,他甚至没还价就买下了。他心里盘算着:这绣工、这料子,拆洗一下,改成一件像样的长衫或者给母亲做件袄面,应该很不错,能省下不少布钱。
他将戏服仔细包好,夹在腋下,走出估衣街时,天色已近黄昏。秋风卷起落叶,打着旋儿扑在他身上,他莫名地感到一阵寒意,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却总觉得身后似有若无地跟着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像是有人在轻轻踩着锣鼓点。
四秦世襄的母亲秦老太太病榻缠绵已有些时日了。见了儿子买回的料子,她昏花的老眼却突然亮了一下。
“这…这绣活真鲜亮…”她枯瘦的手摩挲着戏服上繁复的绣纹,“像是…宫里的手艺…”“娘,您眼力好,这料子厚实,给您改件新袄子过年穿。
”秦世襄强笑着安慰母亲。当夜,秦世襄在灯下拆改戏服。剪刀划开丝线时,他总觉得那绸缎之下似乎还有一层东西,触感异样。
鼻尖萦绕的那股淡淡的、混合着胭脂和陈旧气息的味道,也愈发浓烈起来。
更让他心神不宁的是,他总听见窗外有人幽幽地哼唱着《贵妃醉酒》的调子,断断续续,如泣如诉。他几次推开窗户,外面却只有空荡荡的院落和清冷的月光。“大概是最近太累,幻听了。”他摇摇头,继续手上的活计。戏服改好那日,秦老太太精神头竟难得地好了起来,非让儿子扶她起身,试穿新袄。那件用染血宫装改成的深紫色缎袄穿在她干瘦的身上,显得空荡荡的,却自有一股诡异的、不合时宜的华贵气度。老太太对着模糊的铜镜照了又照,浑浊的眼里泛起奇异的光彩。她突然捏起兰花指,踩着蹒跚的碎步,竟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腔调圆润哀婉,竟颇有几分名伶风韵。秦世襄惊呆了。他母亲是旧式家庭妇女,从未学过唱戏!“娘!
您…您这是怎么了?”秦老太太仿佛没听见,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水袖一甩尽管并没有水袖,眼神迷离地望着虚空,继续唱着:“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唱到“好似嫦娥下九重”一句时,她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
脸上的表情凝固了,身子猛地一僵,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娘!”秦世襄慌忙上前抱住母亲。
秦老太太在他怀里,眼睛瞪得极大,瞳孔里充满了极致的恐惧,仿佛看到了什么无比可怕的东西。嘴角却像被人强行拉扯般,向上弯起一个极其僵硬诡异的笑容。和半年前死去的筱玉楼,一模一样。
五秦老太太的丧事办得凄凉。邻里间窃窃私语,都说秦家撞了邪,那件来路不明的旧袄子是催命符。秦世襄悲痛欲绝,又惊又惧,他将那件惹祸的缎袄卷起来,想一把火烧了干净。可就在他要点火时,一个声音在他脑中阻止了他——万一是这衣服里藏着母亲枉死的线索呢?
万一…万一有什么冤屈附在上面?他是个读书人,本该不信这些怪力乱神,但母亲的死状太过诡异,由不得他不胡思乱想。他最终没下得去手,而是将缎袄重新锁进了母亲生前陪嫁来的那只旧木箱里,贴上封条,藏在阁楼最深的角落,企图将那段可怕的记忆一同封存。日子还得过。秦世襄变卖了部分家产,勉强偿还了为母亲治病欠下的债务,生活逐渐重回轨道。
那件邪门的衣服似乎随着封印而安静下来,再无异状。他甚至开始说服自己,母亲的死或许真的只是巧合,是积劳成疾的突然爆发。一年后的某个雨夜,雷声轰鸣。
秦世襄被一阵凄楚的唱戏声惊醒,那声音清晰无比,仿佛就在他的枕边!
“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是《贵妃醉酒》!是那个调子!他浑身汗毛倒竖,猛地坐起身。黑暗中,他依稀看到窗外似乎立着一个穿着宫装的身影,水袖长舞,身段窈窕,但脸孔却模糊不清。“谁?!”他厉声喝问,声音却抖得不成样子。没有回应。
只有那唱腔还在继续,哀怨婉转,穿透雨声和雷声,一字字敲在他的心上。
秦世襄连滚带爬地冲上阁楼。封条完好,锁也锈迹斑斑,似乎从未有人动过。
他颤抖着手打开木箱——里面空空如也!那件染血的缎袄,不翼而飞了!
巨大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他连滚带爬地跑下阁楼,想逃离这栋令人窒息的房子。仓皇间,他脚下一滑,从楼梯上重重摔了下去,后脑勺磕在坚硬的水泥地上,顿时眼前一黑。
在彻底失去意识前,他最后看到的,是楼梯转角处,一抹熟悉的、华贵的紫色缎子衣角,轻轻飘过。六秦世襄没有死,但摔断了腿,也在额头上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疤痕。更严重的是,他变得有些神经质,时常自言自语,对一件“紫色的衣服”充满恐惧。
学校的工作自然是保不住了,家计再次陷入困顿。他的儿子秦绍远,那时刚满十八岁,正在北平读大学。得知家中巨变,父亲又神志不清,只得忍痛辍学,回到天津卫,扛起家庭重担。年轻的秦绍远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受过新式教育,坚信科学理性。
他对父亲所说的“邪衣索命”、“冤魂唱戏”之类的呓语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父亲遭受连番打击后产生的癔症和幻觉。他将父亲的病归咎于贫困和压力,决心努力赚钱,治好父亲的病,重振家声。他在码头找了份记账的辛苦活儿,每日早出晚归。
微薄的薪水除了维持家用和给父亲抓药,所剩无几。
生活的重压让这个年轻人迅速褪去了青涩,变得沉默而坚韧。然而,有些东西,并非你不信,它就不存在。一个夏夜,秦绍远加班晚归。月色如水,将小巷照得一片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