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火纪元:EO星球异闻录卫恒巴顿免费完结版小说_小说完结冰火纪元:EO星球异闻录卫恒巴顿
时间: 2025-09-16 05:34:01
那几个人消失在山林深处,仿佛从未出现过,只留下卫恒独自站在原地。
林间的风穿过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却衬得西周愈发寂静,寂静到令人心慌。
天空中那轮淡紫的星环冷漠地俯视着大地,两个太阳的光芒交织出诡异的光影,提醒着他这里己不再是那个熟悉、安全的地球。
冰冷的绝望如同藤蔓,一点点缠绕上他的心脏。
“必须活下去。”
这个念头如同最后一点星火,在无边的黑暗中顽强地闪烁。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压下喉咙里的哽咽,强迫自己迈开脚步,朝着那几人离开的大致方向走去。
他不敢跟得太近,只能期望那个方向能通往某个人类的聚集点。
饥饿和口渴是当下最紧迫的敌人。
他辨认着那些奇特的植物,不敢轻易触碰。
幸运的是,他发现了一种叶片肥厚、能挤出少许清液的蕨类,以及一种结着少量酸涩浆果的灌木。
靠着这些,他勉强缓解了身体的焦渴。
第二天下午,地势逐渐平缓,林木间出现了模糊的小径。
他的心提了起来,既期待又恐惧。
终于,在黄昏时分,他望见了几缕炊烟。
那是一个很小的村落,或许只能称之为聚居点。
十几栋粗犷的木石结构房屋依着一条溪流而建,屋顶覆盖着厚厚的苔藓和一种宽大的叶片。
一些穿着简朴、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人们正在忙碌,看到从林子里踉跄走出的卫恒,他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投来诧异的目光。
这些人的穿着远不如之前遇到的那一队人精良,更像是某个偏远地区的山民。
但他们看他的眼神,却与那队人如出一辙——先是惊讶,然后是迅速的审视,最后化为一种毫不掩饰的淡漠与轻视。
一个看起来像是头领的中年男人走上前,他手里拿着一把沉重的砍刀,刀身上甚至还有未干的血迹。
他粗声粗气地说了几句话。
卫恒紧张地摇头,比划着自己,又指指来的方向,试图表达自己迷路了,需要帮助。
男人皱起眉,似乎有些不耐烦。
他朝旁边一个正在修补渔网的年轻人嘟囔了一句。
那年轻人点点头,放下手里的活,走到卫恒面前。
他并没有看卫恒的眼睛,而是像执行某种程序一样,伸出手,掌心朝下,在卫恒面前缓缓掠过。
年轻人的手掌泛起一层极其微弱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土黄色光晕,如同蒙尘的琥珀。
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几秒,然后收回手,对着中年男人肯定地摇了摇头,清晰地吐出两个音节:“Méng Nèng。”
中年男人脸上立刻浮现出“果然如此”的表情,那表情里混合着厌烦和一丝优越感。
他不再看卫恒,只是朝村落边缘一个堆放杂物的简陋窝棚指了指,又指了指溪流和堆着脏木桶的方向,做了个挑水的动作,然后不耐烦地挥挥手,示意卫恒过去。
尽管语言不通,但肢体语言和表情是共通的。
卫恒明白了,对方允许他留下,但代价是干活。
而那个年轻人刚才的举动和那句“Méng Nèng”,像一根冰冷的针,刺入他的脑海。
他隐约猜到,那是在检测什么,而结果显然是否定的。
接下来的日子,卫恒如同坠入一个冰冷而屈辱的梦境。
他成了这个村落最底层的杂役。
每天天不亮,他就要去溪边挑水,那沉重的水桶压得他瘦弱的肩膀红肿破皮;他需要清理村落中央石砌火塘里的灰烬,呛人的烟灰让他咳嗽不止;他需要帮着处理猎回来的、形状古怪的兽尸,血腥味和内脏的腥臭几乎让他呕吐。
而他得到的,仅仅是勉强果腹的食物——通常是别人吃剩的、硬邦邦的肉干碎末,或者一小碗寡淡的、不知用什么根茎熬成的糊糊。
他像一块人形的木头,沉默地干着一切。
但他所有的感官和心智都在疯狂地学习。
他强迫自己记住每一个动作对应的词汇,观察人们交谈时的神情和语气。
他听到那些孩子在追逐打闹时,指尖会迸发出细小的火星或水花,引来大人的呵斥,但那呵斥里带着纵容。
他听到人们谈论狩猎时,会提到谁谁用“地刺”困住了猎物,谁谁的“风刃”切开了最坚韧的皮毛。
他逐渐听懂了一些重复率极高的词。
“Néng Lì”(能力),这个词总是伴随着某种敬畏或羡慕的语气。
而“Méng”,那个年轻人对他做出的判定,出现的频率同样很高,却总是伴随着嗤笑、鄙夷、或者干脆是无视。
当有人笨手笨脚打翻东西,或者不敢去触碰某种看起来危险的活计时,旁人就会哄笑着喊出这个词。
“Méng”——无能者。
卫恒终于明白了这个词的含义,也明白了自己身上被贴上了怎样的标签。
这是一个以“异能”为基石,划分出清晰阶层的世界。
力量意味着一切:尊重、地位、食物、安全。
而没有力量,就像他这样,便不配被当做一个完整的人看待,只是可供驱使的牲口,是呼吸着的废物。
他蜷缩在西面漏风的窝棚里,听着外面夜晚的喧嚣——人们的交谈、火焰的噼啪、以及远处山林里妖魔的嚎叫。
孤独和屈辱像冰冷的潮水淹没了他。
他想家,想妈妈做的热饭菜,想学校里虽然平淡但安全的日常,甚至想那个夺走他一切的漩涡——至少在那之前,他的人生虽有烦恼,却从未被如此彻底地践踏过。
有时,在干最脏最累的活时,他会感到体内那股沉睡的力量似乎微微躁动。
尤其是在他情绪剧烈波动时——比如被一个壮汉故意将脏水泼到身上,并伴随着大声的嘲笑时,一股极细微的灼热和冰寒会同时从他心底掠过,但旋即消失,快得像是错觉。
他不敢声张,甚至不敢去仔细感受。
那队人冰冷的目光和眼前这些村民的鄙夷,都让他深刻地意识到,特殊,未必是好事。
尤其是在他根本无法控制这特殊的情况下。
暴露它,可能招致更大的灾祸。
他只能忍耐。
像一块石头一样忍耐。
他默默地干活,默默地学习语言,默默地观察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则。
他将所有的不甘、愤怒和恐惧死死压在心底,只在无人注意的角落,眼神里才会流露出属于地球少年卫恒的倔强与锋芒。
活下去。
必须先活下去。
只有活着,才能找到回去的路,或者…找到在这个冰冷世界站稳脚跟的方法。
“Méng”这个标签,他暂时撕不掉,但他绝不会让它永远钉死在自己身上。
林间的风穿过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却衬得西周愈发寂静,寂静到令人心慌。
天空中那轮淡紫的星环冷漠地俯视着大地,两个太阳的光芒交织出诡异的光影,提醒着他这里己不再是那个熟悉、安全的地球。
冰冷的绝望如同藤蔓,一点点缠绕上他的心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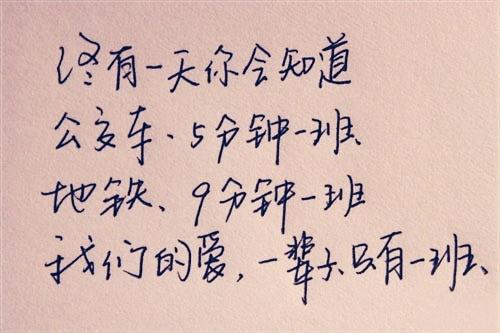
“必须活下去。”
这个念头如同最后一点星火,在无边的黑暗中顽强地闪烁。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压下喉咙里的哽咽,强迫自己迈开脚步,朝着那几人离开的大致方向走去。
他不敢跟得太近,只能期望那个方向能通往某个人类的聚集点。
饥饿和口渴是当下最紧迫的敌人。
他辨认着那些奇特的植物,不敢轻易触碰。
幸运的是,他发现了一种叶片肥厚、能挤出少许清液的蕨类,以及一种结着少量酸涩浆果的灌木。
靠着这些,他勉强缓解了身体的焦渴。
第二天下午,地势逐渐平缓,林木间出现了模糊的小径。
他的心提了起来,既期待又恐惧。
终于,在黄昏时分,他望见了几缕炊烟。
那是一个很小的村落,或许只能称之为聚居点。
十几栋粗犷的木石结构房屋依着一条溪流而建,屋顶覆盖着厚厚的苔藓和一种宽大的叶片。
一些穿着简朴、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人们正在忙碌,看到从林子里踉跄走出的卫恒,他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投来诧异的目光。
这些人的穿着远不如之前遇到的那一队人精良,更像是某个偏远地区的山民。
但他们看他的眼神,却与那队人如出一辙——先是惊讶,然后是迅速的审视,最后化为一种毫不掩饰的淡漠与轻视。
一个看起来像是头领的中年男人走上前,他手里拿着一把沉重的砍刀,刀身上甚至还有未干的血迹。
他粗声粗气地说了几句话。
卫恒紧张地摇头,比划着自己,又指指来的方向,试图表达自己迷路了,需要帮助。
男人皱起眉,似乎有些不耐烦。
他朝旁边一个正在修补渔网的年轻人嘟囔了一句。
那年轻人点点头,放下手里的活,走到卫恒面前。
他并没有看卫恒的眼睛,而是像执行某种程序一样,伸出手,掌心朝下,在卫恒面前缓缓掠过。
年轻人的手掌泛起一层极其微弱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土黄色光晕,如同蒙尘的琥珀。
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几秒,然后收回手,对着中年男人肯定地摇了摇头,清晰地吐出两个音节:“Méng Nèng。”
中年男人脸上立刻浮现出“果然如此”的表情,那表情里混合着厌烦和一丝优越感。
他不再看卫恒,只是朝村落边缘一个堆放杂物的简陋窝棚指了指,又指了指溪流和堆着脏木桶的方向,做了个挑水的动作,然后不耐烦地挥挥手,示意卫恒过去。
尽管语言不通,但肢体语言和表情是共通的。
卫恒明白了,对方允许他留下,但代价是干活。
而那个年轻人刚才的举动和那句“Méng Nèng”,像一根冰冷的针,刺入他的脑海。
他隐约猜到,那是在检测什么,而结果显然是否定的。
接下来的日子,卫恒如同坠入一个冰冷而屈辱的梦境。
他成了这个村落最底层的杂役。
每天天不亮,他就要去溪边挑水,那沉重的水桶压得他瘦弱的肩膀红肿破皮;他需要清理村落中央石砌火塘里的灰烬,呛人的烟灰让他咳嗽不止;他需要帮着处理猎回来的、形状古怪的兽尸,血腥味和内脏的腥臭几乎让他呕吐。
而他得到的,仅仅是勉强果腹的食物——通常是别人吃剩的、硬邦邦的肉干碎末,或者一小碗寡淡的、不知用什么根茎熬成的糊糊。
他像一块人形的木头,沉默地干着一切。
但他所有的感官和心智都在疯狂地学习。
他强迫自己记住每一个动作对应的词汇,观察人们交谈时的神情和语气。
他听到那些孩子在追逐打闹时,指尖会迸发出细小的火星或水花,引来大人的呵斥,但那呵斥里带着纵容。
他听到人们谈论狩猎时,会提到谁谁用“地刺”困住了猎物,谁谁的“风刃”切开了最坚韧的皮毛。
他逐渐听懂了一些重复率极高的词。
“Néng Lì”(能力),这个词总是伴随着某种敬畏或羡慕的语气。
而“Méng”,那个年轻人对他做出的判定,出现的频率同样很高,却总是伴随着嗤笑、鄙夷、或者干脆是无视。
当有人笨手笨脚打翻东西,或者不敢去触碰某种看起来危险的活计时,旁人就会哄笑着喊出这个词。
“Méng”——无能者。
卫恒终于明白了这个词的含义,也明白了自己身上被贴上了怎样的标签。
这是一个以“异能”为基石,划分出清晰阶层的世界。
力量意味着一切:尊重、地位、食物、安全。
而没有力量,就像他这样,便不配被当做一个完整的人看待,只是可供驱使的牲口,是呼吸着的废物。
他蜷缩在西面漏风的窝棚里,听着外面夜晚的喧嚣——人们的交谈、火焰的噼啪、以及远处山林里妖魔的嚎叫。
孤独和屈辱像冰冷的潮水淹没了他。
他想家,想妈妈做的热饭菜,想学校里虽然平淡但安全的日常,甚至想那个夺走他一切的漩涡——至少在那之前,他的人生虽有烦恼,却从未被如此彻底地践踏过。
有时,在干最脏最累的活时,他会感到体内那股沉睡的力量似乎微微躁动。
尤其是在他情绪剧烈波动时——比如被一个壮汉故意将脏水泼到身上,并伴随着大声的嘲笑时,一股极细微的灼热和冰寒会同时从他心底掠过,但旋即消失,快得像是错觉。
他不敢声张,甚至不敢去仔细感受。
那队人冰冷的目光和眼前这些村民的鄙夷,都让他深刻地意识到,特殊,未必是好事。
尤其是在他根本无法控制这特殊的情况下。
暴露它,可能招致更大的灾祸。
他只能忍耐。
像一块石头一样忍耐。
他默默地干活,默默地学习语言,默默地观察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则。
他将所有的不甘、愤怒和恐惧死死压在心底,只在无人注意的角落,眼神里才会流露出属于地球少年卫恒的倔强与锋芒。
活下去。
必须先活下去。
只有活着,才能找到回去的路,或者…找到在这个冰冷世界站稳脚跟的方法。
“Méng”这个标签,他暂时撕不掉,但他绝不会让它永远钉死在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