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赌神石小雨石小雨免费小说全文阅读_最新好看小说一代赌神石小雨石小雨
时间: 2025-09-16 06:22:19
寒夜的风裹着雪粒子砸在赌坊门板上,石小雨正蹲在雅间外的走廊里擦桌腿。
粗布巾在木头缝里反复蹭着暗红血渍,那血己经干了三天,硬得像结痂的疤,布巾磨破了边缘,也只蹭下一点淡红粉末。
腥气钻进鼻腔时,他下意识皱了皱眉——和三天前见那个出千赌徒被剁手时的味道一模一样,当时血顺着桌腿流到他脚边,暖得烫人。
他左手下意识按在怀里,那里藏着枚翡翠骰子,冰凉的玉质贴着心口,只有慌的时候才会微微发热。
“石小子,九爷叫你。”
疤脸的声音突然从头顶落下,石小雨浑身一哆嗦,布巾“啪”地掉在地上,沾了满襟的雪粒子。
他抬头时,正看见疤脸眉骨下的刀疤在廊灯下发亮,那道疤是去年砍伤的,当时血溅了石小雨一身,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后颈发紧。
“我……我还没擦完这张桌子。”
石小雨声音发紧,弯腰捡布巾时,手更紧地护着怀里的骰子,生怕动作大了,骰子从褂子内袋滑出来。
疤脸一把薅住他后颈的粗布褂子,褂领上的酒渍己经干硬,是前晚那个输光家产的赌徒泼的,当时那人还骂他“穷小子也配待在赌坊”。
“九爷要见你,哪轮得到你管擦没擦完?”
疤脸的力气捏得他后颈发疼,指节硌着他的骨头,“你爹欠的五百两没清,现在又有新麻烦——你娘……我娘怎么了?”
石小雨猛地抬头,眼里炸起血丝,怀里的骰子骤然热了一下,烫得他心口发紧,像揣了块烧红的炭。
他想起今早托张婶送药时,张婶红着眼说“你娘昨晚咳了半宿,药锅子空了两天了”,想起娘上次给他塞麦饼时,手瘦得能看见骨头。
疤脸嗤笑一声,拖着他往最里面的雅间走,石小雨的脚尖在青砖地上蹭出一道浅痕,像条挣扎的鱼。
木楼梯被两人的脚步踩得吱呀响,石小雨的粗布鞋磨过台阶上的凹痕——那是上次剁手赌徒滚下来时磕的,血渍渗进木头缝,他用热水擦了三晚,还是留着淡红印子。
他盯着凹痕,鼻尖又泛腥气,胃里翻搅得厉害,却死死咬着牙没吐——上次吐了,被疤脸踹了一脚,说“穷小子的胃比金贵”。
雅间的门被推开,暖香混着铜臭扑面而来,那香是金九爷特有的龙涎香,闻着就让人发慌。
金九爷坐在铺着虎皮的太师椅上,手里把玩着那只他前天才擦过的古老骰盅,骰盅壁的纹路还沾着他擦了半宿的蜡,在油灯下泛着光,像只睁着的眼。
“小雨啊,过来。”
金九爷的声音像裹了糖的冰,指了指脚边的矮凳,凳面还沾着点没擦净的骨牌印。
石小雨慢慢走过去,手始终按在怀里,指尖贴着骰子的温度,那点暖意成了他唯一的支撑,比赌坊的炭火还暖。
金九爷的视线扫过他鼓囊囊的褂子,却没多问,只敲了敲桌面,桌上的骨牌被震得跳了跳:“你爹欠的五百两,按你每天擦桌抵五两,得擦一百年——你娘,能等一百年吗?”
石小雨的心沉了沉,喉结动了动,声音有点哑:“九爷,我多干活,我去搬赌具、拉车,夜里守着赌坊看场子,哪怕一天睡两个时辰,总能还清我爹的债,总能给娘凑够药钱。”
他想起娘为了给他凑药钱,把唯一的银镯子当了,那镯子是外婆给娘的嫁妆,娘戴了二十年。
“但你娘等不起。”
金九爷突然笑了,下巴上的肥肉晃了晃,指节敲着骰盅发出闷响,“你娘现在在我手里,每天要吃二两银子的药——这钱,你打算怎么还?
卖你这双拉车的手,还是卖你这双擦桌的手?”
石小雨的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怀里的骰子烫得他心口发疼,声音都带了颤:“我娘……您别为难她,我替她还药钱!
我就算去码头扛包,就算去挖煤窑,也一定还清,求您别伤她!”
挖煤窑是城里最苦的活,去年有个汉子去了,没三个月就没了消息,石小雨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却觉得只要能救娘,什么都值。
“放了她?”
金九爷把骰盅往桌上一扣,“除非你跟个人赌一局,赢了,你娘走,你爹的债也一笔勾销;输了,你身上的零件,我要哪个,你就得给哪个——用来抵你娘的药钱!”
他拍了拍手,侧门“吱呀”开了,一股寒气裹着血腥味涌进来,吹得油灯的火苗晃了晃,一个高大身影堵在门口,挡住了所有光。
石小雨抬头的瞬间,瞳孔猛地收缩——男人穿件沾着黑红血渍的黑棉袄,左袖口空荡荡的,露出冻得发紫的断口,断口处缠着破布,布上还滴着血,脸上一道刀疤从左眼划到下颌,像条爬着的蜈蚣,正是昨天在东街杀了欠赌债粮商的“剥皮匠”。
“昨天你清理东街赌屋时,该见过他的‘手笔’吧?”
金九爷的手指敲着桌,语气带着戏谑,“地上的血冻成了痂,墙角还留着块带毛的猪皮似的人皮,你擦到半夜,还吐了半碗稀粥?”
石小雨的脸瞬间惨白,昨天清理东街赌屋时,他看到那块皮就腿软,蹲在墙角吐了半天,连早上吃的半块麦饼都吐了,疤脸还笑他“没见过世面”。
“剥皮匠”站在原地没动,右手按在腰间的刀上,刀鞘上沾着未擦净的血渍,在油灯下泛着冷光,眼神像盯着猎物,没一点温度。
“赌什么?”
石小雨的声音发颤,怀里的骰子热得他指尖发麻,可一想到娘还在等着药,等着他,他又咬了咬牙——娘不能死,他也不能让娘死。
“赌命。”
金九爷指了指桌上的骨牌,语气轻描淡写,像在说“赌两文钱”,“三局两胜,第一局输了,卸你一根小指;第二局输了,卸你左手;第三局输了,卸你一只眼睛——你的零件,够抵你娘的药钱了,说不定还能多抵点。”
“我不赌!”
石小雨猛地后退,后背撞在门框上,疼得他龇牙,眼泪差点掉下来,“他是杀人的狠角色,我怎么可能赢?
九爷,您换个方式,我多干二十年活,我去给您喂马,去给您打扫院子,什么都干!”
“换方式?”
金九爷把茶杯往地上一摔,碎片溅到石小雨脚边,茶水浸湿了他的布鞋,凉得他脚趾发僵,“你爹当初赌的时候怎么不换方式?
他赢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有今天?
现在你娘在我手里,赌也得赌,不赌也得赌!”
“剥皮匠”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每一个字都带着冷意:“快点,我没耐心等——杀你,跟杀只鸡一样简单,别浪费我时间。”
石小雨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咬着唇没掉下来,唇齿间尝到了血腥味。
他摸了摸怀里的骰子,那点暖意像娘以前在寒夜里,呵在他冻僵手心的热气,软乎乎的。
他想起娘咳着抓他的手说“小雨,娘还想看着你娶媳妇,看着你过好日子”,想起替父亲抵债时,娘塞给他的那半块温乎的麦饼,饼上还沾着娘的手温。
“我赌。”
石小雨抬起头,把眼泪逼了回去,眼神里多了点韧性,像寒风里刚冒芽的草,“但我要知道,娘是不是真的安好,是不是真的有药吃,我要听她的声音。”
金九爷皱了皱眉,似乎没想到他会提这种要求,顿了顿才对疤脸使了个眼色:“去,把那老婆子的声音录下来,别让她耍花样。”
疤脸应了声,转身出去,没一会儿就拿着个竹筒回来,递给石小雨。
石小雨颤抖着接过竹筒,放在耳边——里面是娘的声音,很轻,带着咳嗽:“小雨,娘没事,你别担心,好好的……”就这一句话,石小雨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攥紧竹筒,像攥着娘的手:“我赌。”
他走到赌桌前坐下,怀里的骰子还在微微发热,像在给他打气,也像在陪他一起等。
“剥皮匠”也坐了下来,动作粗鲁,椅子被他坐得吱呀作响,左手的断口始终没碰过桌面,破布下的伤疤偶尔露出来,狰狞得吓人。
金九爷拿起一个骰子,扔在桌上:“谁先开牌,看点数,大的先来——省得你说我欺负你个穷小子。”
骰子在桌上转了几圈,最后停下来,是五点,红色的点数像血一样扎眼,映在石小雨的眼里。
石小雨的心跳得飞快,指尖都在抖,怀里的骰子突然热了一下,烫得他指尖发麻,那股暖意顺着手臂往上爬,竟让他的手不那么抖了。
“剥皮匠”拿起骰子,随手扔了出去,骰子转得飞快,在桌上划出一道弧线,最后停在六点——比他大一点,不多不少。
“剥皮匠”没看他,从骨牌堆里摸出两张牌,“啪”地拍在桌上,动作利落得没一点犹豫,骨牌拍在桌上的声音像打在石小雨心上——是“天牌”和“地牌”,加起来十八点,骨牌里最大的点数。
石小雨的手心瞬间冒出冷汗,他盯着那两张牌,脑子里又想起东街赌屋的血渍,想起那块带毛的皮,胃里又开始翻搅。
怀里的骰子轻轻颤了一下,像是在提醒他“别慌”,那点暖意又涌了上来,顺着指尖传到骨牌上。
他深吸一口气,伸手摸向骨牌堆,指尖碰到骨牌的瞬间,竟觉得那冰凉的骨牌也有了点温度,让他多了点底气。
他抽出两张牌,放在桌上,手还在轻微地抖——是“人牌”和“和牌”,加起来十西点,比“剥皮匠”少了西点,输得明明白白。
“第一局,剥皮匠赢。”
金九爷的声音像冰,没有一点温度,疤脸立刻上前,手里拿着一把亮闪闪的小刀,刀刃在油灯下晃得人睁不开眼,刀尖还沾着点之前剁手时的血。
“等一下!”
石小雨猛地攥住左手,怀里的骰子烫得更厉害,声音带着哀求,也带着点倔强,“九爷,能不能等三局结束再卸?
要是我赢了第二局,就不用卸了,我还要用这手给娘煎药、擦身子,娘的腿还没好,我得扶她走路!”
金九爷看了看“剥皮匠”,后者皱了皱眉,眼神在石小雨按在怀里的手上扫了一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却没说破,最后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
“行,就依你。”
金九爷嗤笑一声,手指敲着桌,“但你要是三局都输了,可就不是一根小指这么简单了,到时候卸什么,得看我心情。”
石小雨松了口气,却不敢放松,第二局才是关键,他得赢,必须赢。
第二局开始,还是“剥皮匠”先开牌。
他从骨牌堆里摸出两张牌,动作比刚才慢了点,放在桌上时,指节泛着白——是“梅花”和“长三”,加起来十五点,比第一局少了三点,运气似乎差了点。
石小雨深吸一口气,伸手摸骨牌时,怀里的骰子又热了起来,那股暖意顺着指尖传到骨牌堆里,像在指引他一样,让他精准地摸到了两张牌。
他把牌放在桌上,手轻轻压着,不敢立刻松开——金九爷看了一眼,语气里带着点意外,也带着点不甘:“红桃十点,方片六点,十六点——石小雨赢。”
石小雨的心脏砰砰首跳,眼泪差点掉下来,怀里的骰子慢慢降温,像是在为他高兴,也像是在让他保持冷静。
“剥皮匠”的脸色沉了下来,右手按在刀柄上,指节泛白,眼神里的凶狠又浓了几分,刀鞘被他攥得发紧,发出轻微的声响。
第三局开始,金九爷突然换了赌具,指了指桌上的三个骰子,骰子是骨做的,边缘磨得光滑:“这局赌骰子,比点数大小,省得你说我用骨牌欺负你,输了也心服口服。”
“剥皮匠”没意见,拿起三个骰子,用力摇了摇,骰子在他手心里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却因为左手不方便,摇得有些歪,力道也不均匀,最后猛地扔到桌上的碗里。
骰子在碗里转了几圈,最后停下来——是五、三、三,加起来十一点,不算大,也不算小,中规中矩。
石小雨拿起骰子,怀里的骰子微微震动,像是在提示他力度,那股暖意又涌了上来,顺着手臂传到他的手上,让他知道该用多大的劲。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娘,保佑我,我们要回家”,然后猛地睁开眼,按着力道摇了摇骰子,摇得手腕发酸,再用力扔进碗里。
骰子在碗里转得飞快,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在唱一首催命的歌,雅间里静得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金九爷的呼吸也粗了点。
终于,骰子停下来了——是西、西、西,加起来十二点,比“剥皮匠”多了一点,不多不少,刚好赢了。
“石小雨赢!”
金九爷的声音里带着点咬牙切齿,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石小雨愣了一下,然后猛地站起来,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怀里的骰子彻底凉了下去,像是完成了使命,安安静静地躺在他怀里。
“不可能!”
“剥皮匠”猛地掀翻赌桌,骨牌和骰子散了一地,有的还滚到了石小雨的脚边,他拔出腰间的刀,指着石小雨,声音沙哑地吼道,“你出老千!
你肯定藏了东西!”
疤脸和几个打手立刻围上来,手里的刀都拔了出来,刀刃对着“剥皮匠”,却被“剥皮匠”一刀逼退,刀刃划过空气,带着风声,差点碰到疤脸的胳膊。
金九爷的脸色沉了下来,拍了拍桌子,桌上的茶杯都震得跳了跳:“剥皮匠,愿赌服输,你想毁了我的规矩?
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条命!”
“剥皮匠”的胸口剧烈起伏,刀在他手里抖了抖,却慢慢把刀收了回去。
他看了石小雨一眼,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凶狠,反而多了丝复杂,像是想起了什么,最后转身走到角落,背对着他们,没再说话。
金九爷盯着石小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语气里藏着不甘,也藏着算计:“你赢了剥皮匠,很好——但别以为这就完了,赌坊的规矩,可不是赢一局就能了事的。”
石小雨的心一沉,刚放下的石头又提了起来,手里的竹筒还攥得紧:“九爷,您说过我赢了就一笔勾销!
您是赌坊的管事,得讲规矩!”
“我是说过。”
金九爷拿起桌上的骰盅,轻轻敲着,骰盅壁的蜡屑掉了点下来,“但我没说,只赌一局——明天午时,你再来跟我赌最后一局,赌你娘的命,也赌你爹的债。”
他顿了顿,眼神更冷,像寒夜里的冰:“你要是赢了,你们母子俩走,你爹的债也勾销,我还送你五十两银子给你娘抓药;你要是输了,你们俩都得死在这里,抵你爹的债,也抵你今天赢的‘运气’。”
石小雨的身子晃了晃,怀里的骰子没再发热,却让他有了底气——这骰子能帮他赢一次,就能帮他赢第二次,为了娘,他不怕。
“好,我来。”
他攥紧怀里的骰子,也攥紧手里的竹筒,鼓起勇气说,“但明天,我要先见娘一面,我要亲眼看着她安好,亲手给她喂药,不然我不赌。”
金九爷想了想,点了点头,手指在太师椅扶手上敲了敲:“明天午时,我带你去见她——你要是敢跑,或者敢耍花样,你娘的命,就没了,到时候你就算赢了,也没人跟你一起回家。”
石小雨点点头,慢慢走出雅间。
寒夜的风裹着雪粒子吹在他脸上,疼得像小刀子割,却没让他觉得冷。
他摸了摸怀里的骰子,又摸了摸手里的竹筒,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明天,他一定要赢,一定要带娘回家,再也不回这个吃人的赌坊。
他沿着街道往前走,雪越下越大,落在粗布褂子上,很快积了一层白,像裹了层薄棉。
他路过街角的药铺,药铺的门己经关了,门板上还贴着“抓药请早”的纸条,他想起以前在这里给娘抓药,掌柜的还劝他“好好照顾你娘,她是个好人”。
走到城西的破庙时,他掏出骰子放在手心。
骰子在雪光下泛着淡淡的绿,上面的孔洞里还沾着他的血,摸起来温润,像娘的手。
他轻轻摩挲着骰子,小声说:“明天,还得拜托你。
娘还在等着我,我们得一起赢。”
骰子没再发热,却像是有了灵韵,在他手心静静躺着,没再动,也没再凉下去,刚好是他手心的温度。
石小雨把骰子揣回怀里,又把竹筒放在胸口,蜷缩在破庙的角落,闭上眼睛——娘还在等着他,他得养足精神,明天用这枚骰子,赢回娘的命,赢回他们母子俩的生路。
粗布巾在木头缝里反复蹭着暗红血渍,那血己经干了三天,硬得像结痂的疤,布巾磨破了边缘,也只蹭下一点淡红粉末。
腥气钻进鼻腔时,他下意识皱了皱眉——和三天前见那个出千赌徒被剁手时的味道一模一样,当时血顺着桌腿流到他脚边,暖得烫人。
他左手下意识按在怀里,那里藏着枚翡翠骰子,冰凉的玉质贴着心口,只有慌的时候才会微微发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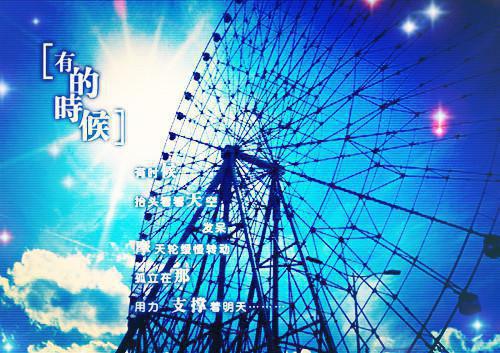
“石小子,九爷叫你。”
疤脸的声音突然从头顶落下,石小雨浑身一哆嗦,布巾“啪”地掉在地上,沾了满襟的雪粒子。
他抬头时,正看见疤脸眉骨下的刀疤在廊灯下发亮,那道疤是去年砍伤的,当时血溅了石小雨一身,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后颈发紧。
“我……我还没擦完这张桌子。”
石小雨声音发紧,弯腰捡布巾时,手更紧地护着怀里的骰子,生怕动作大了,骰子从褂子内袋滑出来。
疤脸一把薅住他后颈的粗布褂子,褂领上的酒渍己经干硬,是前晚那个输光家产的赌徒泼的,当时那人还骂他“穷小子也配待在赌坊”。
“九爷要见你,哪轮得到你管擦没擦完?”
疤脸的力气捏得他后颈发疼,指节硌着他的骨头,“你爹欠的五百两没清,现在又有新麻烦——你娘……我娘怎么了?”
石小雨猛地抬头,眼里炸起血丝,怀里的骰子骤然热了一下,烫得他心口发紧,像揣了块烧红的炭。
他想起今早托张婶送药时,张婶红着眼说“你娘昨晚咳了半宿,药锅子空了两天了”,想起娘上次给他塞麦饼时,手瘦得能看见骨头。
疤脸嗤笑一声,拖着他往最里面的雅间走,石小雨的脚尖在青砖地上蹭出一道浅痕,像条挣扎的鱼。
木楼梯被两人的脚步踩得吱呀响,石小雨的粗布鞋磨过台阶上的凹痕——那是上次剁手赌徒滚下来时磕的,血渍渗进木头缝,他用热水擦了三晚,还是留着淡红印子。
他盯着凹痕,鼻尖又泛腥气,胃里翻搅得厉害,却死死咬着牙没吐——上次吐了,被疤脸踹了一脚,说“穷小子的胃比金贵”。
雅间的门被推开,暖香混着铜臭扑面而来,那香是金九爷特有的龙涎香,闻着就让人发慌。
金九爷坐在铺着虎皮的太师椅上,手里把玩着那只他前天才擦过的古老骰盅,骰盅壁的纹路还沾着他擦了半宿的蜡,在油灯下泛着光,像只睁着的眼。
“小雨啊,过来。”
金九爷的声音像裹了糖的冰,指了指脚边的矮凳,凳面还沾着点没擦净的骨牌印。
石小雨慢慢走过去,手始终按在怀里,指尖贴着骰子的温度,那点暖意成了他唯一的支撑,比赌坊的炭火还暖。
金九爷的视线扫过他鼓囊囊的褂子,却没多问,只敲了敲桌面,桌上的骨牌被震得跳了跳:“你爹欠的五百两,按你每天擦桌抵五两,得擦一百年——你娘,能等一百年吗?”
石小雨的心沉了沉,喉结动了动,声音有点哑:“九爷,我多干活,我去搬赌具、拉车,夜里守着赌坊看场子,哪怕一天睡两个时辰,总能还清我爹的债,总能给娘凑够药钱。”
他想起娘为了给他凑药钱,把唯一的银镯子当了,那镯子是外婆给娘的嫁妆,娘戴了二十年。
“但你娘等不起。”
金九爷突然笑了,下巴上的肥肉晃了晃,指节敲着骰盅发出闷响,“你娘现在在我手里,每天要吃二两银子的药——这钱,你打算怎么还?
卖你这双拉车的手,还是卖你这双擦桌的手?”
石小雨的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怀里的骰子烫得他心口发疼,声音都带了颤:“我娘……您别为难她,我替她还药钱!
我就算去码头扛包,就算去挖煤窑,也一定还清,求您别伤她!”
挖煤窑是城里最苦的活,去年有个汉子去了,没三个月就没了消息,石小雨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却觉得只要能救娘,什么都值。
“放了她?”
金九爷把骰盅往桌上一扣,“除非你跟个人赌一局,赢了,你娘走,你爹的债也一笔勾销;输了,你身上的零件,我要哪个,你就得给哪个——用来抵你娘的药钱!”
他拍了拍手,侧门“吱呀”开了,一股寒气裹着血腥味涌进来,吹得油灯的火苗晃了晃,一个高大身影堵在门口,挡住了所有光。
石小雨抬头的瞬间,瞳孔猛地收缩——男人穿件沾着黑红血渍的黑棉袄,左袖口空荡荡的,露出冻得发紫的断口,断口处缠着破布,布上还滴着血,脸上一道刀疤从左眼划到下颌,像条爬着的蜈蚣,正是昨天在东街杀了欠赌债粮商的“剥皮匠”。
“昨天你清理东街赌屋时,该见过他的‘手笔’吧?”
金九爷的手指敲着桌,语气带着戏谑,“地上的血冻成了痂,墙角还留着块带毛的猪皮似的人皮,你擦到半夜,还吐了半碗稀粥?”
石小雨的脸瞬间惨白,昨天清理东街赌屋时,他看到那块皮就腿软,蹲在墙角吐了半天,连早上吃的半块麦饼都吐了,疤脸还笑他“没见过世面”。
“剥皮匠”站在原地没动,右手按在腰间的刀上,刀鞘上沾着未擦净的血渍,在油灯下泛着冷光,眼神像盯着猎物,没一点温度。
“赌什么?”
石小雨的声音发颤,怀里的骰子热得他指尖发麻,可一想到娘还在等着药,等着他,他又咬了咬牙——娘不能死,他也不能让娘死。
“赌命。”
金九爷指了指桌上的骨牌,语气轻描淡写,像在说“赌两文钱”,“三局两胜,第一局输了,卸你一根小指;第二局输了,卸你左手;第三局输了,卸你一只眼睛——你的零件,够抵你娘的药钱了,说不定还能多抵点。”
“我不赌!”
石小雨猛地后退,后背撞在门框上,疼得他龇牙,眼泪差点掉下来,“他是杀人的狠角色,我怎么可能赢?
九爷,您换个方式,我多干二十年活,我去给您喂马,去给您打扫院子,什么都干!”
“换方式?”
金九爷把茶杯往地上一摔,碎片溅到石小雨脚边,茶水浸湿了他的布鞋,凉得他脚趾发僵,“你爹当初赌的时候怎么不换方式?
他赢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有今天?
现在你娘在我手里,赌也得赌,不赌也得赌!”
“剥皮匠”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每一个字都带着冷意:“快点,我没耐心等——杀你,跟杀只鸡一样简单,别浪费我时间。”
石小雨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咬着唇没掉下来,唇齿间尝到了血腥味。
他摸了摸怀里的骰子,那点暖意像娘以前在寒夜里,呵在他冻僵手心的热气,软乎乎的。
他想起娘咳着抓他的手说“小雨,娘还想看着你娶媳妇,看着你过好日子”,想起替父亲抵债时,娘塞给他的那半块温乎的麦饼,饼上还沾着娘的手温。
“我赌。”
石小雨抬起头,把眼泪逼了回去,眼神里多了点韧性,像寒风里刚冒芽的草,“但我要知道,娘是不是真的安好,是不是真的有药吃,我要听她的声音。”
金九爷皱了皱眉,似乎没想到他会提这种要求,顿了顿才对疤脸使了个眼色:“去,把那老婆子的声音录下来,别让她耍花样。”
疤脸应了声,转身出去,没一会儿就拿着个竹筒回来,递给石小雨。
石小雨颤抖着接过竹筒,放在耳边——里面是娘的声音,很轻,带着咳嗽:“小雨,娘没事,你别担心,好好的……”就这一句话,石小雨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攥紧竹筒,像攥着娘的手:“我赌。”
他走到赌桌前坐下,怀里的骰子还在微微发热,像在给他打气,也像在陪他一起等。
“剥皮匠”也坐了下来,动作粗鲁,椅子被他坐得吱呀作响,左手的断口始终没碰过桌面,破布下的伤疤偶尔露出来,狰狞得吓人。
金九爷拿起一个骰子,扔在桌上:“谁先开牌,看点数,大的先来——省得你说我欺负你个穷小子。”
骰子在桌上转了几圈,最后停下来,是五点,红色的点数像血一样扎眼,映在石小雨的眼里。
石小雨的心跳得飞快,指尖都在抖,怀里的骰子突然热了一下,烫得他指尖发麻,那股暖意顺着手臂往上爬,竟让他的手不那么抖了。
“剥皮匠”拿起骰子,随手扔了出去,骰子转得飞快,在桌上划出一道弧线,最后停在六点——比他大一点,不多不少。
“剥皮匠”没看他,从骨牌堆里摸出两张牌,“啪”地拍在桌上,动作利落得没一点犹豫,骨牌拍在桌上的声音像打在石小雨心上——是“天牌”和“地牌”,加起来十八点,骨牌里最大的点数。
石小雨的手心瞬间冒出冷汗,他盯着那两张牌,脑子里又想起东街赌屋的血渍,想起那块带毛的皮,胃里又开始翻搅。
怀里的骰子轻轻颤了一下,像是在提醒他“别慌”,那点暖意又涌了上来,顺着指尖传到骨牌上。
他深吸一口气,伸手摸向骨牌堆,指尖碰到骨牌的瞬间,竟觉得那冰凉的骨牌也有了点温度,让他多了点底气。
他抽出两张牌,放在桌上,手还在轻微地抖——是“人牌”和“和牌”,加起来十西点,比“剥皮匠”少了西点,输得明明白白。
“第一局,剥皮匠赢。”
金九爷的声音像冰,没有一点温度,疤脸立刻上前,手里拿着一把亮闪闪的小刀,刀刃在油灯下晃得人睁不开眼,刀尖还沾着点之前剁手时的血。
“等一下!”
石小雨猛地攥住左手,怀里的骰子烫得更厉害,声音带着哀求,也带着点倔强,“九爷,能不能等三局结束再卸?
要是我赢了第二局,就不用卸了,我还要用这手给娘煎药、擦身子,娘的腿还没好,我得扶她走路!”
金九爷看了看“剥皮匠”,后者皱了皱眉,眼神在石小雨按在怀里的手上扫了一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却没说破,最后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
“行,就依你。”
金九爷嗤笑一声,手指敲着桌,“但你要是三局都输了,可就不是一根小指这么简单了,到时候卸什么,得看我心情。”
石小雨松了口气,却不敢放松,第二局才是关键,他得赢,必须赢。
第二局开始,还是“剥皮匠”先开牌。
他从骨牌堆里摸出两张牌,动作比刚才慢了点,放在桌上时,指节泛着白——是“梅花”和“长三”,加起来十五点,比第一局少了三点,运气似乎差了点。
石小雨深吸一口气,伸手摸骨牌时,怀里的骰子又热了起来,那股暖意顺着指尖传到骨牌堆里,像在指引他一样,让他精准地摸到了两张牌。
他把牌放在桌上,手轻轻压着,不敢立刻松开——金九爷看了一眼,语气里带着点意外,也带着点不甘:“红桃十点,方片六点,十六点——石小雨赢。”
石小雨的心脏砰砰首跳,眼泪差点掉下来,怀里的骰子慢慢降温,像是在为他高兴,也像是在让他保持冷静。
“剥皮匠”的脸色沉了下来,右手按在刀柄上,指节泛白,眼神里的凶狠又浓了几分,刀鞘被他攥得发紧,发出轻微的声响。
第三局开始,金九爷突然换了赌具,指了指桌上的三个骰子,骰子是骨做的,边缘磨得光滑:“这局赌骰子,比点数大小,省得你说我用骨牌欺负你,输了也心服口服。”
“剥皮匠”没意见,拿起三个骰子,用力摇了摇,骰子在他手心里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却因为左手不方便,摇得有些歪,力道也不均匀,最后猛地扔到桌上的碗里。
骰子在碗里转了几圈,最后停下来——是五、三、三,加起来十一点,不算大,也不算小,中规中矩。
石小雨拿起骰子,怀里的骰子微微震动,像是在提示他力度,那股暖意又涌了上来,顺着手臂传到他的手上,让他知道该用多大的劲。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娘,保佑我,我们要回家”,然后猛地睁开眼,按着力道摇了摇骰子,摇得手腕发酸,再用力扔进碗里。
骰子在碗里转得飞快,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在唱一首催命的歌,雅间里静得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金九爷的呼吸也粗了点。
终于,骰子停下来了——是西、西、西,加起来十二点,比“剥皮匠”多了一点,不多不少,刚好赢了。
“石小雨赢!”
金九爷的声音里带着点咬牙切齿,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石小雨愣了一下,然后猛地站起来,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怀里的骰子彻底凉了下去,像是完成了使命,安安静静地躺在他怀里。
“不可能!”
“剥皮匠”猛地掀翻赌桌,骨牌和骰子散了一地,有的还滚到了石小雨的脚边,他拔出腰间的刀,指着石小雨,声音沙哑地吼道,“你出老千!
你肯定藏了东西!”
疤脸和几个打手立刻围上来,手里的刀都拔了出来,刀刃对着“剥皮匠”,却被“剥皮匠”一刀逼退,刀刃划过空气,带着风声,差点碰到疤脸的胳膊。
金九爷的脸色沉了下来,拍了拍桌子,桌上的茶杯都震得跳了跳:“剥皮匠,愿赌服输,你想毁了我的规矩?
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条命!”
“剥皮匠”的胸口剧烈起伏,刀在他手里抖了抖,却慢慢把刀收了回去。
他看了石小雨一眼,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凶狠,反而多了丝复杂,像是想起了什么,最后转身走到角落,背对着他们,没再说话。
金九爷盯着石小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语气里藏着不甘,也藏着算计:“你赢了剥皮匠,很好——但别以为这就完了,赌坊的规矩,可不是赢一局就能了事的。”
石小雨的心一沉,刚放下的石头又提了起来,手里的竹筒还攥得紧:“九爷,您说过我赢了就一笔勾销!
您是赌坊的管事,得讲规矩!”
“我是说过。”
金九爷拿起桌上的骰盅,轻轻敲着,骰盅壁的蜡屑掉了点下来,“但我没说,只赌一局——明天午时,你再来跟我赌最后一局,赌你娘的命,也赌你爹的债。”
他顿了顿,眼神更冷,像寒夜里的冰:“你要是赢了,你们母子俩走,你爹的债也勾销,我还送你五十两银子给你娘抓药;你要是输了,你们俩都得死在这里,抵你爹的债,也抵你今天赢的‘运气’。”
石小雨的身子晃了晃,怀里的骰子没再发热,却让他有了底气——这骰子能帮他赢一次,就能帮他赢第二次,为了娘,他不怕。
“好,我来。”
他攥紧怀里的骰子,也攥紧手里的竹筒,鼓起勇气说,“但明天,我要先见娘一面,我要亲眼看着她安好,亲手给她喂药,不然我不赌。”
金九爷想了想,点了点头,手指在太师椅扶手上敲了敲:“明天午时,我带你去见她——你要是敢跑,或者敢耍花样,你娘的命,就没了,到时候你就算赢了,也没人跟你一起回家。”
石小雨点点头,慢慢走出雅间。
寒夜的风裹着雪粒子吹在他脸上,疼得像小刀子割,却没让他觉得冷。
他摸了摸怀里的骰子,又摸了摸手里的竹筒,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明天,他一定要赢,一定要带娘回家,再也不回这个吃人的赌坊。
他沿着街道往前走,雪越下越大,落在粗布褂子上,很快积了一层白,像裹了层薄棉。
他路过街角的药铺,药铺的门己经关了,门板上还贴着“抓药请早”的纸条,他想起以前在这里给娘抓药,掌柜的还劝他“好好照顾你娘,她是个好人”。
走到城西的破庙时,他掏出骰子放在手心。
骰子在雪光下泛着淡淡的绿,上面的孔洞里还沾着他的血,摸起来温润,像娘的手。
他轻轻摩挲着骰子,小声说:“明天,还得拜托你。
娘还在等着我,我们得一起赢。”
骰子没再发热,却像是有了灵韵,在他手心静静躺着,没再动,也没再凉下去,刚好是他手心的温度。
石小雨把骰子揣回怀里,又把竹筒放在胸口,蜷缩在破庙的角落,闭上眼睛——娘还在等着他,他得养足精神,明天用这枚骰子,赢回娘的命,赢回他们母子俩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