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刷弹幕朕的快递呢?(赵高嬴政)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秦始皇刷弹幕朕的快递呢?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赵高嬴政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秦始皇刷弹幕朕的快递呢?)
秦弹幕:咸阳三月天咸阳的三月总裹着一层湿软的风,从渭水上游漫下来,把两岸的柳丝染得发绿,堆在枝头像没散的烟。阿房宫前的驰道是去年刚夯的,黄土掺了糯米汁,硬得能映出人影,此刻却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砸得发颤——一匹黑马破尘而来,马鬃上还沾着陇西的沙,四蹄翻飞间溅起的泥点,落在道旁新栽的柏树上,晕开小小的褐痕。
骑手是个二十出头的郎卫,玄色短打被汗水浸得半透,贴在铜色的胸膛上,汗珠顺着锁骨往下淌,在腰腹的旧疤处聚成细流,又滴进绑腿里。他背后斜插着三支黑羽箭,箭尾的雕翎还在颤,腰间悬着的虎符泛着冷光,是陇西郡守亲授的调兵信物。
离宫门还有十丈远,他猛地勒住缰绳,黑马人立而起,长嘶声刺破晨雾,惊得檐角铜雀扑棱棱飞起,翅膀扫过瓦当,落下几片青灰。
郎卫翻身下马的动作快得像离弦的箭,单膝砸在驰道上,发出沉闷的响,膝盖处的皮甲瞬间磨出白痕。他双手高高举起一只漆封木匣,匣身刻着三道朱痕——这是陇西郡加急送来的八百里驿报,每道痕都代表着沿途换马时驿卒盖的火漆,三道,便是跑死了三匹马。
宫门处的铜钉森然排列,每个钉头都铸着饕餮纹,在晨光里泛着冷光。两名执剑卫士上前,按剑的手青筋暴起,先验了虎符,又用银刀挑开木匣上的漆封,取出里面的木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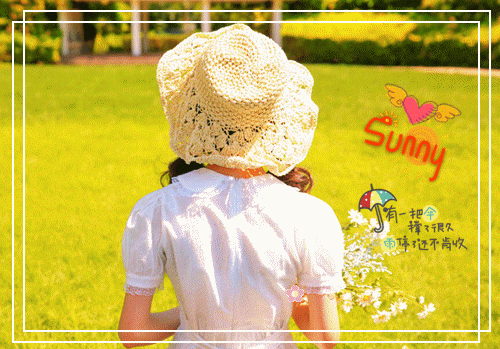
为首的卫士从怀中摸出朱笔,在牍尾的急字上勾了一道,朱砂透过木纤维渗进去,像在时光里划开一道细缝。就在这一瞬,咸阳城上空突然亮了——不是日出的光,是一行半透明的金篆,凭空悬在阿房宫的飞檐之上。那字有斗大,笔画如赤金熔铸,还带着融融的暖意,在日光里微微抖动:系统提示:秦始皇上线,全体弹幕礼仪准备。
金篆刚出现时,没人敢动。执剑卫士的手停在剑柄上,郎卫还保持着单膝跪地的姿势,连檐角的铜雀都忘了飞,停在半空转着脑袋。直到金篆的光映亮了宫门的饕餮纹,不知是谁先啊了一声,紧接着,宫门前的人全跪了下去,额头抵着硬邦邦的驰道,不敢抬头——那是天兆,是神明的字迹。阿房宫的高台在宫城最北端,站在上面能看见整个咸阳城。嬴政今日没穿冕旒,那套缀着十二串玉珠的礼冠太沉,压得他太阳穴发疼,此刻只穿了一袭玄绡便袍,衣摆垂在台阶上,被风掀起细小的弧度。
他面前没有群臣,也没有堆积如山的竹简,唯有一卷幽蓝光幕悬浮在半空,像从未来偷渡来的水镜,边缘还泛着细碎的光纹。光幕里正映着宫门前的景象,郎卫手中的木匣被卫士解开,露出里面一方帛书,帛色发暗,上面的字是用血写的,笔画狰狞——匈奴南下了,昨日破了陇西的两座烽燧,杀了守卒三百。嬴政的眉心猛地一跳,指节无意识地在虚空敲了敲,发出哒哒的轻响,像有人在暗处叩击陌生的器物。下一息,一条朱红色的弹幕突然从他指尖跃出,拖着长长的尾焰,在光幕上炸开:朕的快递呢?
陇西距咸阳八百里,三日未达,驿丞当烹!那行字刚出现,便在半空散成万点火星,落在宫人甲胄上,烫出一个个细小的焦孔。甲胄的铁皮被烫得滋啦响,宫人吓得扑通
跪倒,黑压压一片,齐呼陛下息怒,声音震得台阶上的青苔都在颤。可嬴政没理他们,因为更多的弹幕像瀑布一样,从光幕更高处轰然冲下来,颜色各异,密密麻麻叠在一起,像一场倒悬的流星雨。云中郡守:陛下,马已跑死三匹,驿卒昼夜无眠,昨日陇西至咸阳的驰道塌了半里,臣已命人抢修,还请陛下宽限!
穿越者 9527:笑死,秦朝没柏油路,没快递车,马再快也跑不过物流差评啊,始皇大大消消气,要不试试建个驿站中转站?徐福:陛下别急,臣在蓬莱岛托仙人代购了瞬移符,今日下单明日就能到咸阳,包邮!下次再有急报,臣用符送,保准比八百里驿报快!蒙恬:臣已派铁鹰锐士沿驰道沿途接力,若再延误,臣愿自请斩首,以谢陛下!荀子今天也很方:臣以为,当修一条高速驰道,从咸阳通到陇西,再通到云中,宽三丈,用夯土加青石,车马日行千里,日后传檄天下,皆可一日达!韩非小号:楼上儒生闭嘴!法家反对一切未经陛下准许的建议,修驰道要征徭役,要耗粮草,不如加税,让百姓多交粮,养更多驿卒!李斯:陛下,韩非此言不妥,加税恐引民怨,修驰道虽耗力,却是长久之计,还请陛下三思!嬴政眯起眼,目光扫过那些弹幕,忽然发现愤怒这种情绪,竟然能被看得见。
光幕左侧跳出一个赤色的柱状图,标着怒意值,此刻已经飙到了七格,红色的柱子几乎要顶到光幕的边缘——他记得上次怒意值满格时,是嫪毐叛乱,他斩了嫪毐三族,连带着咸阳城的三百个门客都被枭首。一群废物。嬴政冷哼一声,指尖在怒意值的柱子上轻轻一点。奇迹发生了,那根赤色的柱子瞬间清零,光幕上还飘过一行鎏金小字:始皇帝使用技能朕恕尔等,全体臣民怒气值-100。
跪着的宫人松了口气,刚要起身,却听见咸阳城的方向传来一阵喧哗。嬴政探头往下看,只见城里的百姓一个个都仰着头,脸上又是惊又是怕,有的人还伸手去抓头顶的空气——原来咸阳城的百姓头顶,也冒出了细小的气泡,像刚煮开的米粥,一个接一个地鼓出来,里面还裹着黑色的小字。
卖浆的老妪在渭水岸边摆了个摊子,正给客人舀浆,抬头就看见自己头顶飘着一行字:今天的黄豆又涨价了,磨出来的豆腐少了半块,秦币越来越不值钱,再这样下去,老婆子要喝西北风了。她吓得手一抖,浆碗摔在地上,碎瓷片溅了一地,可气泡还在往外冒,连她昨晚跟隔壁王婆抱怨宫里头的人都是傻子
的话,都被公放了出来。一个总角小儿在巷子里蹦跳着,手里攥着块麦芽糖,头顶的气泡却出卖了他:阿母藏在陶罐里的腌鱼被我偷吃了,我还把鱼刺埋在院子的桃树下,阿母肯定找不到!他娘正好从屋里出来,看见那行字,气得抄起扫帚就追,小儿一边跑一边哭,气泡里又蹦出一句:早知道不偷吃了,阿母的扫帚好疼!整座咸阳城变成了一口沸水锅,人人自危。商贩不敢再跟客人讨价还价,怕心里的这客人真抠门被公放;官吏不敢再收贿赂,怕这银子够买两亩地
的念头飘到上司眼里;连宫里的太监都不敢在背后说嬴政的坏话,怕刚念叨完陛下今天又没吃饭,就被头顶的气泡卖了。更糟的是咸阳令,他一大早去府衙查法令,刚翻开竹简就傻了眼——竹简上的法令条文正在逐字褪色,盗牛者斩的斩字先没了,接着是匿户者罚布二匹的罚字,最后整个竹简都变得光秃秃的,只剩下竹片的本色。他再翻其他竹简,都是一样的情况,仿佛那些字被弹幕里的口水溶解了,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法,正在崩解。
嬴政站在高台上,脸色比身上的玄袍还要黑。他忽然明白,那些弹幕不是祥瑞,也不是方士的幻术,是天——或者说后世的亿万人——在透过时光,跟他讲话。
他们知道他的过去,知道他的现在,甚至可能知道他的未来。他挥手召来李斯,声音冷得像冰:传朕的旨意,炼字为狱。凡弹幕中涉及国政、妄议朝政者,皆腰斩;凡百姓头顶气泡中藏有反心者,诛三族。李斯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头发已经白了大半,此刻吓得浑身发抖,忙跪倒在地:臣……臣遵旨。可他刚转身要走,头顶突然蹦出一行惨白的小字,比纸钱还要白:陛下,臣……臣也不知道怎么关闭弹幕,臣怕,臣怕自己哪天心里想错了,也被腰斩。嬴政愣住了。他活了三十九岁,从邯郸质子到秦王,再到始皇帝,见过无数人怕他——嫪毐怕他,吕不韦怕他,六国的君王怕他,连匈奴单于都怕他。可他第一次看见,自己最信任的丞相,怕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弹幕。更让他心慌的是,他发现自己也怕。
他怕哪天自己心里想长城修得太慢了,弹幕里就跳出暴君!不把百姓当人看!
;他怕自己想徐福怎么还不回来,弹幕里就跳出嬴政就是怕死,还想长生不老
;他甚至怕自己晚上做了个噩梦,第二天全咸阳的人都知道他梦见了嫪毐的鬼魂。无力
——这个词突然钻进他的脑子里,像一把钝刀,慢慢割着他的心脏。他这辈子,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想要灭韩,韩就灭了;想要修长城,长城就修了;想要称皇帝,全天下都得叫他陛下。可现在,他连关闭弹幕都做不到,连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想法都做不到。夜幕降临时,阿房宫的灯火全亮了,几千盏油灯挂在廊柱上,把宫殿照得像白昼,却照不亮那卷悬浮的光幕。
嬴政坐在高台的玉座上,四周的宫人都被他屏退了,只有赵高执着一支烛台,站在他身后。
赵高是个阉人,三十多岁,个子不高,总是弓着腰,像一只随时准备讨好主人的狗。
烛火的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贴在地上,像一条伺机而动的黑蛇。
嬴政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几乎被风吹散:赵高,你可看见那些字?赵高忙跪倒在地,额头抵着冰凉的玉阶:回陛下,臣……臣什么都没看见。臣只看见陛下一个人在自言自语,还看见宫人跪了一地。嬴政沉默了。他知道赵高没说谎,因为他刚才问过卫士,问过宫女,问过李斯,只有他一个人能看见那卷光幕,能看见那些弹幕。仿佛整个天下,只有他一个人被扔进了这个奇怪的弹幕世界里。他抬起手,在虚空里慢慢写下一行字,每个笔画都透着犹豫:后世如何看我?光幕静了三息,连风都好像停了。紧接着,无数条弹幕像雪崩一样爆了出来,密密麻麻地叠在光幕上,几乎要把光幕撑破:历史系小学生:嬴政就是个暴君!焚书坑儒,杀了那么多读书人,还修长城,累死了几十万百姓,活该被骂!基建狂魔:楼上的别只看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