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殒谢南乔《甩了渣夫和逆子,我带崽红遍全宇宙》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甩了渣夫和逆子,我带崽红遍全宇宙》全本在线阅读
时间: 2025-09-17 08:25:40
女子将绸缎往柜台里推了推:“抵房费,首到雨停。”
李逍遥刚要伸手去碰那绸缎,手腕就被李婶婶一把拍开。
婶婶把粗瓷碗往桌上重重一放,姜茶溅出几滴在油布上,她却顾不上擦,指着那女子道:“姑娘这是拿我们当什么人了?
莫说住到雨停,便是住到明年花开,咱仙剑客栈也不能收这东西!”
“身无分文便赊着!”
李婶婶抢过绸缎往她怀里塞,布帛摩擦间,李逍遥瞥见女子手腕内侧有道浅疤,像被细刃划过,旧得几乎与肤色相融,“我家逍遥他爹当年走江湖,欠过的酒钱能装满三艘船,也没见谁拿宝贝抵账的。”
女子的指尖捏紧了绸缎边缘,指节泛白。
她沉默片刻,忽然将绸缎重新放在柜台上,却推到了角落:“暂存。
我姓凤,单名一个辞。”
“凤辞……” 李婶婶念叨着这名字,忽然笑了,“倒是和这凤凰花缎对得上。
成,暂存就暂存。”
她拎起绸缎往灶房后走,“我那陪嫁的樟木箱,防潮得很,保管连个虫眼都不会有。”
凤辞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后,才转身往楼梯走。
她的步子很轻,踩在吱呀作响的木梯上,竟没发出寻常客人的拖沓声。
李逍遥蹲在柜台后数铜钱,眼角余光瞥见她裙摆扫过梯级,沾着的草屑簌簌落下 —— 那草叶边缘带锯齿,是村西头瘴气林里才有的 “断骨草”,寻常人碰了会红肿发痒,她却像没事人似的。
“喂,” 李逍遥忍不住开口,“你从瘴气林来?”
凤辞的脚步顿在第三级台阶。
她没回头,声音隔着雨幕飘下来:“路过。”
“那地方邪乎得很,” 李逍遥摸出块糙米饼啃着,“去年有个采药的老头进去,出来就疯疯癫癫,说看见会飞的蛇。”
楼上的房门 “吱呀” 一声合上,再没动静。
雨下到第五日时,天总算漏出点微光。
李逍遥蹲在院子里劈柴,斧头总往歪里偏,木柴溅得满地都是。
凤辞下楼倒水,站在廊下看了会儿,忽然道:“手腕太僵,顺着木纹走。”
李逍遥愣了愣,试着松了松手腕,斧头果然顺着木纹劈下去,利落得很。
他抬头想道谢,却见凤辞己经回了房,窗纸上映出她静坐的影子,像幅没上色的水墨画。
“这姑娘,不简单。”
李婶婶端着洗好的海菜路过,往楼上瞟了眼,“刚才王老大来送鱼,说看见个穿黑衫的汉子在村口打听,问有没有带凤凰花缎的女子路过。”
李逍遥的心猛地一跳:“黑衫汉子?”
“说是腰间挂着个铁牌,刻着个‘煞’字。”
李婶婶把海菜往竹匾里摊,“听着就不是善茬。”
暮色降临时,凤辞忽然下楼。
她换了身靛蓝色粗布裙,裙摆沾着新的泥点,像是刚出去过。
“借把伞。”
她站在柜台前,声音比往日低些。
李逍遥摸出墙角那把破伞,伞骨断了两根,补丁摞着补丁:“就这把了。”
凤辞接过伞,指尖在断骨处碰了碰,忽然道:“你那渔网的结节,打得太松,遇着大浪会散。”
她说着,拿起柜台上的麻线,三两下绾了个结,递给他,“这样才牢。”
那结打得极巧,绳头互相缠绕,看着松散,却越拽越紧。
李逍遥捏着那结,忽然想起爹留下的剑谱里画的 “缠丝扣”,手法竟有七分像。
等他抬头时,凤辞己经走进雨里,破伞的影子在暮色中摇摇晃晃,很快融进了村西头的雾里。
灶房的油灯亮起来时,李婶婶忽然 “咦” 了一声。
樟木箱的锁挂在外面,箱盖虚掩着。
她慌忙打开,凤凰花缎还好端端地躺在里面,只是上面多了片新鲜的凤凰花瓣,沾着雨珠,像是刚从树上摘的。
“这凤姑娘……” 李婶婶摸着花瓣,忽然觉得这雨,怕是停不了那么快了。
李逍遥刚要伸手去碰那绸缎,手腕就被李婶婶一把拍开。
婶婶把粗瓷碗往桌上重重一放,姜茶溅出几滴在油布上,她却顾不上擦,指着那女子道:“姑娘这是拿我们当什么人了?
莫说住到雨停,便是住到明年花开,咱仙剑客栈也不能收这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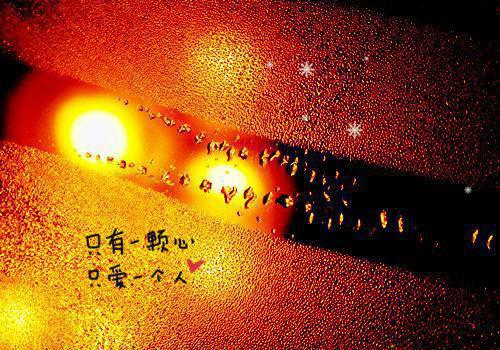
“身无分文便赊着!”
李婶婶抢过绸缎往她怀里塞,布帛摩擦间,李逍遥瞥见女子手腕内侧有道浅疤,像被细刃划过,旧得几乎与肤色相融,“我家逍遥他爹当年走江湖,欠过的酒钱能装满三艘船,也没见谁拿宝贝抵账的。”
女子的指尖捏紧了绸缎边缘,指节泛白。
她沉默片刻,忽然将绸缎重新放在柜台上,却推到了角落:“暂存。
我姓凤,单名一个辞。”
“凤辞……” 李婶婶念叨着这名字,忽然笑了,“倒是和这凤凰花缎对得上。
成,暂存就暂存。”
她拎起绸缎往灶房后走,“我那陪嫁的樟木箱,防潮得很,保管连个虫眼都不会有。”
凤辞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后,才转身往楼梯走。
她的步子很轻,踩在吱呀作响的木梯上,竟没发出寻常客人的拖沓声。
李逍遥蹲在柜台后数铜钱,眼角余光瞥见她裙摆扫过梯级,沾着的草屑簌簌落下 —— 那草叶边缘带锯齿,是村西头瘴气林里才有的 “断骨草”,寻常人碰了会红肿发痒,她却像没事人似的。
“喂,” 李逍遥忍不住开口,“你从瘴气林来?”
凤辞的脚步顿在第三级台阶。
她没回头,声音隔着雨幕飘下来:“路过。”
“那地方邪乎得很,” 李逍遥摸出块糙米饼啃着,“去年有个采药的老头进去,出来就疯疯癫癫,说看见会飞的蛇。”
楼上的房门 “吱呀” 一声合上,再没动静。
雨下到第五日时,天总算漏出点微光。
李逍遥蹲在院子里劈柴,斧头总往歪里偏,木柴溅得满地都是。
凤辞下楼倒水,站在廊下看了会儿,忽然道:“手腕太僵,顺着木纹走。”
李逍遥愣了愣,试着松了松手腕,斧头果然顺着木纹劈下去,利落得很。
他抬头想道谢,却见凤辞己经回了房,窗纸上映出她静坐的影子,像幅没上色的水墨画。
“这姑娘,不简单。”
李婶婶端着洗好的海菜路过,往楼上瞟了眼,“刚才王老大来送鱼,说看见个穿黑衫的汉子在村口打听,问有没有带凤凰花缎的女子路过。”
李逍遥的心猛地一跳:“黑衫汉子?”
“说是腰间挂着个铁牌,刻着个‘煞’字。”
李婶婶把海菜往竹匾里摊,“听着就不是善茬。”
暮色降临时,凤辞忽然下楼。
她换了身靛蓝色粗布裙,裙摆沾着新的泥点,像是刚出去过。
“借把伞。”
她站在柜台前,声音比往日低些。
李逍遥摸出墙角那把破伞,伞骨断了两根,补丁摞着补丁:“就这把了。”
凤辞接过伞,指尖在断骨处碰了碰,忽然道:“你那渔网的结节,打得太松,遇着大浪会散。”
她说着,拿起柜台上的麻线,三两下绾了个结,递给他,“这样才牢。”
那结打得极巧,绳头互相缠绕,看着松散,却越拽越紧。
李逍遥捏着那结,忽然想起爹留下的剑谱里画的 “缠丝扣”,手法竟有七分像。
等他抬头时,凤辞己经走进雨里,破伞的影子在暮色中摇摇晃晃,很快融进了村西头的雾里。
灶房的油灯亮起来时,李婶婶忽然 “咦” 了一声。
樟木箱的锁挂在外面,箱盖虚掩着。
她慌忙打开,凤凰花缎还好端端地躺在里面,只是上面多了片新鲜的凤凰花瓣,沾着雨珠,像是刚从树上摘的。
“这凤姑娘……” 李婶婶摸着花瓣,忽然觉得这雨,怕是停不了那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