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潮屠城(陆川周铭)最新推荐小说_最新免费小说尸潮屠城陆川周铭
1 雨夜的匿名信2018年深秋,江城市连下了三天暴雨。梧桐树叶被雨水泡得发沉,贴在柏油路上像摊开的墨绿色尸骸,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土腥气,混着老城区特有的煤烟味,压得人胸口发闷。我坐在“渡鸦事务所”的旧皮椅上,指尖夹着的香烟燃到了滤嘴,烫得指腹发麻才反应过来。窗外的雨帘把对面的老居民楼揉成模糊的灰影,只有二楼那扇挂着褪色蓝布帘的窗户亮着灯——那是独居的张老太家,她每天这个点都会坐在窗边织毛衣,今天却没见人影。我皱了皱眉,刚要移开目光,门被猛地推开,带着一身寒气的林秋闯了来。“陈默,你快看这个。
”她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拍在我桌上,雨水顺着她的黑色风衣下摆滴在地板上,晕出一小片深色水渍。林秋是市公安局的法医,也是我为数不多的“合作对象”——准确来说,是她总把那些警方束手无策的悬案偷偷塞给我,再用“帮忙”的名义蹭我这儿的速溶咖啡。
我掐灭烟头,拿起信封。信封是最普通的牛皮纸材质,没有邮票,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有正面用打印体写着“渡鸦事务所 陈默 亲启”。封口处没有胶水,是用细麻绳系的活结,解开时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松节油味。“哪里来的?”我问。
“楼下收发室老张给我的,说早上打扫卫生时在门口捡到的,看地址是你的就给我带上来了——他知道我常来这儿。”林秋拉开椅子坐下,从包里掏出笔记本,“我查了收发室的监控,凌晨四点二十左右,有个穿黑色连帽衫的人把信封放在门口,戴着手套和口罩,看不清脸,身高大概一米七五左右,走路有点跛,左腿好像不太方便。”我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A4纸,同样是打印体,内容很简短:“10月17日,西郊废弃玻璃厂,有东西给你看。别告诉警察。”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只有这一行字。
我把纸举起来对着灯光看了看,没有水印,也没有隐藏的字迹。纸上同样有淡淡的松节油味,和信封上的味道一致。“10月17日……就是明天。”林秋凑过来看了一眼,眉头皱得更紧,“西郊废弃玻璃厂?那地方三年前就停产了,后来因为出过一场火灾,一直没人管,现在荒得很,白天都没人去。”我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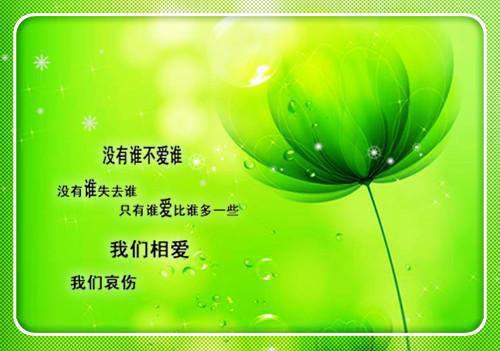
渡鸦事务所开了五年,大多时候只接些找猫找狗、查婚外情的小案子,很少和这种“匿名信+神秘地点”的事扯上关系。对方为什么找我?为什么不让告诉警察?
“有东西给你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觉得是恶作剧?”林秋见我不说话,试探着问。
“不像。”我摇摇头,把纸和信封放回桌上,“打印体、无署名、避开监控,还特意提醒别告诉警察,太刻意了。如果是恶作剧,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林秋点点头,从笔记本里翻出一张照片推给我:“这是三年前玻璃厂火灾的现场照,我托档案室的朋友找的。火灾是从熔制车间烧起来的,最后整个车间都塌了,当时没人伤亡,因为停产前已经把人都撤了。后来消防队查过,说是电路老化引起的,没立案。
”照片里的熔制车间只剩下断壁残垣,黑色的钢架扭曲成奇怪的形状,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灰烬,空气中似乎都能透过照片闻到焦糊味。我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忽然注意到角落有个模糊的白色物体,像是一块布料。“这是什么?”我指着那个物体问。
“哦,当时消防队说是一块塑料布,烧剩下的,没在意。”林秋凑过来看了一眼,“怎么了?
有问题?”“不确定。”我把照片还给她,“明天去看看就知道了。”“你真要去?
”林秋的语气带着担忧,“对方身份不明,地点又偏僻,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我穿便服,不算‘告诉警察’。”我想了想,点头同意了。
林秋的法医身份有时候能派上用场,而且她格斗术不错,真遇到危险也能有个照应。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天空依旧是灰蒙蒙的,阳光像被稀释过的牛奶,勉强透过云层洒在地面上。我和林秋约在事务所楼下见面,她穿了件米色的冲锋衣,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里面装了法医工具箱和一些应急用品。“车我找好了,在对面巷子里。”林秋指了指不远处的巷子,“是我表哥的私家车,没挂牌照,不会引人注意。”我点点头,跟着她往巷子走。巷子很窄,两侧是斑驳的砖墙,墙上贴满了小广告,风一吹,卷着落叶和灰尘扑在脸上。走到巷子尽头,一辆银灰色的大众停在那里,车窗贴着深色的膜,看不清里面。“上车。
”林秋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我坐进去,她绕到驾驶座,发动车子。西郊离市区很远,开车要一个多小时。路上很安静,只有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林秋打开收音机,里面放着舒缓的轻音乐,却没能缓解车厢里的紧张气氛。“你说,对方会是谁?
”林秋忽然开口问。“不知道。”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树木,“可能是知情人,也可能是凶手。”“凶手?”林秋的手顿了一下,“你觉得和三年前的火灾有关?
”“可能性很大。”我转过头看着她,“如果只是普通的案子,对方没必要特意提到玻璃厂,还不让告诉警察。三年前的火灾说是电路老化,但如果是人为纵火,现在有人想翻案,找我这个‘局外人’,或许是因为信不过警察。”林秋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说:“如果真的是人为纵火,那当时为什么没查出来?
消防队的报告应该不会出错吧?”“报告是人写的,人会出错,也会撒谎。”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到了地方再说吧。”车子在郊区的土路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了废弃玻璃厂的影子。玻璃厂的大门早就没了,只剩下两根锈迹斑斑的水泥柱子,柱子上还能看到模糊的“江城玻璃厂”字样。厂区里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风一吹,杂草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有人在暗处低语。林秋把车停在离大门不远的一棵树下,关掉引擎。“我们步行进去,车停在这里,万一有事能快点逃。”我点点头,和她一起下车。
刚走了几步,就闻到一股淡淡的松节油味,和信封上的味道一模一样。“你闻。
”林秋停下脚步,皱着鼻子,“松节油味。”“对方应该已经来过了。
”我顺着味道的方向走,“味道是从熔制车间那边飘过来的。”熔制车间在厂区的最里面,和照片里一样,只剩下断壁残垣。我们踩着杂草往里面走,脚下时不时会踩到碎玻璃,发出“咯吱”的声音。走到车间中央,松节油味更浓了,我看到地面上有一个新挖的土坑,坑旁边放着一把铁锹,铁锹上还沾着湿土。“在这里。”我走过去,蹲在坑边。坑不深,大概一米左右,里面铺着一块白色的塑料布,塑料布下面似乎裹着什么东西。林秋也蹲下来,从包里掏出手套戴上,小心翼翼地掀开塑料布的一角。当看到里面的东西时,她倒吸了一口凉气,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塑料布下面裹着的,是一具骸骨。
骸骨已经有些风化,骨头的颜色呈黄褐色,关节处有明显的断裂痕迹。最诡异的是,骸骨的胸腔里插着一块破碎的镜片,镜片的边缘很锋利,上面还残留着一点点暗红色的痕迹,像是干涸的血迹。“这……这是谁?”林秋的声音有些发颤,她从包里掏出相机,对着骸骨拍了几张照片,“看骸骨的形态,应该是女性,年龄大概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死亡时间至少在两年以上。”我盯着骸骨胸腔里的镜片,忽然想起了什么。“三年前的火灾,现场是不是也发现了一块塑料布?”林秋点点头,手忙脚乱地从包里翻出笔记本:“对,就是我昨天给你看的那张照片里的,当时说是烧剩下的塑料布,没在意。现在看来,那块塑料布可能就是裹骸骨的这块,火灾是为了掩盖尸体?”“很有可能。”我站起身,环顾四周。熔制车间的墙壁上有很多裂缝,角落里堆着废弃的玻璃制品,阳光从裂缝里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显得格外阴森。“对方把我们引到这里,就是为了让我们发现这具骸骨。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不是警察?”林秋蹲在坑边,仔细检查着骸骨:“骸骨的颅骨有明显的凹陷,应该是钝器伤,致命伤可能是这个。
胸腔里的镜片……看起来像是普通的玻璃窗镜片,边缘被打磨过,应该是死后插进去的,像是某种标记。”我走到车间的角落,那里堆着一堆废弃的玻璃碎片,阳光照在碎片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我拿起一块碎片,闻了闻,上面有淡淡的松节油味。
“松节油是用来稀释玻璃颜料的,玻璃厂的工人应该经常用。”“你的意思是,凶手是玻璃厂的工人?或者至少和玻璃厂有关?”林秋走过来,看着我手里的玻璃碎片。
“可能性很大。”我把碎片放回原处,“三年前的火灾,说是电路老化,但如果是人为纵火,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这具尸体。现在有人把尸体挖出来,找我们来发现,说明这个人知道真相,而且想让真相曝光,但又不敢直接找警察,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牵涉其中,或者害怕凶手报复。”林秋点点头,从包里掏出物证袋,小心翼翼地把骸骨胸腔里的镜片取出来放进去:“我先把这个镜片带回局里化验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DNA或者指纹。骸骨的话,需要联系市局的考古队来挖掘,毕竟我们没有专业的挖掘工具,万一破坏了现场就不好了。”“不行。”我立刻阻止她,“匿名信里说别告诉警察,如果我们现在联系市局,对方可能会有反应,说不定会打草惊蛇。
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对方的目的是什么,冒然行动太危险。”“那怎么办?
”林秋看着坑里的骸骨,有些着急,“总不能把它留在这里吧?万一被别人发现,或者被凶手回来处理掉,我们就什么线索都没有了。”我想了想,说:“先把骸骨重新埋回去,做个标记,等晚上再来。你去化验镜片,我去查一下三年前玻璃厂的员工名单,看看有没有失踪的女性员工。我们分头行动,有消息随时联系。”林秋点点头,同意了我的计划。我们一起把骸骨重新用塑料布裹好,埋回土坑里,在旁边的一棵歪脖子树上系了一根红绳作为标记。然后,我们迅速离开了玻璃厂,开车返回市区。路上,林秋把镜片送到了市局的物证科,让他们加急化验。我则回到了事务所,开始查三年前玻璃厂的员工名单。
玻璃厂的资料很难找,因为停产之后,大部分员工都遣散了,档案也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
我找了几个以前在工厂上班的老熟人,打了十几个电话,个退休的老会计那里拿到了一份2015年的员工名单——也就是玻璃厂停产前一年的名单。
名单上有一百多个人,女性员工有三十多个。我把名单打印出来,逐一排查,看看有没有在2015年到2016年之间失踪的女性员工。查了一下午,终于有了线索。
名单上有一个叫“苏晴”的女性员工,出生于1988年,在玻璃厂的彩绘车间工作,负责给玻璃制品上色。根据老会计的回忆,苏晴在2016年3月突然没来上班,当时厂长以为她是辞职了,没在意,也没报警。后来玻璃厂停产,大家就更没人提起她了。
“苏晴……”我看着名单上的名字,心里有种预感,坑里的骸骨可能就是她。
我立刻给林秋打电话,告诉她这个线索。“苏晴?”林秋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带着一丝兴奋,“我刚拿到镜片的化验报告,镜片上没有指纹,但有微量的血迹,经过DNA比对,和市局数据库里一个叫‘苏晴’的失踪人口的DNA一致!
苏晴在2016年5月被她的家人报了失踪,因为一直没找到人,所以她的DNA被录入了数据库。”“太好了!”我忍不住握紧了拳头,“这么说,坑里的骸骨就是苏晴。那她的死因应该就是颅骨钝器伤,胸腔里的镜片是死后插进去的,可能是凶手的某种签名。”“嗯。”林秋的声音顿了一下,“还有一个线索,镜片上除了苏晴的血迹,还有一点点玻璃颜料的残留,和彩绘车间用的颜料成分一致。
”“彩绘车间……苏晴就是在彩绘车间工作的。”我看着名单上的“彩绘车间”四个字,“凶手应该就是和苏晴在同一个车间工作的人,或者至少是熟悉彩绘车间情况的人。
”“我现在就去查彩绘车间的员工名单,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林秋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