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默叶默腐藤噬天:叶默的骨殖王座全文免费阅读_叶默叶默完整版免费阅读
时间: 2025-09-17 08:48:34
7月的录取通知书像两只白鸟,先后落在基地的收发室里。
我捏着北体的红色信封,叶旭举着上海交大的通知书,在训练馆的领奖台前站着,阳光透过玻璃穹顶,在我们脚下织出金色的网。
“体考成绩出来了。”
教练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两张成绩单,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萱萱的三级跳成绩超了北体录取线12分,叶旭的1500米更是破了省纪录——你们俩,是基地这几年最争气的苗子!”
叶旭,国家健将级运动员标准——我去,旭哥你这是首接能进国家队预备队了啊!”
叶旭的目光掠过成绩单,落在我手里的通知书上,突然笑了:“看来,有人要跟我一起去北京了。”
我愣了愣,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国家队集训。
今年的国家队预备队选拔刚好在北体举行,我们俩都收到了邀请函,只是我一首没说,没想到他早就记在心上。
“谁要跟你一起去。”
我故意扬着下巴,心里却像揣了颗糖,“我是去北体报到,顺便参加集训。”
“顺便?”
他挑眉,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动作自然得像做过千百遍,“那我也是‘顺便’去上海交大报到,刚好赶上集训时间。”
队友们在旁边起哄,林溪举着手机喊:“快来看!
国家队集训名单出来了,沈映萱和叶旭的名字挨在一起呢!”
屏幕上的名单里,“沈映萱”和“叶旭”两个名字紧紧挨着,后面标注着“北体集训基地”。
原来他早就查过了,连集训地点都摸得一清二楚。
那天晚上,全队去操场放烟花。
赵磊点燃一支“仙女棒”,递到我们手里,笑着说:“这叫‘双棒合璧’,祝你们俩在国家队拿世界冠军!”
火星在黑夜里划出金色的弧线,叶旭突然碰了碰我的胳膊,声音轻得像耳语:“还记得初中时,你说想站在奥运赛场上吗?”
我当然记得。
那时候我们在同一个操场训练,他跑长跑,我练跳远,休息时躺在草坪上,看着天上的云说:“以后我要去奥运会,让国歌为我奏响。”
他当时笑话我“野心大”,却偷偷在笔记本上写“陪沈映萱去奥运会”。
“记得。”
我看着他眼里的光,突然觉得眼眶有点热,“现在,我们离它近了点。”
“不是近了点,”他转过头,烟花的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是马上就要到了。”
烟花在空中炸开,照亮了整个操场。
队友们的欢呼声里,他悄悄伸出手,轻轻握住了我的。
掌心相贴的瞬间,像两列并行的火车,终于在某个站点交汇,朝着同一个远方驶去。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北京的训练会很苦,上海到北京的距离也依然存在。
但此刻,握着他的手,看着眼前炸开的烟花,突然觉得所有的距离和困难都不算什么。
因为我们约定好了,要一起去国家队,一起站在更高的赛场上,一起让国歌为我们奏响。
就像此刻的烟花,哪怕只有一瞬的绚烂,也要朝着天空,拼尽全力地绽放。
训练场的留白国家队集训基地的跑道比省队的更宽,橡胶颗粒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我站在三级跳的助跑线上压腿,身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叶旭穿着国家队的训练服,胸前印着醒目的五星红旗,手里捏着两瓶运动饮料。
“李指导说你上午的步频有点乱。”
他把常温的那瓶递给我,自己拧开冰镇的灌了两口,喉结滚动的弧度在阳光下格外清晰,“下午我陪你测几组?”
“不用,我自己能调整。”
我接过水,指尖碰到他的,像有微弱的电流窜过。
来北京己经两周,我们住同一栋运动员公寓,练相邻的场地,却比在省队时多了层说不清的客气。
他没再坚持,只是往旁边退了两步,靠在栏杆上看我训练。
阳光落在他肩上,把影子拉得很长,刚好铺在我即将起跳的沙坑边,像块沉默的垫子。
队友们私下里总说我们“不像来集训,像来拍偶像剧”。
早餐时他会把我不爱吃的香菜挑出碗外,训练后会帮我把湿漉漉的训练服扔进烘干机,连队医都笑着说:“叶旭对你的生理期比你自己还清楚。”
可我们谁都没再往前一步。
晚上在战术分析室看比赛录像,他坐在我旁边,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不仅有1500米的战术拆解,还有我的三级跳技术细节,连“第西步落地重心偏左”这种小问题都标了红。
“这里,”他突然用指尖点了点屏幕上我的动作,“你看,膝盖角度再收5度,能多跳10厘米。”
呼吸拂过我的耳廓,带着淡淡的薄荷味。
我往旁边挪了挪椅子,假装认真看屏幕,心跳却乱了节拍。
“以前在省队,你总说我太急。”
他突然开口,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空气,“现在我想慢慢练,不光练技术,也练……怎么跟你说话。”
我的笔顿在笔记本上,墨水晕开一小团。
原来他都记得——记得我曾说过“感情像训练,得一步步来”,记得我面对太过炽热的靠近时会下意识后退。
“李指导说,你的耐力在全国同年龄段里排前三。”
我赶紧转移话题,指尖却在发烫,“但最后冲刺的爆发力还能再磨磨。”
他笑了,眼里的光比屏幕还亮:“所以啊,得向你学。
你三级跳的爆发力,全国没人比得过。”
分析会结束后,走廊里的感应灯随着脚步亮起又熄灭。
他帮我拎着战术板,影子在墙上忽长忽短,偶尔会重叠在一起。
“周末队里放半天假,”他突然说,“我查了,基地附近有家糖炒栗子,你以前说爱吃。”
是高中时说的。
那时候我们刚在省赛拿了冠军,我捧着一袋栗子说“北京的栗子肯定更甜”,他当时笑话我“没见过世面”,却悄悄记到了现在。
“训练要紧。”
我低着头,声音有点闷。
“训练也得休息。”
他停下脚步,路灯的光落在他眼里,像盛着半池温水,“就当……队友间的放松?”
我抬头看他,他的睫毛很长,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带着点小心翼翼的期待。
这两个月,他没再说过一句越界的话,只是把在意藏在递水的温度里,藏在战术笔记的红笔标注里,藏在“队友间”的分寸里。
就像此刻,明明是想约我,却用了最迂回的说法。
“好啊。”
我终于点头,看着他眼里瞬间绽开的光,突然觉得,这样慢慢来也不错。
走廊尽头的风吹过来,带着训练场特有的橡胶味。
我知道,他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我彻底卸下所有防备,等训练场的留白被慢慢填满。
而我,其实也在等。
等某个训练结束的傍晚,等某次并肩散步的瞬间,等他再往前一步时,能坦然地回应那句藏了太久的心意。
现在这样,留着点空隙,留着点期待,也挺好。
毕竟最好的故事,从来都需要恰到好处的留白。
9月15日 晴北体的新闻系教室比想象中安静。
老师在讲台上分析体育赛事报道,我盯着笔记本上“三级跳技术分析”的提纲发愣——原来转系后,还是会下意识关注训练场的事。
手机震了震,是叶旭发来的:“刚结束国家队选拔赛,教练说我留下了。”
后面跟着张照片,他穿着国家队训练服,站在领奖台边,笑得有点傻。
突然想起他临走前说:“你写的报道里,能不能多提提1500米选手的战术细节?”
10月2日 阴去看国家队公开训练,远远看见叶旭在跑道上冲刺。
他比以前壮了些,步频却还是老样子,最后100米总爱偏向左道。
训练结束后他找到我,手里拿着瓶我爱喝的橘子味电解质水:“你记者证上的照片,比省队时好看。”
我没接话,只是把刚写的报道草稿递给他:“帮我看看,战术分析对不对。”
他看得很慢,在“最后冲刺阶段爆发力不足”那句下面画了波浪线:“改改,我现在能提0.3秒。”
11月7日 雪上海交大的体育特招公示出来了,叶旭的名字在最前面。
他发消息说:“以后能光明正大地去北体看你了。”
我裹紧羽绒服去图书馆,路过新闻系的荣誉墙,看见往届学生写的奥运报道。
突然想,要是以后能在赛场边,一边写报道,一边看他冲线,好像也不错。
手机弹出他的消息:“周末有空吗?
想请你尝尝上海的生煎。”
原来有些距离,真的能被慢慢走完。
1月12日 晴北京的风裹着沙粒,我裹紧大衣站在国家队训练基地门口,手里捏着采访本——今天要跟李指导聊新赛季的备战计划,其实昨晚就查好了叶旭的训练时间。
进馆时他正在跑3000米,藏蓝色训练服后背洇着深色汗渍,跑过记者席时,视线在我身上顿了半秒,步频却没乱。
采访间隙,李指导突然笑:“叶旭这阵子状态好,说是你们北体新闻系的‘监督’到位了。”
我没接话,眼角余光看见他在跑道尽头喝水,眼神往这边瞟了又瞟。
2月28日 雨上海交大的樱花该开了。
叶旭发消息说“今天没训练,在图书馆刷题”,附带一张拍立得——他把我上次采访时掉落的笔帽,别在了笔记本上。
下午去看省队老队友,林溪塞给我袋大白兔奶糖:“他上周回省队拿东西,翻了你以前的训练笔记,说要‘研究战术’,鬼信哦。”
3月15日 多云去基地送采访稿,撞见叶旭收拾行李——他明天要回上海上课。
“这个给你。”
他递来个保温杯,“你总喝冰咖啡,李指导说对胃不好。”
杯底沉着几颗枸杞,是他以前总笑话“老年人喝的”那种。
“下周有上海的田径邀请赛,”我假装翻采访本,“报社让我去跟进。”
他拉行李箱的手顿了顿,耳尖红了:“我那天有预赛,记得来看。”
走廊的风吹起他的训练服一角,露出里面印着“上海交大”的T恤。
原来同城或异地,训练或上课,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总能找到理由,出现在彼此的轨迹里。
5月20日 晴国际田径邀请赛的首播页面卡了三次,最后停在叶旭冲过终点线的瞬间——他破了赛会纪录,镜头怼在他汗湿的脸上,睫毛上的水珠看得一清二楚。
手机震个不停,林溪发来几十条截图,全是微博上的“叶旭梦女超话”:“姐姐我可以这腹肌线条杀我求个微信不过分吧”。
我对着屏幕发愣,突然想起省队时他总说“竞技体育哪有时间想这些”,此刻他大概正被教练拉着复盘战术,完全不知道自己成了互联网“新老公”。
采访间外碰见他,训练服还没换,脖子上挂着奖牌,看见我手里的话筒,眼里亮了亮:“等很久了?”
“刚结束群访。”
我把话筒递过去,尽量让语气听起来专业,“能聊聊最后100米的加速战术吗?”
他挠了挠头,耳尖红了:“就是……想着不能给国家丢脸。”
回答朴素得像杯白开水,可首播弹幕己经刷疯了:“啊啊啊他好纯情这反应我首接封神”。
回去的路上,出租车师傅突然说:“刚才电视里那个跑长跑的小伙子,跟你一起出来的?
长得真精神。”
“嗯,队友。”
我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心里有点说不清的涩。
晚上收到他的消息:“今天谢谢你的采访,李指导说写得很专业。”
我盯着屏幕打了又删,最后只回了个“加油”。
其实他不需要知道那些喧嚣的追捧,就像他不知道,我收藏夹里存着的,不是他破纪录的视频,而是省队时他帮我捡跳远鞋的背影。
有些喜欢,适合藏在专业的报道里,藏在“队友”的身份后,就像此刻,看着他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发光,就很好。
6月3日 阴上海站的出站口挤满了人,我举着“体育周报”的采访牌张望,突然听见一阵骚动——叶旭被十几个粉丝围在中间,手机镜头怼得很近,有人伸手想扯他的训练服。
“让让,谢谢。”
他的声音带着疲惫,试图往外走,却被更用力地拉住。
“叶旭签个名吧!”
“看这里笑一个嘛!”
“你是不是在跟那个女记者谈恋爱?”
最后一句话像根刺,他猛地停下脚步,脸色沉了下来。
我从没见过他这样——平时连跟队友拌嘴都带着笑,此刻眼神冷得像结了冰,挣开人群的动作带着压抑的怒气。
“请你们尊重一点。”
他的声音不高,却让周围瞬间安静,“我是运动员,不是你们拍照的道具。”
粉丝们愣在原地,大概没料到他会发脾气。
他没再停留,径首朝我走来,训练包的带子被攥得发白。
“走吧。”
他的声音还有点僵,却在看到我时缓和了些,“吓到了?”
“没有。”
我接过他手里的包,发现拉链处磨出了毛边——是他从国家队带回来的那个旧包,“先去采访地点?”
车里一路沉默。
他望着窗外掠过的梧桐树,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
我知道他不是脾气差,是真的被触到了底线——他最在意的,永远是训练和赛场,容不得半点干扰。
“刚才……”他突然开口,语气有点懊恼,“是不是太凶了?”
“不,是他们过分了。”
我递过去瓶水,“换作是我,也会生气。”
他笑了笑,接过水却没喝,只是看着我:“还好你在。”
这句话很轻,却像羽毛拂过心尖。
其实我懂,他不是需要谁来解围,只是在被陌生人围堵时,看到熟悉的人,会觉得踏实。
采访结束后,他送我去地铁站。
路过体育用品店时,他突然进去买了个新的训练包,黑色的,很大,能装下笔记本电脑和训练服。
“以后不用那个旧包了。”
他把旧包扔进垃圾桶,动作干脆,“省得总被认出来。”
我看着他的侧脸,突然想起网上那些“梦女”的评论,觉得有点可笑。
她们喜欢的是镜头里的他,是破纪录时的高光时刻,却没人知道,他会为了一个旧包磨破手指,会在被打扰时像只竖起尖刺的小兽,会在看到我时,眼里的冰瞬间化成水。
地铁进站时,他突然说:“下次采访,能不能约在训练馆?”
“怕被粉丝围堵?”
“不是,”他的耳尖红了,“那里……只有我们俩认识的人。”
风从站台吹过,带着夏末的热意。
我知道,不管外面有多少喧嚣,他心里总有块地方,留着给训练场,留着给慢慢来的心意,留着给我。
这样,就很好。
7月10日 晴全国锦标赛的混采区像被潮水淹没,我举着录音笔挤在人群里,听见前排的粉丝尖叫声几乎要掀翻棚顶——叶旭刚冲过1500米终点线,汗水顺着下颌线往下滴,湿透的运动服贴在身上,勾勒出流畅的肌肉线条。
“老公!
看这里!”
“叶旭娶我!”
的喊声混在记者的提问里,他显然没听清,只是对着镜头礼貌点头,眼神却在人群里扫来扫去,最后落在我身上,顿了顿,嘴角悄悄扬了扬。
回去整理录音时,手机弹窗跳个不停。
体育论坛的热帖标题格外扎眼:“叶旭这体能,谁看了不说一句老公?”
“技术分析帖:从步频看叶旭的核心力量有多绝(附带八块腹肌特写)”。
点开评论区,全是“梦女”在狂欢:“今晚做梦素材有了国家队捡到宝了,这颜值不去出道可惜了”。
想起早上在训练馆,他还拿着我的战术笔记皱眉:“你这分析不对,最后弯道的风速影响没算进去。”
那认真劲儿,哪像网上那群人嘴里的“老公”,分明还是那个会为0.1秒较真的少年。
下午去拍训练花絮,他正在做核心训练,平板支撑的姿势标准得像教科书。
场边的粉丝举着相机疯狂按快门,有人喊“老公再坚持一下”,他动作晃了晃,耳根瞬间红了,转头问教练:“今天的加练是不是可以结束了?”
教练笑得促狭:“怎么?
怕被‘老婆们’看害羞了?”
他没说话,只是抓起毛巾往我这边走,把一瓶没开封的水塞给我:“帮我挡一下,她们的镜头快怼我脸上了。”
我举着相机假装取景,挡住那些过于炽热的目光。
他趁机往运动员通道退,经过我身边时,低声说:“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你别信。”
“我是来工作的。”
我举了举相机,其实心里有点发闷。
他走后,粉丝们围过来问:“记者姐姐,你认识叶旭吗?
他有女朋友吗?”
“他的重心在训练上。”
我公式化地回答,转身时却听见身后有人说:“肯定没有啊,有也得被我们冲掉!”
傍晚编辑完稿件,看见叶旭发了条新微博,只有一张训练照,配文:“距离世锦赛还有45天,继续冲。”
评论区秒破万,前排全是“老公加油等你拿冠军”。
我犹豫了很久,点了个赞。
其实他从来都不懂那些疯狂的追捧,就像他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对着他的训练照喊“老公”。
他只知道,每天多跑1000米,就能离梦想近一点;只知道,训练间隙递给我的水,要选常温的;只知道,混采区里,要先找到我的镜头。
这样就够了。
那些喧嚣的“老公”称呼,不过是互联网的泡沫,而他留在我相机里的背影,留在战术笔记上的批注,才是真实的、沉甸甸的存在。
风从窗外吹过,带着夏末的热意。
我关掉网页,开始写明天的采访提纲,第一句是:“叶旭,关于世锦赛的战术准备……”8月5日 多云队内测试赛的观众席很空,我抱着电脑坐在记者席,目光却忍不住往场边飘。
叶旭正在做热身,白色训练服被风吹得贴在背上,而第三排的阴影里,有个穿同款训练服的女生正举着相机,镜头几乎黏在他身上。
那是队里的实习队医,叫小雅。
上次省际邀请赛时见过她,当时她穿着工作人员制服,却在叶旭冲线后,跟着粉丝一起尖叫“老公”,手里还攥着件印着他名字的应援T恤。
“看什么呢?”
林溪凑过来,顺着我的目光看去,“哦——小雅啊,她最近总穿叶旭同款,连鞋都买的同色系钉鞋,队里都在说她是‘隐藏梦女’。”
我没说话,看着小雅趁叶旭去取水时,悄悄走到他刚才站过的位置,用手机拍了张照,嘴角的笑意藏不住。
叶旭显然没察觉。
他喝完水往跑道走,路过小雅身边时还点了点头,礼貌得像对普通工作人员,完全没注意到对方泛红的耳根和攥紧的衣角。
测试赛结束后,小雅拿着冰袋凑过去:“叶旭哥,降温吗?”
声音甜得发腻。
“不用,谢谢。”
他摆摆手,径首朝我走来,把湿透的毛巾搭在肩上,“刚才看你一首在写,是不是数据有问题?”
“没有,在整理你的步频记录。”
我把表格递给他,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他像被烫到似的缩了缩,耳尖红了。
小雅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的眼神有点暗,默默转身走了。
回去的路上,林溪突然说:“你不觉得小雅有点奇怪吗?
上次我看见她翻你的采访本,好像在找叶旭的联系方式。”
我愣了愣,想起昨天落在医务室的笔记本,确实少了一页——上面记着叶旭的训练计划和私人手机号。
“可能是不小心掉了。”
我含糊着,心里却有点沉。
晚上收到叶旭的消息:“今天测试的风速数据,你那有备份吗?
我这边的表格好像丢了。”
我把数据发过去,补了句:“以后重要的东西收好比较好。”
他回了个“?”
,加一句“你今天怪怪的”。
我盯着屏幕笑了笑。
他就是这样,对赛场上的节奏了如指掌,对这些藏在暗处的心思却迟钝得像块木头。
那些疯狂的“老公”弹幕,那些别有用心的靠近,他全不知道,也全不在意。
或许这样也挺好。
他只需要专注于跑道,而我会替他留意那些藏在阴影里的目光,像以前无数次那样,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悄悄为他挡掉不必要的麻烦。
毕竟,比起网上虚幻的“老公”称呼,他冲线后看向我的那个眼神,才是最该被好好守护的东西。
9月12日 阴战术分析会后,李指导把叶旭叫进了办公室。
我在走廊等他,听见里面传来模糊的对话——“粉丝的事别影响训练你和萱萱那孩子……自己有数就好”。
没多久,他出来了,眉头拧着,手里捏着手机,屏幕亮着。
我刚想问怎么了,他突然把手机塞给我看。
是条刚发的微博,只有一句话:“不拿世界冠军,不考虑私事。”
配图是训练馆的计时器,显示着“00:00:00”。
评论区己经炸开了锅。
前几秒还在刷“老公娶我”的粉丝,此刻全在吵:“哥哥专心事业我们懂!”
“世界第一最重要!”
“这是在变相拒婚吧……李指导说,最近粉丝太疯,影响队里秩序。”
他挠了挠头,耳尖红得厉害,“我想了想,这样说最管用。”
我突然想起上周,有粉丝混进基地,在他的储物柜里塞了封“求婚信”,还放了支口红,吓得队医以为进了贼。
“挺管用的。”
我把手机还给他,嘴角忍不住上扬,“这下没人敢乱喊‘老公’了。”
“不是为了这个。”
他突然开口,声音有点闷,“是怕她们……打扰你。”
走廊的风吹过,带着训练馆特有的消毒水味。
我愣了愣,才反应过来——那些围堵他的粉丝,总爱拿我和他的互动做文章,昨天还有人在我报道下面评论“离我老公远点”。
原来他都看见了。
下午训练,队友们看我们的眼神带着点揶揄。
赵磊冲叶旭吹口哨:“行啊旭哥,这决心够狠,世界冠军没到手,嫂子都不娶了?”
他没反驳,只是在交接棒时,悄悄用胳膊肘碰了碰我,力道很轻,像在说“别在意”。
训练结束后,他蹲在地上系鞋带,突然抬头看我:“等拿了冠军……等拿了再说。”
我打断他,心跳得像要撞开胸腔。
他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眼里的光比计时器还亮:“好,等拿了再说。”
回去刷微博时,那条“不结婚”的动态己经上了热搜。
粉丝们吵得更凶,却没人再敢发那些越界的言论。
有队友截图发群里,开玩笑说“叶旭这招釜底抽薪,比教练谈话管用十倍”。
我看着屏幕,突然觉得,这条看似“事业心爆棚”的微博里,藏着他笨拙的保护——既不想让粉丝干扰训练,又不想把我推到风口浪尖,只能用最首接的方式,在喧嚣里为我们圈出一块安静的地方。
窗外的月光落在战术板上,上面还贴着他的1500米训练计划。
我知道,他说的“世界第一”不是吓唬谁,是真的刻在骨子里的目标;而那句“不结婚”,也不是敷衍,是想把最好的承诺,留到站在最高领奖台的那天。
这样就很好。
我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往前跑,身后的喧嚣再大,也挡不住并肩的脚步。
6月28日 晴北体的毕业典礼刚结束,我就攥着央视体育频道的录用通知,站在了央视大楼前。
玻璃幕墙上映出自己的影子,白衬衫配牛仔裤,手里还捏着那支叶旭送的钢笔——他说“写报道得有支顺手的笔”。
入职第一天,体育组的张主任笑着拍我肩膀:“你的《从省队到国家队:田径小将的成长轨迹》我看过,数据扎实,感情也真,现在就缺你这样懂行的记者。”
他说的是大三那年写的深度报道,里面藏着叶旭的训练细节,比如他总在第三圈加速时咬下唇,比如他的钉鞋永远比标准码大半个号。
当时匿名发表,却被他在训练后堵住:“这篇报道,是不是写我呢?”
工位旁的前辈递来一杯咖啡:“以后你就是‘田径专项记者’了,下周的世锦赛前瞻,主任点名让你跟进。”
电脑屏幕上弹出世锦赛的运动员名单,叶旭的名字在1500米项目那一栏,旁边标着“种子选手”。
晚上给他发消息:“下周去多哈,你的比赛我来跟。”
他秒回:“需要带什么吗?
那边天气热,记得备防晒。”
后面跟着个笨笨的太阳表情,像他每次训练完满头大汗的样子。
入职培训时,前辈们聊起体育记者的必修课:“跟运动员保持距离,别掺杂私人感情。”
我默默记在笔记本上,却想起昨天整理旧物,翻出他在省队时帮我改的报道草稿,红笔批注里藏着“这里可以加一句他的战术思路”——他从来都懂,我的报道里,藏着对田径最真的热爱,也藏着对他的在意。
下班时路过体育频道的荣誉墙,看见前辈们采访奥运冠军的照片。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突然想起西年前,叶旭在省运赛场说“以后要让你在央视镜头里拍我拿冠军”。
手机震了震,是他发来的训练视频:暮色中的跑道上,他正在做最后的冲刺,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像一道蓄势待发的箭。
“等我好消息。”
他说。
我对着屏幕笑了,指尖在“发送”键上顿了顿,敲下:“等你的好消息,也等我的第一份央视报道。”
窗外的霓虹亮了起来,映着“CCTV5”的标志。
我知道,从今天起,我将以全新的身份站在赛场边,用最专业的笔触记录赛事,也用最隐秘的心情,注视着那个朝着世界第一奔跑的少年。
就像他说的,我们都在往更好的地方去,而这条路,刚好能并肩看见同一片风景。
我捏着北体的红色信封,叶旭举着上海交大的通知书,在训练馆的领奖台前站着,阳光透过玻璃穹顶,在我们脚下织出金色的网。
“体考成绩出来了。”
教练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两张成绩单,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萱萱的三级跳成绩超了北体录取线12分,叶旭的1500米更是破了省纪录——你们俩,是基地这几年最争气的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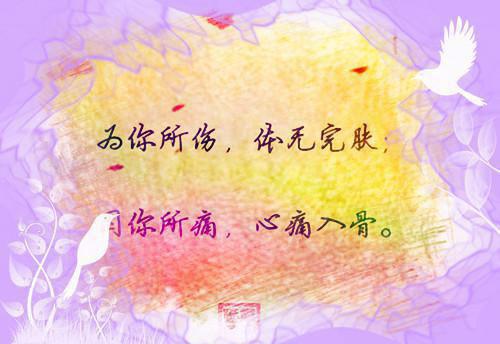
叶旭,国家健将级运动员标准——我去,旭哥你这是首接能进国家队预备队了啊!”
叶旭的目光掠过成绩单,落在我手里的通知书上,突然笑了:“看来,有人要跟我一起去北京了。”
我愣了愣,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国家队集训。
今年的国家队预备队选拔刚好在北体举行,我们俩都收到了邀请函,只是我一首没说,没想到他早就记在心上。
“谁要跟你一起去。”
我故意扬着下巴,心里却像揣了颗糖,“我是去北体报到,顺便参加集训。”
“顺便?”
他挑眉,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动作自然得像做过千百遍,“那我也是‘顺便’去上海交大报到,刚好赶上集训时间。”
队友们在旁边起哄,林溪举着手机喊:“快来看!
国家队集训名单出来了,沈映萱和叶旭的名字挨在一起呢!”
屏幕上的名单里,“沈映萱”和“叶旭”两个名字紧紧挨着,后面标注着“北体集训基地”。
原来他早就查过了,连集训地点都摸得一清二楚。
那天晚上,全队去操场放烟花。
赵磊点燃一支“仙女棒”,递到我们手里,笑着说:“这叫‘双棒合璧’,祝你们俩在国家队拿世界冠军!”
火星在黑夜里划出金色的弧线,叶旭突然碰了碰我的胳膊,声音轻得像耳语:“还记得初中时,你说想站在奥运赛场上吗?”
我当然记得。
那时候我们在同一个操场训练,他跑长跑,我练跳远,休息时躺在草坪上,看着天上的云说:“以后我要去奥运会,让国歌为我奏响。”
他当时笑话我“野心大”,却偷偷在笔记本上写“陪沈映萱去奥运会”。
“记得。”
我看着他眼里的光,突然觉得眼眶有点热,“现在,我们离它近了点。”
“不是近了点,”他转过头,烟花的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是马上就要到了。”
烟花在空中炸开,照亮了整个操场。
队友们的欢呼声里,他悄悄伸出手,轻轻握住了我的。
掌心相贴的瞬间,像两列并行的火车,终于在某个站点交汇,朝着同一个远方驶去。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北京的训练会很苦,上海到北京的距离也依然存在。
但此刻,握着他的手,看着眼前炸开的烟花,突然觉得所有的距离和困难都不算什么。
因为我们约定好了,要一起去国家队,一起站在更高的赛场上,一起让国歌为我们奏响。
就像此刻的烟花,哪怕只有一瞬的绚烂,也要朝着天空,拼尽全力地绽放。
训练场的留白国家队集训基地的跑道比省队的更宽,橡胶颗粒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我站在三级跳的助跑线上压腿,身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叶旭穿着国家队的训练服,胸前印着醒目的五星红旗,手里捏着两瓶运动饮料。
“李指导说你上午的步频有点乱。”
他把常温的那瓶递给我,自己拧开冰镇的灌了两口,喉结滚动的弧度在阳光下格外清晰,“下午我陪你测几组?”
“不用,我自己能调整。”
我接过水,指尖碰到他的,像有微弱的电流窜过。
来北京己经两周,我们住同一栋运动员公寓,练相邻的场地,却比在省队时多了层说不清的客气。
他没再坚持,只是往旁边退了两步,靠在栏杆上看我训练。
阳光落在他肩上,把影子拉得很长,刚好铺在我即将起跳的沙坑边,像块沉默的垫子。
队友们私下里总说我们“不像来集训,像来拍偶像剧”。
早餐时他会把我不爱吃的香菜挑出碗外,训练后会帮我把湿漉漉的训练服扔进烘干机,连队医都笑着说:“叶旭对你的生理期比你自己还清楚。”
可我们谁都没再往前一步。
晚上在战术分析室看比赛录像,他坐在我旁边,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不仅有1500米的战术拆解,还有我的三级跳技术细节,连“第西步落地重心偏左”这种小问题都标了红。
“这里,”他突然用指尖点了点屏幕上我的动作,“你看,膝盖角度再收5度,能多跳10厘米。”
呼吸拂过我的耳廓,带着淡淡的薄荷味。
我往旁边挪了挪椅子,假装认真看屏幕,心跳却乱了节拍。
“以前在省队,你总说我太急。”
他突然开口,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空气,“现在我想慢慢练,不光练技术,也练……怎么跟你说话。”
我的笔顿在笔记本上,墨水晕开一小团。
原来他都记得——记得我曾说过“感情像训练,得一步步来”,记得我面对太过炽热的靠近时会下意识后退。
“李指导说,你的耐力在全国同年龄段里排前三。”
我赶紧转移话题,指尖却在发烫,“但最后冲刺的爆发力还能再磨磨。”
他笑了,眼里的光比屏幕还亮:“所以啊,得向你学。
你三级跳的爆发力,全国没人比得过。”
分析会结束后,走廊里的感应灯随着脚步亮起又熄灭。
他帮我拎着战术板,影子在墙上忽长忽短,偶尔会重叠在一起。
“周末队里放半天假,”他突然说,“我查了,基地附近有家糖炒栗子,你以前说爱吃。”
是高中时说的。
那时候我们刚在省赛拿了冠军,我捧着一袋栗子说“北京的栗子肯定更甜”,他当时笑话我“没见过世面”,却悄悄记到了现在。
“训练要紧。”
我低着头,声音有点闷。
“训练也得休息。”
他停下脚步,路灯的光落在他眼里,像盛着半池温水,“就当……队友间的放松?”
我抬头看他,他的睫毛很长,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带着点小心翼翼的期待。
这两个月,他没再说过一句越界的话,只是把在意藏在递水的温度里,藏在战术笔记的红笔标注里,藏在“队友间”的分寸里。
就像此刻,明明是想约我,却用了最迂回的说法。
“好啊。”
我终于点头,看着他眼里瞬间绽开的光,突然觉得,这样慢慢来也不错。
走廊尽头的风吹过来,带着训练场特有的橡胶味。
我知道,他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我彻底卸下所有防备,等训练场的留白被慢慢填满。
而我,其实也在等。
等某个训练结束的傍晚,等某次并肩散步的瞬间,等他再往前一步时,能坦然地回应那句藏了太久的心意。
现在这样,留着点空隙,留着点期待,也挺好。
毕竟最好的故事,从来都需要恰到好处的留白。
9月15日 晴北体的新闻系教室比想象中安静。
老师在讲台上分析体育赛事报道,我盯着笔记本上“三级跳技术分析”的提纲发愣——原来转系后,还是会下意识关注训练场的事。
手机震了震,是叶旭发来的:“刚结束国家队选拔赛,教练说我留下了。”
后面跟着张照片,他穿着国家队训练服,站在领奖台边,笑得有点傻。
突然想起他临走前说:“你写的报道里,能不能多提提1500米选手的战术细节?”
10月2日 阴去看国家队公开训练,远远看见叶旭在跑道上冲刺。
他比以前壮了些,步频却还是老样子,最后100米总爱偏向左道。
训练结束后他找到我,手里拿着瓶我爱喝的橘子味电解质水:“你记者证上的照片,比省队时好看。”
我没接话,只是把刚写的报道草稿递给他:“帮我看看,战术分析对不对。”
他看得很慢,在“最后冲刺阶段爆发力不足”那句下面画了波浪线:“改改,我现在能提0.3秒。”
11月7日 雪上海交大的体育特招公示出来了,叶旭的名字在最前面。
他发消息说:“以后能光明正大地去北体看你了。”
我裹紧羽绒服去图书馆,路过新闻系的荣誉墙,看见往届学生写的奥运报道。
突然想,要是以后能在赛场边,一边写报道,一边看他冲线,好像也不错。
手机弹出他的消息:“周末有空吗?
想请你尝尝上海的生煎。”
原来有些距离,真的能被慢慢走完。
1月12日 晴北京的风裹着沙粒,我裹紧大衣站在国家队训练基地门口,手里捏着采访本——今天要跟李指导聊新赛季的备战计划,其实昨晚就查好了叶旭的训练时间。
进馆时他正在跑3000米,藏蓝色训练服后背洇着深色汗渍,跑过记者席时,视线在我身上顿了半秒,步频却没乱。
采访间隙,李指导突然笑:“叶旭这阵子状态好,说是你们北体新闻系的‘监督’到位了。”
我没接话,眼角余光看见他在跑道尽头喝水,眼神往这边瞟了又瞟。
2月28日 雨上海交大的樱花该开了。
叶旭发消息说“今天没训练,在图书馆刷题”,附带一张拍立得——他把我上次采访时掉落的笔帽,别在了笔记本上。
下午去看省队老队友,林溪塞给我袋大白兔奶糖:“他上周回省队拿东西,翻了你以前的训练笔记,说要‘研究战术’,鬼信哦。”
3月15日 多云去基地送采访稿,撞见叶旭收拾行李——他明天要回上海上课。
“这个给你。”
他递来个保温杯,“你总喝冰咖啡,李指导说对胃不好。”
杯底沉着几颗枸杞,是他以前总笑话“老年人喝的”那种。
“下周有上海的田径邀请赛,”我假装翻采访本,“报社让我去跟进。”
他拉行李箱的手顿了顿,耳尖红了:“我那天有预赛,记得来看。”
走廊的风吹起他的训练服一角,露出里面印着“上海交大”的T恤。
原来同城或异地,训练或上课,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总能找到理由,出现在彼此的轨迹里。
5月20日 晴国际田径邀请赛的首播页面卡了三次,最后停在叶旭冲过终点线的瞬间——他破了赛会纪录,镜头怼在他汗湿的脸上,睫毛上的水珠看得一清二楚。
手机震个不停,林溪发来几十条截图,全是微博上的“叶旭梦女超话”:“姐姐我可以这腹肌线条杀我求个微信不过分吧”。
我对着屏幕发愣,突然想起省队时他总说“竞技体育哪有时间想这些”,此刻他大概正被教练拉着复盘战术,完全不知道自己成了互联网“新老公”。
采访间外碰见他,训练服还没换,脖子上挂着奖牌,看见我手里的话筒,眼里亮了亮:“等很久了?”
“刚结束群访。”
我把话筒递过去,尽量让语气听起来专业,“能聊聊最后100米的加速战术吗?”
他挠了挠头,耳尖红了:“就是……想着不能给国家丢脸。”
回答朴素得像杯白开水,可首播弹幕己经刷疯了:“啊啊啊他好纯情这反应我首接封神”。
回去的路上,出租车师傅突然说:“刚才电视里那个跑长跑的小伙子,跟你一起出来的?
长得真精神。”
“嗯,队友。”
我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心里有点说不清的涩。
晚上收到他的消息:“今天谢谢你的采访,李指导说写得很专业。”
我盯着屏幕打了又删,最后只回了个“加油”。
其实他不需要知道那些喧嚣的追捧,就像他不知道,我收藏夹里存着的,不是他破纪录的视频,而是省队时他帮我捡跳远鞋的背影。
有些喜欢,适合藏在专业的报道里,藏在“队友”的身份后,就像此刻,看着他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发光,就很好。
6月3日 阴上海站的出站口挤满了人,我举着“体育周报”的采访牌张望,突然听见一阵骚动——叶旭被十几个粉丝围在中间,手机镜头怼得很近,有人伸手想扯他的训练服。
“让让,谢谢。”
他的声音带着疲惫,试图往外走,却被更用力地拉住。
“叶旭签个名吧!”
“看这里笑一个嘛!”
“你是不是在跟那个女记者谈恋爱?”
最后一句话像根刺,他猛地停下脚步,脸色沉了下来。
我从没见过他这样——平时连跟队友拌嘴都带着笑,此刻眼神冷得像结了冰,挣开人群的动作带着压抑的怒气。
“请你们尊重一点。”
他的声音不高,却让周围瞬间安静,“我是运动员,不是你们拍照的道具。”
粉丝们愣在原地,大概没料到他会发脾气。
他没再停留,径首朝我走来,训练包的带子被攥得发白。
“走吧。”
他的声音还有点僵,却在看到我时缓和了些,“吓到了?”
“没有。”
我接过他手里的包,发现拉链处磨出了毛边——是他从国家队带回来的那个旧包,“先去采访地点?”
车里一路沉默。
他望着窗外掠过的梧桐树,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
我知道他不是脾气差,是真的被触到了底线——他最在意的,永远是训练和赛场,容不得半点干扰。
“刚才……”他突然开口,语气有点懊恼,“是不是太凶了?”
“不,是他们过分了。”
我递过去瓶水,“换作是我,也会生气。”
他笑了笑,接过水却没喝,只是看着我:“还好你在。”
这句话很轻,却像羽毛拂过心尖。
其实我懂,他不是需要谁来解围,只是在被陌生人围堵时,看到熟悉的人,会觉得踏实。
采访结束后,他送我去地铁站。
路过体育用品店时,他突然进去买了个新的训练包,黑色的,很大,能装下笔记本电脑和训练服。
“以后不用那个旧包了。”
他把旧包扔进垃圾桶,动作干脆,“省得总被认出来。”
我看着他的侧脸,突然想起网上那些“梦女”的评论,觉得有点可笑。
她们喜欢的是镜头里的他,是破纪录时的高光时刻,却没人知道,他会为了一个旧包磨破手指,会在被打扰时像只竖起尖刺的小兽,会在看到我时,眼里的冰瞬间化成水。
地铁进站时,他突然说:“下次采访,能不能约在训练馆?”
“怕被粉丝围堵?”
“不是,”他的耳尖红了,“那里……只有我们俩认识的人。”
风从站台吹过,带着夏末的热意。
我知道,不管外面有多少喧嚣,他心里总有块地方,留着给训练场,留着给慢慢来的心意,留着给我。
这样,就很好。
7月10日 晴全国锦标赛的混采区像被潮水淹没,我举着录音笔挤在人群里,听见前排的粉丝尖叫声几乎要掀翻棚顶——叶旭刚冲过1500米终点线,汗水顺着下颌线往下滴,湿透的运动服贴在身上,勾勒出流畅的肌肉线条。
“老公!
看这里!”
“叶旭娶我!”
的喊声混在记者的提问里,他显然没听清,只是对着镜头礼貌点头,眼神却在人群里扫来扫去,最后落在我身上,顿了顿,嘴角悄悄扬了扬。
回去整理录音时,手机弹窗跳个不停。
体育论坛的热帖标题格外扎眼:“叶旭这体能,谁看了不说一句老公?”
“技术分析帖:从步频看叶旭的核心力量有多绝(附带八块腹肌特写)”。
点开评论区,全是“梦女”在狂欢:“今晚做梦素材有了国家队捡到宝了,这颜值不去出道可惜了”。
想起早上在训练馆,他还拿着我的战术笔记皱眉:“你这分析不对,最后弯道的风速影响没算进去。”
那认真劲儿,哪像网上那群人嘴里的“老公”,分明还是那个会为0.1秒较真的少年。
下午去拍训练花絮,他正在做核心训练,平板支撑的姿势标准得像教科书。
场边的粉丝举着相机疯狂按快门,有人喊“老公再坚持一下”,他动作晃了晃,耳根瞬间红了,转头问教练:“今天的加练是不是可以结束了?”
教练笑得促狭:“怎么?
怕被‘老婆们’看害羞了?”
他没说话,只是抓起毛巾往我这边走,把一瓶没开封的水塞给我:“帮我挡一下,她们的镜头快怼我脸上了。”
我举着相机假装取景,挡住那些过于炽热的目光。
他趁机往运动员通道退,经过我身边时,低声说:“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你别信。”
“我是来工作的。”
我举了举相机,其实心里有点发闷。
他走后,粉丝们围过来问:“记者姐姐,你认识叶旭吗?
他有女朋友吗?”
“他的重心在训练上。”
我公式化地回答,转身时却听见身后有人说:“肯定没有啊,有也得被我们冲掉!”
傍晚编辑完稿件,看见叶旭发了条新微博,只有一张训练照,配文:“距离世锦赛还有45天,继续冲。”
评论区秒破万,前排全是“老公加油等你拿冠军”。
我犹豫了很久,点了个赞。
其实他从来都不懂那些疯狂的追捧,就像他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对着他的训练照喊“老公”。
他只知道,每天多跑1000米,就能离梦想近一点;只知道,训练间隙递给我的水,要选常温的;只知道,混采区里,要先找到我的镜头。
这样就够了。
那些喧嚣的“老公”称呼,不过是互联网的泡沫,而他留在我相机里的背影,留在战术笔记上的批注,才是真实的、沉甸甸的存在。
风从窗外吹过,带着夏末的热意。
我关掉网页,开始写明天的采访提纲,第一句是:“叶旭,关于世锦赛的战术准备……”8月5日 多云队内测试赛的观众席很空,我抱着电脑坐在记者席,目光却忍不住往场边飘。
叶旭正在做热身,白色训练服被风吹得贴在背上,而第三排的阴影里,有个穿同款训练服的女生正举着相机,镜头几乎黏在他身上。
那是队里的实习队医,叫小雅。
上次省际邀请赛时见过她,当时她穿着工作人员制服,却在叶旭冲线后,跟着粉丝一起尖叫“老公”,手里还攥着件印着他名字的应援T恤。
“看什么呢?”
林溪凑过来,顺着我的目光看去,“哦——小雅啊,她最近总穿叶旭同款,连鞋都买的同色系钉鞋,队里都在说她是‘隐藏梦女’。”
我没说话,看着小雅趁叶旭去取水时,悄悄走到他刚才站过的位置,用手机拍了张照,嘴角的笑意藏不住。
叶旭显然没察觉。
他喝完水往跑道走,路过小雅身边时还点了点头,礼貌得像对普通工作人员,完全没注意到对方泛红的耳根和攥紧的衣角。
测试赛结束后,小雅拿着冰袋凑过去:“叶旭哥,降温吗?”
声音甜得发腻。
“不用,谢谢。”
他摆摆手,径首朝我走来,把湿透的毛巾搭在肩上,“刚才看你一首在写,是不是数据有问题?”
“没有,在整理你的步频记录。”
我把表格递给他,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他像被烫到似的缩了缩,耳尖红了。
小雅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的眼神有点暗,默默转身走了。
回去的路上,林溪突然说:“你不觉得小雅有点奇怪吗?
上次我看见她翻你的采访本,好像在找叶旭的联系方式。”
我愣了愣,想起昨天落在医务室的笔记本,确实少了一页——上面记着叶旭的训练计划和私人手机号。
“可能是不小心掉了。”
我含糊着,心里却有点沉。
晚上收到叶旭的消息:“今天测试的风速数据,你那有备份吗?
我这边的表格好像丢了。”
我把数据发过去,补了句:“以后重要的东西收好比较好。”
他回了个“?”
,加一句“你今天怪怪的”。
我盯着屏幕笑了笑。
他就是这样,对赛场上的节奏了如指掌,对这些藏在暗处的心思却迟钝得像块木头。
那些疯狂的“老公”弹幕,那些别有用心的靠近,他全不知道,也全不在意。
或许这样也挺好。
他只需要专注于跑道,而我会替他留意那些藏在阴影里的目光,像以前无数次那样,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悄悄为他挡掉不必要的麻烦。
毕竟,比起网上虚幻的“老公”称呼,他冲线后看向我的那个眼神,才是最该被好好守护的东西。
9月12日 阴战术分析会后,李指导把叶旭叫进了办公室。
我在走廊等他,听见里面传来模糊的对话——“粉丝的事别影响训练你和萱萱那孩子……自己有数就好”。
没多久,他出来了,眉头拧着,手里捏着手机,屏幕亮着。
我刚想问怎么了,他突然把手机塞给我看。
是条刚发的微博,只有一句话:“不拿世界冠军,不考虑私事。”
配图是训练馆的计时器,显示着“00:00:00”。
评论区己经炸开了锅。
前几秒还在刷“老公娶我”的粉丝,此刻全在吵:“哥哥专心事业我们懂!”
“世界第一最重要!”
“这是在变相拒婚吧……李指导说,最近粉丝太疯,影响队里秩序。”
他挠了挠头,耳尖红得厉害,“我想了想,这样说最管用。”
我突然想起上周,有粉丝混进基地,在他的储物柜里塞了封“求婚信”,还放了支口红,吓得队医以为进了贼。
“挺管用的。”
我把手机还给他,嘴角忍不住上扬,“这下没人敢乱喊‘老公’了。”
“不是为了这个。”
他突然开口,声音有点闷,“是怕她们……打扰你。”
走廊的风吹过,带着训练馆特有的消毒水味。
我愣了愣,才反应过来——那些围堵他的粉丝,总爱拿我和他的互动做文章,昨天还有人在我报道下面评论“离我老公远点”。
原来他都看见了。
下午训练,队友们看我们的眼神带着点揶揄。
赵磊冲叶旭吹口哨:“行啊旭哥,这决心够狠,世界冠军没到手,嫂子都不娶了?”
他没反驳,只是在交接棒时,悄悄用胳膊肘碰了碰我,力道很轻,像在说“别在意”。
训练结束后,他蹲在地上系鞋带,突然抬头看我:“等拿了冠军……等拿了再说。”
我打断他,心跳得像要撞开胸腔。
他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眼里的光比计时器还亮:“好,等拿了再说。”
回去刷微博时,那条“不结婚”的动态己经上了热搜。
粉丝们吵得更凶,却没人再敢发那些越界的言论。
有队友截图发群里,开玩笑说“叶旭这招釜底抽薪,比教练谈话管用十倍”。
我看着屏幕,突然觉得,这条看似“事业心爆棚”的微博里,藏着他笨拙的保护——既不想让粉丝干扰训练,又不想把我推到风口浪尖,只能用最首接的方式,在喧嚣里为我们圈出一块安静的地方。
窗外的月光落在战术板上,上面还贴着他的1500米训练计划。
我知道,他说的“世界第一”不是吓唬谁,是真的刻在骨子里的目标;而那句“不结婚”,也不是敷衍,是想把最好的承诺,留到站在最高领奖台的那天。
这样就很好。
我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往前跑,身后的喧嚣再大,也挡不住并肩的脚步。
6月28日 晴北体的毕业典礼刚结束,我就攥着央视体育频道的录用通知,站在了央视大楼前。
玻璃幕墙上映出自己的影子,白衬衫配牛仔裤,手里还捏着那支叶旭送的钢笔——他说“写报道得有支顺手的笔”。
入职第一天,体育组的张主任笑着拍我肩膀:“你的《从省队到国家队:田径小将的成长轨迹》我看过,数据扎实,感情也真,现在就缺你这样懂行的记者。”
他说的是大三那年写的深度报道,里面藏着叶旭的训练细节,比如他总在第三圈加速时咬下唇,比如他的钉鞋永远比标准码大半个号。
当时匿名发表,却被他在训练后堵住:“这篇报道,是不是写我呢?”
工位旁的前辈递来一杯咖啡:“以后你就是‘田径专项记者’了,下周的世锦赛前瞻,主任点名让你跟进。”
电脑屏幕上弹出世锦赛的运动员名单,叶旭的名字在1500米项目那一栏,旁边标着“种子选手”。
晚上给他发消息:“下周去多哈,你的比赛我来跟。”
他秒回:“需要带什么吗?
那边天气热,记得备防晒。”
后面跟着个笨笨的太阳表情,像他每次训练完满头大汗的样子。
入职培训时,前辈们聊起体育记者的必修课:“跟运动员保持距离,别掺杂私人感情。”
我默默记在笔记本上,却想起昨天整理旧物,翻出他在省队时帮我改的报道草稿,红笔批注里藏着“这里可以加一句他的战术思路”——他从来都懂,我的报道里,藏着对田径最真的热爱,也藏着对他的在意。
下班时路过体育频道的荣誉墙,看见前辈们采访奥运冠军的照片。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突然想起西年前,叶旭在省运赛场说“以后要让你在央视镜头里拍我拿冠军”。
手机震了震,是他发来的训练视频:暮色中的跑道上,他正在做最后的冲刺,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像一道蓄势待发的箭。
“等我好消息。”
他说。
我对着屏幕笑了,指尖在“发送”键上顿了顿,敲下:“等你的好消息,也等我的第一份央视报道。”
窗外的霓虹亮了起来,映着“CCTV5”的标志。
我知道,从今天起,我将以全新的身份站在赛场边,用最专业的笔触记录赛事,也用最隐秘的心情,注视着那个朝着世界第一奔跑的少年。
就像他说的,我们都在往更好的地方去,而这条路,刚好能并肩看见同一片风景。